遭遇信心冲击的文科青年:世界还需要人文吗?
作者: 罗拉哲学硕士,把学历改成大专到咖啡馆求职
青年生存词条
No.7 :文科隐身人
词条释义:在全球性的新一轮文科衰退潮中,“文科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我国的文科生面临着学科价值贬损、社会评价走低、求职难度上升等困境,不少人遭遇自信心和身份认同冲击,在社交场合回避自己的专业,用“无用”来自嘲,陷入自我怀疑,也不再公开承认自己喜欢文学和艺术……文科生们逐渐“隐声”及“隐身”,但并没有放弃对抗偏见,努力破局,寻求“解除隐身”的各种可能。
在算法校准效率、数据解构意义的时代,似乎所有无法被即时兑换的学习都可能沦为一种“错误”,那些曾经滋养人类文明的人文类学科,突然变得“无用”。年轻的文科生们被卡在双重困境中:一面是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发生系统性偏移,致使 “文科无用论” 甚嚣尘上;一面是个体不得不在量化价值天平上试图自证分量,他们虽然热爱自己的专业,却愈发难以自信地阐述文科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通过三位不同人生轨迹的文科生的故事,观察“文科羞耻”症候群的部分切片,或许可以看到,那些无法被自动化的批判性思考、共情能力与伦理追问,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防线。

一年前,庄小白已经停更好几个月的社交账号收到私信,一位关注她许久的女生留言,希望她聊一聊“文科就是服务业”背后的社会情绪,庄小白盯着留言沉默许久,最终什么也没写。
能够谈些什么呢?她那时在春招季上求职不顺利,正在一家咖啡店打小时工,“确实是在做服务业”。而在更早一些时候,她曾看到戴锦华教授对此的回应,戴教授认为,“这个说法好丑,但是这个东西是事实,因为对整个人文的贬低、对梦想和创造力的贬低,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疾病。”庄小白心底里是认同的,但她明面上并没有底气用病态来形容文科被唱衰的处境,因为整个世界似乎都传递着同一个声音——“求职不理想,是你自己还不够优秀”,她对文科的自豪感正在一点点消减。
但从前的庄小白不是这样的,她爱好广泛,有强烈的表达欲,并且也擅长表达。上大学期间,庄小白在她的社交账号上更新文章和视频,用哲学知识解读社会热点、生活现象以及影视、文学等艺术作品,因语言风趣、内容简洁易懂,她渐渐积累了几千名相对稳定的读者。她说:“有人说我的解读总能给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带来启发,更多人在讨论区彼此碰撞出新的火花,那种时刻会觉得自己也算在做一种微小的文化启蒙,就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她面对最常见的提问“学哲学有什么用”时,常常很坦率地回答“无用”,她相信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相信超越工具理性、直指存在本质的价值自觉对社会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对人文精神的这种自信心具体是从哪个事件开始变得虚弱,好像只要离开理论的世界,回到三次元,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在提醒她“不合时宜”。
文科生求职不易已经算是这几年被反复讨论的普遍现象,起初倒并没有令庄小白太过焦虑,因为她了解求职不容易有市场供求的原因,有宏观经济发展的原因,不一定全是个人的问题,她对自己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否定,只是在反复投递简历和刷面试结果都不理想之后,有一些挫败感,而且能在丧完之后打起精神,再加上她物欲不重,自觉可以过“贫穷但快乐”的生活。某次在脱口秀节目里看到一位哲学女硕士大国手讲述自己毕业四年没上班的生活体验时,庄小白还笑说,这不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吗?
但后来,更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微妙贬损让她渐渐焦虑起来。过节时亲戚来家里,看到她做全职儿女,趁她去厨房洗水果时悄悄问妈妈:小白好歹是硕士,真的找不到工作吗?这样下去怎么行。“言下之意好像是我自己懒惰,不愿意出去工作,或者是太过挑拣,不肯脚踏实地。”从前实习认识的一个姐姐想要介绍庄小白相亲,男方一听她是哲学专业的,立刻用开玩笑的方式婉拒,说他自己是俗人,不敢和文艺青年谈恋爱。“文艺青年”,如今在互联网上常常是一个嘲讽的梗,在这个语境里,喜欢文艺等于矫情,等于啥也干不好还装腔作势。
去年冬天,妈妈生了一场不算小的病,医保报销之后,仍然花了不小的一笔钱。虽然爸妈的积蓄勉力应付了这笔支出,但在病床前,庄小白一向秉承的“穷且益坚”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动摇。“我那时候内心开始慌乱,害怕如果再有一次意外,我连一份稳定的收入都没有,拿什么来保护爸爸妈妈呢?也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那些自洽,是不是一种无力面对现实的伪装和逃避?”
早前看脱口秀,大国手在节目中调侃哲学时说:“假如去上班,别人擅长推广运营、数据分析,而我擅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留下问题。”庄小白当时哈哈大笑,后来,她渐渐有点笑不起来,因为没有人想要真正活成段子。
在咖啡店打工时,庄小白在应聘及入职资料中把学历填成了普通大专,周围没有人知道这个总是认真擦杯子的女孩是一名哲学硕士。她的账号也渐渐沉寂,因为在自我定位与社会评价体系之间,她还没有理顺自己。“我真切地体会到,很多人生难题,无法靠思想来实际解决。而再坚定的自我,在现实困难面前,总归多少是会被影响的。信心不够,再写东西就会缺乏精气神,写出来自己都不信服。”
最近,庄小白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求职。她收藏了许多文科生跨行求职的面试攻略,以及如何进一步打开思路开拓求职途径,也买了复习资料,准备报考下半年的几个编制考试。
在小红书刷经验帖时,庄小白看到一些顶级名校哲学专业毕业的前辈们发的笔记,在前辈们的分享中,他们的同学如今遍布诸多行业,不乏金融、咨询企业的精英大咖。尽管庄小白一直以来都不认同优绩主义,但在看到他人华丽世界时,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闪念:“或许还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强,如果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卷到顶级名校,结果是不是会有不同?”
讲述人
庄小白: 1999年生,哲学硕士,毕业一年,做过几份短期兼职,目前在求职中。
在清华读文科硕士,也会有文科羞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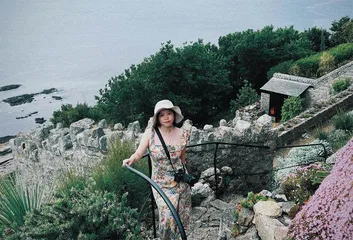
文科训练的是一种复合能力。真正学好文科的人,看市场、看企业,会更具备战略的高度与深度。
在另一座城市,公孙大娘过上了庄小白设想过的生活,她是清华大学的文科硕士。
公孙是坚定的文科爱好者,从小到大一直喜欢文科,也对文科抱有坚定的信心,本科学中文,研究生读新传,都是她的主动选择。如今她在社交平台上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分享职业思路、社科文化,以及一些社会现状的思考。
无论文章里还是视频中,她的表达都充满自信,看不出任何对文科身份的犹豫或不认同,但她的成长时代已经过了“文科热潮”阶段。无论是社会经济、就业环境,还是社会评价体系,都在促使这代年轻人重新审视对文科的浪漫化设想,选择更务实的理工科学习方向,公孙一路走来,体验过许多文科不被看好的时刻。
高中选择文理时,教化学的班主任曾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要学文,因为文科生首先在高考时就不占优势,理科考到全省几千名都能上985,但文科要考入全省前一千名才有可能,而且文科就业难、起薪低。现在回头看,老师虽不是歧视文科,但文科在社会体系中的客观处境确实如此。
清华读研时,公孙所在的新传专业被戏称为“养老院”,她遇到过一些理工科的男生带着理科优越感鄙视新传专业,“他们认为新闻专业门槛很低,随便学学都行,不需要高智商”。
公孙的日常表达方式也曾被一些人用很难听的字眼评价,因为她说话习惯用书面语,喜欢引经据典,有时候会随口引用诗词。在社交场合提到自己喜欢读书时,也会接收到很多异样的眼光,她说:“大家会觉得我在装文艺、矫情什么的。我不为文科羞耻,但有别人在替我羞耻。”




讲述人
公孙大娘:95后,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硕士。从小热爱文科,在成长中不断以文科生身份去探索职业边界,追求职业理想,先后经历三次转行,从体制内、教育行业、科技行业到AI 公司。
好在,外界对文科的贬低虽然令人不舒适,但公孙自己从未停止对人文理想的探索。她说自己是从心而行的人,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实习期间,她去过几家国内知名的传媒集团,发现职业环境与自己想要践行的人文理想相去较远,于是在毕业后考了选调生,想要去基层做具体的事,帮助具体的人,后来,又辞职转入教育行业、科技行业,再转到现在的AI 公司。“一直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给他人提供人文关怀,用人文精神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在以理工科闻名的清华读文科,在科技公司里从事市场工作,公孙都没有过“边缘派”的感觉,在她看来,文科和理科并不是二元对立、也不是主从关系,只是不同的领域,不同学科的人可以在工作中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目标。
即使当前全球性的文科专业裁撤潮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她也认为文科生不必因为就业难、社会唱衰文科而丧失对自己的认同,就业难是诸多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有宏观经济形势,也有就业市场的供需不平衡。文科岗位需求少,毕业生供大于求,并不等于文科不重要、文科生没有专业。
“文科训练的是一种复合能力。真正学好文科的人,看市场、看企业,会更具备战略的高度与深度。对用户和市场的洞察,同理心,与人沟通的能力,表达的能力,把技术语言翻译为大众语言从而和消费者产生连接的能力,都可以帮助文科生在许多行业里很好地胜任工作,文科生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公孙说。
当“算法至上、绩效为王”的工具理性思想在工作和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时,公孙认为,文科生不仅不要羞于表达,反而更应该站出来谈论。“我们可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周期危机,可以反思科技进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可以思考优绩主义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伤害、个体如何在信息洪流中建设自己的价值体系,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需要社科对人的关怀和帮助。我们还可以借助AI 技术,替自己实现许多的设想,提升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当然,前提还是本身有创意,擅于和AI 交流。”
这个在文科耻感环境中始终摒弃外界评价,一路昂扬自信的姑娘,如今正在用自己的人文素养,将代码世界转化为对一个个具体人的关怀。未来或许她还会继续转行或转岗,但文科教育带给她的思辨精神、对他人的同理心、对世界的关怀和悲悯,都会成为她做职业选择和人生选择时永恒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