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缓冲区打造心灵复原力
作者: 蒙丫 三水木 松果 一皆 乌咪 吕曦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精神问题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社会的“隐形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有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新华网2024年的消息称:在中国,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达到了16.6%,影响人群超过2.3亿。这些数字背后,折射的是真实的人生困境。
本期《特别企划》,我们通过三位女性的视角,呈现不同生命阶段的精神困境与突围,她们中有人是“鸡娃”赛道上的妈妈,在教育压力中寻找平衡与方向;有人童年受伤,多年后回家修复家庭关系;有人是深陷焦虑的职场人,通过潜水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缓冲区。
我们也邀请了两位从事心理学教育与研究的专家,请她们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波动中,寻找复原的方向。面对困境,我们并不孤单,可以寻找同伴,求助专家,解锁内在自愈力,开启人生修复模式,韧性生长。

教育篇
谁是起跑线上的赢家?三个孩子的成长观察
我孩子是个普娃,智力平平,成绩一般,升入名校初中部,完全是沾了学区划分的光。
开学第一周,名校就给家长来了个下马威——周二突袭式摸底考试,周六召开家长会。初一教研组组长是个留短发的中年女老师,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在座的都是亲生父母吧?”家长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停顿了五六秒又补了一句,“生孩子谁都会,懂培养孩子的才是亲爹亲妈!”哦,听懂了,这是骂我们这届家长差,孩子成绩也差。
家长会后,家长们迅速行动起来,报班的、拉群鸡娃的。我们小区里的十几个初一学生家长也拉了个群,不知道是谁起的群名,叫做“Y小区状元家长群”。九年后再看群名,我只有一声叹息。
“正能量小队长”的枯萎
小区里的头号状元种子选手,绰号“正能哥”。他跟我女儿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评优模范干部,言行特别正能量,调皮生给他起了个外号“正能量小队长”,后来大家叫他“正能哥”。
正能哥的妈妈是一名微商,喜欢晒“成绩单”。有时晒销售额破亿,有时晒销冠迪拜团建,但晒得最多的还是她的优秀作品——正能哥。她晒他在名师工作室弹钢琴、在体育馆游泳池畅游(都是中考加分项目)。她对孩子的学习也抓得紧,正能哥小学时一直是年级前十名。
鸡娃群中,孩子成绩好的家长自然是意见领袖。正能妈分享过一份孩子的暑假学习计划表,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每四十五分钟为一个单位,严密有序。
当时,我家队友特别羡慕人家的执行力,希望女儿跟着学,结果女儿不屑一顾:他那日子过得跟判了“无期徒刑”似的,敢逼我,我跳楼给你看!
她爹扼腕叹息:普娃就是普娃,不上进,没觉悟。
初二下半学期,正能妈突然消声了,不久后,一个爆炸性消息在家长群传开:正能哥“病”了。
根据传出的消息,正能妈曾找同学家长购买强力安眠药,没成功,那位家长很气愤,说正能哥很可怜,一个月都没好好合过眼,一睡就做噩梦,他妈也不带他看医生,非说他只是心理脆弱。
这是受了多大的刺激?群里家长纷纷从孩子那里打听情况,拼凑出了事情的大概轮廓。
原来,随着初二课业难度骤然加深,孩子们为了解压,开始玩游戏,多数家长睁只眼闭只眼,那毕竟是孩子不多的减压出口。班上有个男孩很仗义,偷借给正能哥一部任天堂游戏机,被正能妈发现,她像疯了一样,抄起菜刀冲过去,哐哐哐三刀劈断了“任天堂”。
这件事后,正能哥就像被抽走了魂,仿佛那刀劈的不是游戏机,而是他的最后一丝喘息。
到底是长年累月全年无休的学习压垮了他,还是“妈妈三刀劈断游戏机”的场景击溃了他,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总之,一个外表能量满满的正常孩子,突然“枯萎”了。
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晚自习,我女儿放学回来说正能哥“疯了”,晚自习时对着教室角落大喊“有鬼”,还跳到凳子上,仿佛在躲避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吓得全班学生争先恐后逃出教室,学校也紧急通知家长接他去医院。
到了初三下半学期,正能哥正式办理了病休。
再后来,我就再没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妈把家长都拉黑了。

从“状元种子选手”到“说唱歌手”
小区还有一个叫直树的男孩。
直树爸是个投资人,谈起期货、外币、比特币交易等头头是道,他曾“不经意地”在群里透露,除了买学区房,还为孩子准备了三年两百万的辅导费用。我们这些普通人哪见过这种大阵仗的“教育投资”,纷纷点赞这股教育决心。
正能妈和直树爸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鸡娃路线,前者是密不透风的陪伴,后者靠钱砸,我们都想看看哪种投入更见效。直树从不去补习班,都是名校的硕士博士生上门一对一教学,他的成绩在初一初二的时候都不错。
然而,正能哥出了状况后,直树的画风也急转直下。
初三上学期,直树的成绩下滑厉害,大家都知道他家砸钱补习的事儿,成绩提不上去难免会议论。有次班主任在课上说他爱打扮,心不在学习上,浪费父母钱,没想到这一下子戳到了直树的痛点,他当场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怒怼班主任。
“演讲”的内容大意是:你一辈子打工能赚多少钱?这个世界赚钱的法子多得很,有时候靠脸就行。学习也是为了赚钱,我趁着年轻赚流量,相当于你干十几辈子。
教了十几年书的班主任,听到流量时代的“妖孽”讲歪理邪说,气得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
那天晚上,直树家打孩子砸东西的声音特别大,业主半夜要报警。后来听说直树和他爸讲,那三年几百万的中考投资,他即使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赚回来,不如给他投一千万做网红,赚上一个亿,分他爸一半当教育回报。直树爸一拳抡到儿子嘴上,暴力表态:你没有投资价值,一毛钱都不会投。
自那后,直树打死也不愿上一对一辅导课,也不去学校,跑回了潮汕老家。
2023年前后,精准又可怕的抖音大数据不断向我推送直树的直播:一头姜黄色卷杂毛,自恋油腻的怼脸拍,再加上爆闪的特效和绕口的说唱,完全看不到当年清秀小男生的影子。如果有网友说他唱得不行,他会追着骂十几分钟不带停的。原来的家长群成员,估计也都收到了抖音推送,有个当医生的妈妈跟我讲:直树这孩子,看着像是有点躁郁症的迹象。
也不知道直树赚到一个亿没有,但直树爸是说到做到,没为儿子提供任何资金支持,翻看他的朋友圈,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十岁的次子和三岁的小女儿身上,开始注重传统文化培养,从背诵《弟子规》开始。


翻盘的“大仙儿”
连续两位状元种子选手败走,我们这个“高开低走”的状元群里,家长们没了鸡娃的心气,纷纷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值,生怕再出个意外。再后来,孩子们都上了高中,或普高或本部牛高,一直到高三,也没有成绩特别出挑的孩子。
但是最近,我女儿跟我说,那个“高开低走”群里,还有一个潜水的种子选手的妈妈,她娃在学校有个外号:大仙儿。
大仙儿的学习成绩中上,英语成绩接近满分。女儿回忆,大仙儿平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老迟到,只对科幻小说感兴趣,聊天都是人类终极命运之类的形而上问题,英语课时写纯英文科幻小说。
这女孩的妈妈也比较特别,在暗潮涌动的群里,她从没问过跟提分报班有关的问题,就问过几次谁家孩子有空结伴一起去玩乐队。
而且这位妈妈常年缺席家长会,据说都在国外飞,我只在初三家长会上见过她一次,当时老师让她给孩子赶紧找个辅导班提一下理科分,她一点也不在意,现场跟老师掰扯“教育是人生长线战略”,老师生气说“中考才决定人生长线”。
中考结束,这孩子上了一所普通高中,但她妈对此挺满意,还带孩子去国外玩了一圈。别家都在朋友圈发孩子直升重点本部高中的喜报,只有她发孩子写的英文科幻小说在国外某个不知名的小说赛事中获奖,全家去领奖的喜讯。
2024年,文科系的大仙儿居然靠着参加科幻小说大赛时认识的某个外国大学教授,申请到了一个人工智能项目的参与机会,拿着奖学金去法国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跨越,在女儿中学同学群里沸腾了好一阵子。虽然自媒体都在喊“文科已死”,但这个爱写科幻小说的女生,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她朋友圈里的自拍照,眼神里闪烁着光。反倒是女儿的同学们“自鸡”了多年,早已成为眼里无光,未来梦想只是考公刷绩点的沉闷躺平族。
作为一个普通妈妈,我无法断言哪种教育方式最适合孩子,也没见过哪个家长能给孩子铺就一条完美的未来之路。人生漫长,或许,真正的教育,并不在于让孩子在起跑线上耗尽所有精力,而在于呵护他们对生活和未知的热情,这样,未来的道路上,他们才是眼里有光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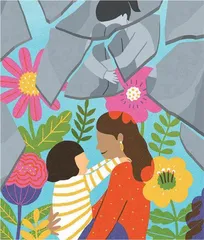
家庭篇
“断亲”之后,与家重逢
剪刀戳出的血窟窿
母亲打我,从不需要理由。
我七岁时,有一天母亲在小树林里捡到一根趁手的槐树枝,她仔细撕掉树皮做成棍子,立在床边。第二天,我无故挨打,仿佛是为测试棍子是否好用。
挨打时,我通常躲在门后,那里空间小,棍子挥动的幅度不会太大。我无法预测棍子下一个落点是腿上、手臂上还是头上,只能死死盯着棍子的轨迹,用手臂护住头部,有时候判断错误,就显得很滑稽。
父母离婚后,我和姐姐被判给母亲。离婚让母亲愤怒不已,她固执地认为所有人都欺负她,她必须控制我们姐妹不要变坏,同时与“负心”的父亲、冷眼的亲戚、说闲话的邻居等“坏人”战斗。
姐姐大我七岁,为讨好母亲,她常“举报”
我,或抢先打我。她下手更狠,常打得我鼻血横流,有时还借用“武器”,比如拿剪刀戳我的腿,至今我小腿上还有伤痕,摸上去中间是凹陷的,就是当年戳出的血窟窿。
挨打最让人难为情的是夏天,手臂和腿上一道青一道紫,我不敢穿短袖、裙子,再热也穿长袖长裤。但有些事却遮掩不了,因为母亲的好战不仅局限在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