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图》,宋人与南食的恩怨情仇
作者: 庄语乐荔枝,在古代也写作荔支,是宋代院体画(宫廷画)的一大主题,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幅册页《荔枝图》(图1)就是其中的典型。册页这种形制兴起于唐代,将多张小幅书画作品分页装裱成册,便于欣赏和收藏,因此在后世也十分流行。这幅《荔枝图》没有款识,横25.3厘米,纵24.3厘米,以丝绢设色,工笔描绘荔枝的样貌,彰显了宋代院体画的写实风格。
宋人心头好
今天,四川、福建、两广地区都是荔枝的重要产地,但在宋代以前,荔枝种植北界虽到蜀地,但主要在岭南,也就是今天的两广、海南地区。由于交通不发达,岭南荔枝进贡到中原,非常劳民伤财,以至于汉和帝曾经禁止进贡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枝自唐代以来长期被认为来自岭南;近来虽有学者依据《舆地纪胜》等材料指出,杨贵妃吃的荔枝其实来自蜀地,但岭南说也没有就此被否定。到了晚唐五代,中原动荡,大量中原移民入闽,给闽地带来巨大的发展,也就直接导致了当地荔枝种植业的进步。

上海博物馆藏
据宋初笔记《清异录》记载,当时闽地士人进京赶考,对家乡荔枝大加吹捧,说:“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面对他人质疑,更是直言天底下哪有能和闽地荔枝并驾齐驱的水果。有江西人以杨梅与之相争,最后两人竟大吵一架。虽有闽人自夸之嫌,但在宋代,闽地荔枝胜过岭南,也是士人中的共识,比如宋初大臣陶榖,身为陕西人,就认为岭南荔枝确实比不上闽地荔枝。
闽地的荔枝种植大盛,也让研究荔枝成为一门学问,用以记录和鉴赏不同种类荔枝的谱录也随之涌现,其中福建人蔡襄(字君谟)的《荔枝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直到明末,邓庆宷编纂《闽中荔支通谱》时,仍将这部书列为第一卷,题作《宋蔡君谟荔支谱》(图2)。蔡襄开篇就说“荔支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此后,又将岭南和巴蜀的荔枝批评了一番,说它们“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并且表示就算是其中的优等品也只比得上东闽所产荔枝的下等品。蔡襄官居高位,不仅以书法扬名天下,也擅长研究吃喝,茶叶、荔枝皆在其列,经他这么一说,荔枝以闽地最优的印象也就刻入了食客心中,据当代学者陈灿彬统计,此后的各类荔枝谱中,鉴赏福建荔枝的“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岭南”。凡此种种,都是宋代荔枝种植和研究发展的体现。
南食入诗画
荔枝种植的发展当然带来荔枝文学的兴盛。宋人承唐人“解酒荔枝甘”“旧识唯应有荔枝”之后,更是把荔枝当成寂寞生活中的亮色。宣和年间,李纲被贬福建沙阳(即沙县),尝到荔枝的滋味,立马写下了《荔支赋》,标举“且食荔支,此非我力”,面对贬谪生活的无奈,不如放下焦虑,吃荔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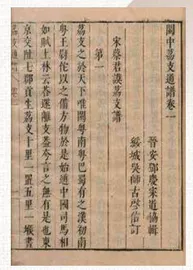
中的《宋蔡君谟荔支谱》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荔枝作为诗文主题不是宋代才有,宋人创作的大量荔枝图画,却是前代所未见的。而且,不少荔枝图随荔枝谱一起发行,蔡襄的《荔枝谱》最初便是如此。这大抵是因为当时的中原人大多没见过生在树上的荔枝,故而需要附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其外貌。荔枝作为图画主题的高光时刻,无疑是被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画进《写生翎毛图》(图3)。这幅《写生翎毛图》今有四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分别题为《写生翎毛》和《翠禽荔枝》的两幅明代仿品,辽宁省博物馆亦藏有一副,形制与台北所藏相同,亦出明人之手。大英博物馆藏的这幅《写生翎毛图》,最初同样被认为是明人伪作,近年,经专家辨正,已基本可以确定是宋徽宗真迹。
总而言之,荔枝在宋代不仅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有专书描写,也延续着在诗文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成为画作的描摹对象,乃至进入宫廷,被皇帝选作“御笔”的主角。一种水果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在古代也是十分特别的了。
不过,如果把荔枝放在“南食书写”的传统中来看,就会发现它鲜亮明快的色泽下暗藏着更为复杂的辛酸之情。饮食诗一直是古诗创作的重要题材,所谓南食,就是南方的食物,尤其是南方特有的食物。在唐宋时的中原人看来,这些化外之地的食物有着可怕的魔力。韩愈被贬潮州,初见岭南饮食,便被牡蛎、虾蟆(蛙类)、章鱼等奇特的食物吓到了,在《答柳柳州食虾蟆》一诗中,大呼“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唯恐自己因食用南食而沾染“蛮夷”之风,并且斥责柳宗元(柳宗元被贬柳州,故称柳柳州),认为他视虾蟆为美味,简直是泯灭人性。这种情绪虽然夸张,但也很好理解,就算是现代人,若不习惯吃蝗虫一类的昆虫或是福建的沙虫(一种环节软体动物)做的“土笋冻”,见到这些食物还是会天然排斥乃至厌恶。
到了宋代,人们对南食的接受程度虽然高了不少,但仍然不乏抗拒。当时“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广南食蛇”,引得中原人每每发笑。对中原士人来说,南方人吃蛙、吃蛇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甚至就连喜爱荔枝的李纲,也在《槟榔》诗中表示,随俗食用槟榔、荔枝,要背负“端忧化岛夷”的心理负担:岛夷是南北朝时北方对南朝的蔑称,一吃南食,就要担心变作蛮夷,这也是当时人的一般认识。而荔枝作为典型的南食,纵然备受追捧,也无法完全摆脱化外之物的底色。
荔枝与苏轼
宋人中最爱谈荔枝的,恐怕非苏轼莫属,他还没去过南方的时候,就心心念念吃荔枝。元祐三年(1088),他送同僚曹辅赴闽地任职,在送别诗中感慨:“一从荔支食,岂念苜蓿盘。”期待自己能吃到荔枝,也就不用再吃乏味如苜蓿的食物了,为此他甚至急切地说“我舟何时发”;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时,友人提议食用蜜渍荔枝,他也欣然赋诗。这时候的荔枝在他笔下还是一种美食的形象,苏轼也许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南贬生涯中,吃荔枝的时候还多着呢,而那时,荔枝的含义也没这么简单了。

大英博物馆藏
苏轼被贬惠州时,姬妾遣散,只有王朝云执意相随,但不久后,朝云就因水土不服而死。究竟为何水土不服呢?朱彧的《萍州可谈》说:广南的市场贩卖用蛇熬制的羹,王朝云原本没见过这种食物,随东坡一起到惠州时,以为蛇羹是一般的海鲜,便买来食用,一问才知道是蛇,她一听就大吐不止,大病数月,最终病死。朱彧随父朱服游宦,与苏轼、王安石等朝中重臣多有来往,苏轼从海南儋耳(今海南儋州市)北归时,朱彧又正好和他相逢,这则信息想必是直接得自苏轼或其身边人。朝云究竟多大程度上是被杯弓蛇影的心理作用吓死,自然已经无从证实,但究竟是这可怕的南食带走了她的生命。苏轼当然悲痛万分,写下了大量的悼念文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出了那首最有名的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孝宗刊本《东坡集》中,这首诗是《食荔支二首》中的第二首,其后半部分则写作:“日啖荔支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图4)诗前,苏轼还写了小序交代具体的故事,即传闻这棵荔枝树是宋初大臣陈尧佐(谥文惠)手植。后来,这首诗单独析出,题为《惠州一绝》,诗中的个别字也发生了变化,这当是流传过程中的讹变,并未影响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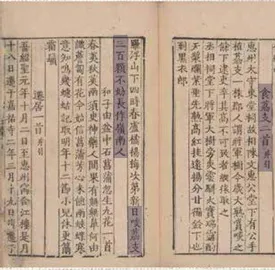
今人并非没有注意到,无论荔枝还是卢橘(枇杷),都是贬谪诗中的重要意象,于是认为“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苏轼苦中作乐,这当然没错;但往往被忽略的是,这句诗还暗含了每日吃荔枝这样的南食,会让人变作岭南人之意。苏轼是眉州人,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人,但与岭南尚有不少距离,他不仅不甘长留岭南,而且也正是岭南的恶劣环境和南食,带走了他心上人的生命。荔枝虽然好吃,但苏轼怀着这样的心绪写荔枝,恐怕也少不了几分仇怨,而这些情绪最终化作一句无奈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当时的苏轼究竟是怨恨还是已经释然,当然任由读者自行体悟,但在之后暗无天日的贬谪生涯中,每每看到荔枝,念及王朝云,又想到自己几年前轻佻的一句“我舟何时发”,这位饱经风雨的文豪胸中,还是会泛起波澜吧。
(责编:李玉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