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手机的日子里,古代人晚上熬夜都在干什么
作者: 三毛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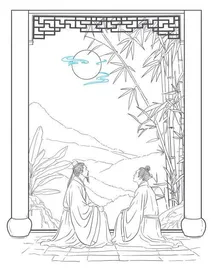
在我们的印象里,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漫漫长夜只有枕头相伴。宵禁制度使许多朝代的夜生活相当乏味。
到了宋朝,宵禁政策松弛,夜晚的寂静被鼎沸的人声代替,街巷灯火通明、好不热闹。越夜越嗨,吃喝玩乐、蹦迪开趴,现代人的夜生活,都是宋朝人玩剩的!
吃喝玩乐,不舍昼夜
夜生活怎能没有夜宵?吴自牧在《梦粱录》第十三卷中描述南宋夜市,“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姜虾……各有叫声”。
想必一进这夜市,就已经食指大动、垂涎三尺了。
吃下各色小食,若是渴了,便来上一碗冷饮。
什么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更是看得人选择困难症都犯了。
吃饱喝足,就该逛逛街、听听曲。瓦舍勾栏有请!进入瓦舍,才懂人声鼎沸的真正含义。瓦舍是宋朝固定的娱乐场所,其中用来演出的舞台往往是一个四方的台子,台子四周装有栏杆,因此称为勾栏。在当时,大的瓦舍有十几座勾栏,最大的勾栏甚至能容纳几千人。
歌舞、杂技、南戏、傀儡戏、驯兽、魔术、皮影戏、相扑……从早到晚、全年无休。如此繁荣的夜市文化,难怪宋朝人舍不得睡觉,要“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
夜游文人的“自我放风”
相信大家在初中都学过《记承天寺夜游》这篇课文,苏轼夜半骤然起兴,拉上张怀民出门赏月。实际上,夜游并非是苏轼的什么小众宝藏爱好。
唐中期后,宵禁制度逐渐宽松,夜晚这个“emo时间”便成为文人“自我放风”的绝佳时间。
或泛舟游湖,或旷野漫步,或吟诗赏月……
文人通过排遣愁绪、修身养性、超脱世俗,也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文章与诗作。
如苏轼最为著名的《赤壁赋》,与好友月夜泛舟的舒畅、对个人遭遇的伤怀、感天地无穷的超脱,情、景、理三者交融,宋代的唐庚评其“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南宋陈起的《夜过西湖》则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夜景。
诗中写“鹊巢犹挂三更月,渔板惊回一片鸥。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
夜半三更,弦月像是挂在鹊巢之上,突如其来的渔板敲击声,惊起鸥鸟翻飞盘旋,欲吟诗却无笔墨可用,索性蘸了春天的西湖水随手写在船头。
透过诗句,今人也能感受到诗人的愉悦。
当然,在夜游这种谈天说地的活动中,“吹牛”可能会迟到,但必不可能缺席。
相信许多人都听过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张岱《夜航船》序言中的这则故事:
一僧人与一士子同乘一船,船上士子高谈阔论,僧人觉得他有大才,心怀敬意,便在狭小的船舱中蜷缩着脚不敢舒展。
当僧人无意听到士子的话中有错漏,于是问他:“澹台灭明是几个人?”士子答:“两个人。”
僧人又问:“那尧舜是几个人?”士子答:“一个人。”
僧人顿时敬意全无,笑着说:“且待小僧伸伸脚。”
“溪浅水声喧”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
古代人有自己的party
你以为通宵开趴是现代人的专利,其实古代的公子王孙、达官贵人们早就研究出了聚众狂欢的一万种方式了。
南唐兵部尚书韩熙载开的party可谓“千古流传”。《韩熙载夜宴图》记录了这场穷奢极欲的派对,图中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宾客酬应,应有尽有,妥妥的狂欢。比起达官贵人,文人们的party可就高雅多了。
他们十分钟情于聚众于庭院中观赏夜景,即使因为照明设备的限制,他们能够欣赏到的景物极其有限,仍乐在其中。
他们观赏最多的是庭院中的花与头顶上的明月,范成大的“绛霞浓淡月微明”便是他观夜间烛光下的海棠花所咏。
除此之外,文人还有一种雅玩,称为“斗茶”,就是每个人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茶,品评分高下。
范仲淹曾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写:“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文人在斗茶这件事上的胜负欲可见一斑。
古人在斗茶时还要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所谓“熬夜强迫症”
古人与现代人的“熬夜强迫症”,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
古人“昼短苦夜长”,于是选择“秉烛游”;而如今的打工人从繁忙的职场中挣脱,疲惫的大脑和身体却只能机械地进行“刷手机”这个动作。
明明如今的物质较古代更加丰富,怎么我们的夜生活却贫瘠得捉襟见肘?
你需要的,是一些“续命”的小放纵。
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河谷的回响里、在山巅的薄雾中找寻情绪的出口。
或许是一个无所事事却又心血来潮的周末,或许是一次期盼已久的假期,来一场或远或近的旅行。倾听山川湖海的自然之音,回望名人名家的历史足迹,感受陌生地域的民俗风情。朝霞、落日和历经时光淬炼的文物,才是洗涤灵魂的良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