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角度看丝绸之路
作者: 刘庆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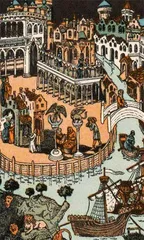
从古代中国通往亚欧大陆各地曾经有多条“丝绸之路”,其中以“沙漠丝绸之路”最为著名。这些路线早已淹没于地下、水下,今天人们的认知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点”,结合文献记载,再连接成“线”。
丝绸之路主要是外传了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物质文明,西域受其影响最大并被纳入中国版图。沙漠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基本上可以说是单向的,往来的商人主要是中亚的粟特人。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丝绸之路兴盛之际都正值中国进入盛世之时。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
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那么,这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这条线路呢?“线”是由千千万万个“点”组成的,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水下的“路”。
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人类史前时代,东亚、地中海、中南美、南亚次大陆等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上述不同文化发展出了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们之间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与先秦时代的农作物小麦、家畜的牛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马车、金属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
东亚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时代已经西渐。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并出现融合。西传过去的也包括农业。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今和田)就可能与中原发生往来。先秦时代以于阗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内地考古发现很多。1974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土了五百多件玉器,经过鉴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玉。
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东方。它传过来的线路是,从和田到吐鲁番,然后北上通过新疆北部,到了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然后再向东,经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阳,然后再往东到了山东,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传播路线。
与此同时,具有先秦时代特点的内地文物,也在西域遗存中屡次被考古发现,如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秦代漆器残片、战国时代“四山纹”铜镜等。考古资料还显示,从甘肃进入新疆东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进的脚步,他们以哈密绿洲为基地,沿天山余脉南北两路继续西行,一路向北进入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另一路向西进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
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草原丝绸之路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欧亚文化交流中仍然在发挥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以平城(今大同)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在平城开凿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石窟寺即云冈石窟。后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区的贵族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庭金币、伊斯兰玻璃器等文物。
公元4—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
沙漠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鉴于西域三十六国与西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与主动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尔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搞屯田,使西域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城址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据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国家的缩影,皇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楼兰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方形的。
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亚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驶国家权力的物化载体。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和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
天山南麓的轮台地区最受瞩目的工作是寻找西汉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遗址,一般认为今轮台县策大雅镇的乌垒城遗址即西汉时代的西域都护府遗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轮台地区还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协尔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台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发现有汉代遗物。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具体城址。
罗布泊和若羌地区是汉王朝在西域经营最多的地方,汉代的楼兰、鄯善古国都在这一地区。这里主要的汉代城址有布淖尔土垠遗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尔乞都克古城等。关于这些古城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城址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
有学者根据出土汉简等认为,古代楼兰道上的布淖尔土垠遗址,可能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LE古城早期是楼兰国都,后期是西域长史治所;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王从LE古城迁至若羌县城附近车尔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尔乞都克古城,作为鄯善国都城: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长史治所或“楼兰之屯”的遗址;LK古城可能是西汉伊循城故址;LL古城则可能是西汉伊循都尉府所在地。
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三千多米,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汉代城址。关于此城址,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国都城员渠城、尉犁国都、焉耆镇城等多种说法。
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北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的遗物、遗迹很多,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
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发现的古代大堤用柳条覆土筑成,应为水利工程。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的一部分。
新疆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是内地农业与农业技术同时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新疆。
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藉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
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八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佉二体钱的不断发现更是西域使用汉文的重要证据。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
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