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理念下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配额悖论
作者: 彭拥军 杨伟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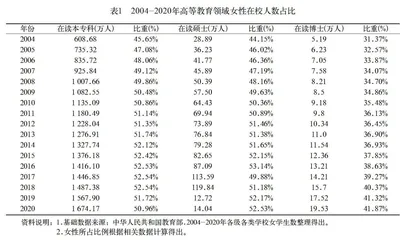
摘要: 配额制度能够帮助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更加公平有效的配置,并保证社会处境不利者获得基本的教育份额。然而在现实性上,公平理念下的高等教育配额设计仍然面临着诸多难以回避的悖论。从高等教育接受者视角看,高考分数对于教育接受者而言意味着平等的教育竞争资格,但不同教育接受者因各种内外因素或不同等级与群体的划分常常会遭遇差异性对待;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视角看,不同高等教育接受者需要面对裹挟其中的高等教育在制造精英与普惠大众间的质量悖论,以及因性别差异等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价值悖论。由于准入悖论、过程悖论和成长悖论的客观存在,公平的分配理念和科学的配额设计在运用于高等教育全过程中,仍然只能小心翼翼而无法左右逢源。
关键词:公平理念;高等教育机会;高等教育资源分配;配额悖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1-0048-12
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演进过程中,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从“是否有学上”的一般性竞争转化为“能否上好学”的优质教育机会竞争,竞争时空由争取上学机会的入口竞争转化为争取优质教育机会的从入口到出口的全程性竞争。竞争格局的变化使如何配置高等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资源变成了特别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配额制度是一种给组织中的个体或群体分配某些资源或机会而事先确定或保留一定分配比例的做法或制度安排[1](P47)。在高等教育场域,我们常常借助配额制度来帮助实现高等教育资源更加公平有效的配置,以便更好地达成高等教育在制造精英与普惠大众之间的适度平衡,并保证社会处境不利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教育份额。然而,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配额制度常常难以回避某些配额悖论。本文试从高等教育接受者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两个视角来加以分析。
一、公平理念下的配额悖论:高等教育接受者视角
高等教育机会如何分配是高等教育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配额制是实现有限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一种简单、快速和高效的制度设计,如果它能够兼顾公平,这种设计就不失为一种方便实用的机会分配手段。然而,从高等教育接受者视角看,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配额设计需要正视以下悖论。
(一)平等的资格与不平等的邀约:高等教育 机会分配的配额悖论
在我国,高考是一种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制度化手段,其不问出身、唯分数选贤的原则彰显了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因为参与到这场“竞技赛”中的所有选手,都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资格。换句话说,在以分数为依据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分配的过程中,首先界定了参与分配的成员资格。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成员资格界定会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或利益冲突,即存在着不平等的邀约。
1.高考成功者与“缺席者”间的邀约冲突
从古代科举制到当今的高考制度,考试已经成为决定教育机会乃至社会机会分配的重要途径。理论上说,考生只要参加了高考就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资格。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心智尚未成熟或者家庭贫困等各种内外因素没有充分开发学习潜能或未能坚持到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两种不同的“缺席者”),高考就成了一场不平等的邀约。原因在于,高考在连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同时,实际上也预演性地使个体的出路或命运与社会职业岗位的继替和社会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关联起来。有鉴于此,我国高考不仅是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的重要教育问题,甚至还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政治,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2]。
事实上,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稀缺性和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优质高等教育的稀缺性都强化了入学机会排他性竞争在教育筛选和社会筛选中的深远影响。它意味着:一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须以其他一些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无法获得同样的高等教育机会为代价,这种差异性高等教育机会通常会传导到社会竞争中而使社会竞争不公平甚至由此放大不公平的社会后果。有鉴于此,高考的教育筛选和社会筛选作用才被人们夸张地称为“一考定终身”。这种言说肯定了高考对分配高等教育机会和预演分配社会机会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隐含着高考实际上难以避免地充当着众多利益相关者教育机会争夺和社会利益争夺的制度性工具这一尴尬事实。正由于高考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与高考成功者相比,高考缺席者不但失去了平等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伴随着失去部分社会资源并潜在影响与之相关的社会成长。概而言之,高考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但不同的人很可能接受的是不平等的邀约。
2.高考正当性与选拔科学性间的认识碰撞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高考是以分数论英雄的。这意味着高考的每一分在理论上具有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同等力量,并以此彰显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高考的社会意义已经超出了教育考试制度的范围,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关联。有鉴于此,每次高考改革都会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大事,每年高考日、分数公布日等与高考相关联的重要时刻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77年高考恢复时,那些希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样的,以“白卷英雄”张铁生①为代表的、希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但没有良好的书面考试竞争条件的人,则对以书本知识作为选拔人才主要手段的高考制度心存不满,张铁生甚至在开卷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上写了一封信。该信后来被《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张铁生则被解读为“白卷英雄”。这些看似向度相反的事件背后,其实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一旦高考由高等教育的入口选拔问题演变成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时,高考应当倡导何种公平的问题就难以回避。对于那些在关键性考试中发挥失常,或者不擅长某些考试内容或某类考试形式的学生来说,他们确实无法有效获得与自身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以公正与科学背书的高考在实践中难免遭遇意外或失灵,故质疑或改革高考的声音无法杜绝。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替代高考之前,高考不失为最具可操作性的筛选工具[3]。这一点也被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革废的种种实践所证实。事实上,人们对高考或高考改革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改革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等操作性层面,因为从理论上说,高考试卷上的每一道题都可以给每位考生提供平等获取分数的机会,但不同考试内容和不同考试方式实际上对不同个体和群体而言,取得分数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甚至迥异的。换句话说,通过考试设计来合理分配高等教育机会崇尚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理念,体现了分数面前高等教育机会的份额平等,但高考内容和方式很难避免让部分群体占据优势却令部分群体面临挑战甚至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即分数虽然意味着平等的份额,但不同群体在具有同等资格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着不平等的邀约。
(二)平等的等级与差异性的机会:高等教育 接受者间的机会悖论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内部群体划分的不同,平等又分为了横向平等(即同一等级同等对待)和纵向平等(即不同等级不同对待)[1](P44)。尽管高考在形式上具有很好的公平性(这里的公平性侧重制度公正性),但高考结果实际造成了考生进入等级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而呈现巨大的差异性或不公平性(这里的公平性侧重结果的形式不平等)。
1.平等的横向学历与不平等的纵向认可
从理论上说,高考一旦成为分配高等教育机会和预演分配社会机会的工具,它必然会使知识(文凭)演变成一种能够增值和便于交换的资本,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间发挥效用。对家庭而言,高考成功与否对个人命运、未来社会资源的占有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并影响家庭社会流动的状况。它可以帮助中高阶层家庭免于家道中落,让中低阶层能够实现向上流动。对基础教育而言,高考成为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关键一环。于社会而言,高考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消除了先天因素的不公,主张天道酬勤。于国家而言,高考是一个招贤纳士的制度化机制[4]。
尽管高考提供了一个平等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台,但由于横向学历的存在,高等教育接受者间存在着机会差异。所谓横向学历,简称“学校历”,是指不同高校同一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历具有差异性的学术含金量或社会认可度,从而使不同学校同一层次的学历具有纵向化特征;与此同时,不同专业由于竞争程度和薪酬回报差异,也会出现横向学历的纵向化特征。高考分数从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或接受高等教育在选择学校、学科和专业方面的机会差异,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了未来的职业选择或社会机会选择。
横向学历尽管在外在形式上看似平等,但人们的关注重点往往是不同高校同一层次文凭的实际含金量或社会认可的含金量。换句话说,我们使用横向学历的时候实际上常常侧重的是其纵向化特征,也就是不同学校同一层次学历的含金量差别。这一差别将会在就业市场中被放大,使社会普遍认为具有更高含金量的专业或文凭呈现更大优势。我国用人单位越来越偏向于看重第一学历就是横向学历纵向化的典型表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承认高考实现教育筛选和预演社会筛选的公平性或制度公正性,并由此确认第一学历的纵向化特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高考成功地把部分学生筛选到不同层次或类型的高校,在高校通过进一步的选拔使大学生出现纵向分化,从而形成完整的纵向学历①结构。高等教育的纵向学历以及广泛认可的横向学历纵向化,使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学历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出现更加复杂的关系。高等教育学历既体现了教育和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同时又可能强化了社会不平等。
2.扩张的文凭热度与分化的正义诉求
我们可以从高考报名率(当年高考报名人数/18岁人口数)的数值变化来反映大众的高等教育热情。1978年至1998年间,高等教育还属于精英教育阶段,高考报名率仅维持在18%以内。1999年至2009年间,大众积极响应高校扩招政策,高考报名率猛增至48%上下。2010年至2020年,大众升学热情依旧持续升温,2015年后高考报名率从50%一路增长至60%以上[5]。究其实,是高考确实能够帮助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公正分配,高等教育学历则预演分配社会机会。就此而言,高等教育接受者接受的知识、获得的文凭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或能力证明,更成为了象征个人身份地位的符号资本。处于分层化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人群渴望文凭的符号功能助其获得精英标签并以此区别于中低端高等教育接受者,而中低端高等教育接受者渴望文凭的符号功能给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应有的符号权力。如此,作为社会符号的文凭,就越来越需要在精英正义(作为表征精英地位社会符号所彰显的正义)与生存正义(作为职业社会筛选符号所彰显的正义)之间做出必要的平衡。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前途应当向才能开放,那些才干和能力处于同一水平,有着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最初地位是什么,亦不管他们生来是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6](P68)。高考这一制度实现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以分数作为个人天赋和努力的量化指标来进行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尽力排除了社会出身和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显然这种制度设计是具有正义性的。但高校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或等级划分,劳动力市场在选择人才时也将学历视为个体拥有的知识、才能和技术或发展潜力的符号标识。就这样,高考不但成为了基础教育竞争的终点,也预示着高等教育竞争的起点和未来社会竞争的立足点。
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稀缺性加剧了高考竞争的严酷性。精英们不得不一再追求更高的身份资本,而普通大众也纷纷朝着精英的目标奋进,从而使人们普遍陷入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漫漫征途。那些没有较好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个人或家庭,往往难以经受得起这种长时段的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值得指出的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考报名人群中出现了一部分复读生群体。这部分人不甘心输在高等教育的起跑线上,追求精英教育资源成了他们复读的主要诉求。然而真实的事实是,在花了更大代价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最终不得不输在中途或者终点。
这种看似怪诞的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着行动的合理性。如果把竞争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比作享用美味的蛋糕,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这样的图景:有些人只能获得一小口蛋糕,有些人能够获得一个薄片,有些人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蛋糕,有些人还能够获得抹上奶油的完整蛋糕,有些人可以获得抹上奶油的完整蛋糕外加餐巾纸。而那些早早远离教育场域或者没有参加高等教育竞争的人,最多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是这样,教育是否能够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7]。
(三)平等的群体与不对等的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悖论
高等教育纵向学历的存在尽管意味着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接受者之间的不平等,但如果这种学历形态确实是形式上开放而竞争规则公正的背景下形成的自然结果,人们往往能够默认其公平性。原因在于,它的存在虽然没有消灭甚至制度性地确认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接受者在教育机会和社会机会上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结果确实体现了学历群体划分规则的公正,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结果不公平不会否认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程序的正义性。然而在现实性上,不管是纵向学历还是横向学历纵向化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人群属性差异(如人群的地域或民族差异等)。有鉴于此,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应该确保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以最大限度彰显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