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第二只看得见的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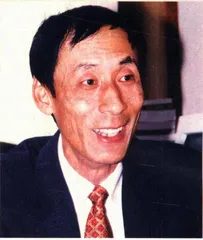
秦晓,山西人,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获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高级经理培训班毕业,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曾任中国石油部国际司副司长,亚洲卫生公司董事长,中信澳大利亚公司董事长,中信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等职务。曾由国家领导人提名,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太平洋工商论坛。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旨演讲人。
罗:你在许多场合,包括一些国际讨论会上提出:现代大公司、大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二只看得见的手”。这种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否想说明,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中,除了政府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现代大公司和大企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秦:亚当·斯密将市场价格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作用称为看不见的手。凯恩斯则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时候,提出运用政府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使经济复苏。从那以后,关于两只手的功能和作用就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争论不休的一个课题。
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本世纪以来现代大公司的出现引起了市场结构的变化。所谓大公司,在中国就是指能够控制国民生产总值60-70%,占国家税收70-80%那几百家企业。
传统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黑箱”,假设它是理性的,会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对于企业内部的决策程序和方式不关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提出的交易理论,使企业开始被视为一种组织形态,它和市场一样,是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方式都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就产生了组织和市场的互相替代运动。现代大型企业的出现不仅是规模经济的要求,也是人们寻求运用组织配置资源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努力的表现。更准确地说就是用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纵向行政组织取代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横向市场交换体系。组织和市场的区别是靠行政方法,还是靠价格信号来运作。所以相对于政府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第一只看得见的手,我称这种企业组织行为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是“第二只看得见的手”。
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界、企业界和决策界都有一种模糊认识,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削弱行政手段,扩大市场的单向过程。比如邯钢经验,它的核心是企业核算。企业不搞核算不能乍存。很多人认为这是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企业确实应该从各个方面去适应市场,但如果把市场机制完全引入企业,实际上又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瓦解和破坏,使企业不能发挥原来利用组织替代市场产生的效益。企业组织内部完全可以不用市场价格,因为它最终寻求的是整体组织的最优。它不用看每一个子公司或每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效益如何,而只需要保证整体效益。如果每个单位都按照市场价格去做的话,它当时没有必要通过兼并或者别的手段把这些单位组织起来,没有必要使自己不断变大。
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共享的资源被分割,造成一些企业孤军作战,或独自建立本应共享的体系,这显然是不合理、不经济的,甚至是种倒退。大公司总部通过大量组织行政手段在内部实施资源配置。所以说,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两只看得见的手在运作。在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重视第二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把中国改革的实质归纳为一种资源的有效配置,一种合理激励机制,最终是一个产权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不能有效配置资源,不能很好解决产权问题,而比较起来,市场经济更有优势。这种说法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不全面,不准确,甚至有误导。我们说到资源,不仅是指生产资源,还应该包括组织和文化资源。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国外发生的许多事件可以用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波音”兼并“麦道”,在美国国内也许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利于垄断,而不利于市场竞争。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这个行为却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如果说改革是通过寻求一种新的机制来配置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话,那么它也要对原有组织资源去进行重新配置和刷新。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没有组织资源,问题是我们在一种新的历史进程中,要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组织资源如何配置。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跨越,它的组织作用不可小视。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提出鼓励大公司出现和鼓励公司兼并,很多还是从效率和生产的角度来认识的。而这实际上是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实质中包含这样一个应有之义,即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并能够自觉地改造我们原有的组织系统,我们会更清醒。
无论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和突破,还是对中国改革实质的认识,提出“第二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都是有意义的。当然,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人为地拼凑企业组织则会违背市场规律,也要受到惩罚。所以,“慎用看得见的手”是一句值得铭记的忠告。
在“亚洲经济奇迹”中,一些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国际化,就是由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来联手运作。这些国家的大公司和政府之间有特殊的配合,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许多故事可讲,有许多案例可说。
罗: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经济生活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恰恰是存在太多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配合,或者是交易。不能充分市场化的种种行为,导致了过多虚假信号和过多的经济泡沫。
秦:他们的批评有合理成份,但不完全对。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的经济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叫FM(Free Market)自由市场,凯恩斯时代的叫SM(Simulating Mar-ket)模拟市场,东南亚国家的叫GM(C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东南亚国家采取这种驾驭市场的方法,有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亚细亚文明的农耕国家,崇尚权威,习惯统一组织的发展方式。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后发展国家必须通过某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组织资源。市场确实是优秀组织方式,但即使是在发达的市场机制国家,市场的发育都是一个自发的、漫长的、痛苦的过程。沿用西方国家的市场手段,明摆着难以形成足够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后发展国家面临的环境,显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同。实际上,在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下这条路对后发展国家是否走得通还是一个问号。当然,“看得见的手”是一柄双刃剑,使用不好就要付出代价。“泡沫”和金融危机,都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使用不好的代价。但是不能说东亚国家当时选择这条道路是没有原因或者完全错误的。
罗:新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之后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将中国经济在今后几年中继续保持8%的高速增长放在首要地位。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看法?
秦:你来之前,我刚会见了美国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银行的首席战略分析家Botton Biggs。最近,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8%的增长率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很重要,但外国投资者并不那么看重,而是更看重中国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软着陆”。一般来说,经济高增长往往同时出现高通胀,政府为了遏制通胀率,采取提高利率、紧缩财政货币等政策,最终引起经济衰退,这叫“硬着陆”。如果通胀率降下来了,又没有发生经济衰退,就叫“软着陆”。应该说,中国自1994年以来,已经逐步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软着陆”。那么,Botton Biggs说的“软着陆”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增长中减少泡沫,改善结构—中国经济第二次软着陆》。我想说的是,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经济现象,不仅难以长久维持,也不可能把它当作一种目标模式来追求。我们应该看到,低通胀的出现,不仅仅是适度货币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也是市场供求发生结构性变化,买方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反映。有效需求不足,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出现的“低通胀”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意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应有足够的认识。
从深层次看,中国的高增长仍是粗放的,外延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以结构恶化、效益下降为代价的。1998年把增长指标定为8%,主要的考虑也不是抑制通胀,而是为了减少失业的压力。那么为了实现8%,政府就要增加基础设施等公共开支的投资,这势必引发通胀的一定程度的上升。
要知道,高增长是一定有代价的。增长积累的时间长了,就出现萧条。自凯恩斯提出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使经济复苏之后,这种周波现象更加明显,高增长、高通胀交替出现。经济界的共识是:双高从来互为因果,互为代价和制约。这个观点至今没有遇到过挑战。到70年代西方经济发生了滞胀,就是高通胀加经济衰退,这是把以前经济增长的代价全表现出来了。这种最坏的组合加上石油危机倒也变成了一件好事,逼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大规模调整结构。大约用了十年,走出低谷。到80年代变成了低增长(4%),低通胀(4%),和低失业率(4%)。三个百分之四,一般叫双低。美国经济十年来维持了双低,说明它在这种模式中找到一条经济发展的路。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Alan Greenspan -天到晚盯的就是通胀率,只要各项指标预示经济过热,马上加息,一年加六七次息,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就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因为高增长后面一定会接着高通胀。所有国家中央银行,就盯一项指标—通货膨胀率,通过货币投放量控制通胀率,不能用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
总之,如果我们在经济增长中,已经实现了以降低高通胀为内容的第一次软着陆,那么,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把增长中的泡沫成份挤掉,同时使产业结构优化,我以为,实现这种意义上的“第二次软着陆”,应该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题。实际上还有第三次软着陆,就是在经济结构比较好的情况下,把增长率再降得低一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即从“高增长、低通胀”向“内涵式的适度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转换。 经济学宏观经济看得见的手企业经济中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