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之间:女儿的“一国两制”经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孟湄)
1997年,小女儿三岁,生日一过我们就跟她说好,秋天就要去上和哥哥一样的学校(北京法国学校的幼儿小班),高兴得她天天背个小书包拽着阿姨出门。
为什么不在秋天前把她送到我们胡同里的幼儿园?我和丈夫想到了这个主意。
胡同里的幼儿园很漂亮,在一座四合院里,院里有一棵很大很老的树。园长很理解我们,接受了女儿“插班”。因为担心孩子认生,我向老师提出让她先从每天去两小时开始,试一个星期,她的老师同意了。我们没想到第三天女儿就跟陪她去的阿姨说:“你回家吧,以后再来接我。”我们喜出望外,欢呼顺利。
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少东西,有时拿回家一些她画的图画,有“庆祝九七回归”的大红球,彩色方块,让我们大笑不已。幼儿园给人感觉极重视启发智力。我见过她的老师组织孩子上课做游戏,她说话的声调和电视里鞠萍阿姨竟然难分真假,园门口的宣传栏里还介绍孩子在本城区智力竞赛的成绩。
法国有位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曾经说:“中国的事情经常是把小孩当大人,把大人当小孩。”细想来是有这么点儿意思。
比如说,老师对我说女儿“有个缺点”:她早上进幼儿园不问老师好,怎么教也不行。老师说女儿不是不会说话,应该养成个好的习惯,女儿也真倔,愣是不开金口,过了第一个月,我碰到老师,她说,用整一个月的时间,你的女儿才说一句“老师好”,一整天别的不说,光是拿手比划自己的要求。老师说的时候,女儿听在一旁,回家的路上她自己告诉我她“就是不一爱一说”。
女儿小不点儿人,有自己的“爱”和“不爱”,我看见过一次全班孩子都坐在那里听故事,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到处蹓跶;还有一次老师在讲西红柿的形状和颜色,她偏是不理不睬,离开座位,把别的孩子没尝完的西红柿统统塞进嘴里;她的我行我素发展到吃饭只要吃老师自己带的饭,也有时候,她成功地让老师领她到幼儿园伙房:挑食。这是她告诉我们她喜欢哪个老师的时候透露的信息。

女儿在幼儿园,络肋胡子是老师
幼儿园有一件事,她特别地“不爱”。有一天,女儿跟我们说:“我不爱老师给我起名字,我不叫小混血儿,也不叫小老外。”我们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她说得不错,她是有她的名字。那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在家里爱玩儿打电话。她拿个玩具手提电话一次次拨号,一次次大声报告自己的名字。她不停地拨号,不停地报名字,我跟孩子爸说她是在给自己“摆平”呢。
她甚至喜欢经常使用“香港回归”这句话,除去她觉得这话好玩儿外,还有一个理由:解释她的名字,她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发“香”音,我们曾经告诉过她香港是她的出生地,她高兴自己有个美丽的现在人人都在叫的名字。
在胡同里的幼儿园两个月,女儿过得很愉快。她的自由自在和吃老师饭也许是“小混血儿”的特权,但我们很感谢老师给她的爱护和快乐。
秋天,女儿进了新幼儿园,新幼儿园房子的建筑不如那座有大树的四合院漂亮。与胡同里幼儿园的物质条件相比差别也并不大。让我们首先觉得不同的是老师想尽办法让孩子玩儿。玩的花样儿多:玩儿泥巴,玩儿沙土,玩儿颜色,玩儿纸,玩碎布头,还有出去玩儿。联系本上报告: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上午,带孩子们去北京的公园,翻斗乐,游戏场;美术馆和博物馆也领他们去。做为家长,我好几次被邀请给班里提供玩儿的材料:卫生纸的空卷筒,作衣服剩下的碎布,空酸奶筒,空冰激凌盒;也有好几次在孩子们出游前被邀请作老师的志愿助手;记得女儿的老师告诉我他终于知道在北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种适合孩子玩儿的泥巴;他还问过我可不可以帮他找到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参观的普通北京人的四合院,他说四合院印在孩子童年的记忆里会很有味道。
女儿进了这个幼儿同,好像我也跟着进了幼儿园。如果某汉学家说中国人把孩子当大人,我可以说我在幼儿园看法国人怎么把孩子当孩子。
新开学的家长会我因为出差错过了,一回到北京我趁着送孩子去跟老师作解释。老师是位男上,中年以上,络腮胡子,笑起来很和蔼:“遗憾您没有来,什么时候下课后您方便,我随时可以和您谈谈。”我终于挤出空,和老师见了面,他只用两句话介绍说小班第一年的教育:主要注重的是让孩子开始和习惯社会群体的生活,智力上给予一些启蒙。他谈的最多的是对女儿的注意:“这个小姑娘话很少,但是我发现她不是有什么问题,她其实很敏感,细致,也喜欢调皮,她有自己的主意。”
有一段时间,早上凡是我送女儿,她就爱哭.老师每每特地把她喜欢的小伙伴领过来和她玩儿,女儿就忘了哭;我跟老师说因为自己出差多,但只要可能,总想送女儿来,可是她偏偏哭,老师很温和地微笑,“还是送送她好,上学的路时间短,也可以和她分享许多,她需要慢慢理解你,也需要时间慢慢习惯你的节奏”。算是老师教了我一回。
又过了不久,我问老师女儿怎么样。老师回答说她没有问题,因为“她爱上了”,我问爱上了谁,“是班里一个最淘气的孩子,这一对儿小人儿,每时每刻厮守在一起,居然很和谐。”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孩子姥姥,她姥姥说“法国人想事儿真逗”。
这以后,关于女儿的“爱”,老师时有信息报告加上他的观察:
—她可真是个小中国女人,不爱说话,可却得让别人听她的,还耍耍赖,
—她耍赖,您可得说说她。我赶紧说。
—孩子有这么个年龄段:两到三岁,正是个开始喜欢说“不”的年龄,她开始喜欢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懂事还要等到以后。
—她太专情了,跟着她的小爱人不放,哎呀,女人呀,这样可不行,将来她会知道男人其实很脆弱的。老师看我听傻了,笑了笑,说这很看得出孩子的个性。
—这要是我们中国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为什么不?她喜欢上一个人,这很好,也很正常。我们知道孩子喜欢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再说要是没有爱,不被人爱,该有多寂寞,多难过。那样的孩子问题也多。
女儿爱把自己的新书带到幼儿园显摆。有一回正赶上我送她,小书包装不下,还得我替她拿在手上。老师看到了告诉我,女儿还曾经亲自把书塞到老师手上让他读给班里的孩子。老师不懂中文,只好把班里一向只负责生活的阿姨请来给孩子们读。他说女儿法文表达不如中文好,所以要给我们看她的中文水平。这是正常的。老师还说班里的孩子有好几种文化背景,混血儿多,他说这是孩子们的财富与尊严,要好好爱护和开发。
女儿和她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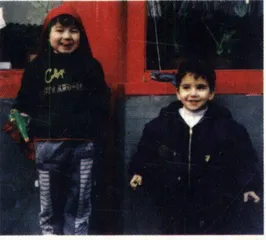
女儿的经验成了我们家里有趣的话题。孩子爸喜欢用法国文化人的口气作评论:“法国有蒙田,有卢梭,有伏尔泰,有弗洛伊德的影响,有拉冈(LACAN)精神分析学派,有儿童精神分析学家杜尔铎(F.DOLTO),所以……”听起来真是形而上,我的概括则是接近毛主席提倡的“由浅入深”,中国人喜欢让孩子乖,喜欢跟孩子说:“别人都不这么做,你也别这么做。”法国人待孩子是反过来,物质上并不娇宠,精神上百般呵护,注重和鼓励每个孩子的个性:“别人这么做,你也跟着做,有意思吗?”“可是,”孩子爸补充道:“别忘了同时要教给孩子:尊重别人,尊重别人和自己不一样,不打扰别人。”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7年,女儿像朵小花一样开了。她一反过去喜欢沉默的习惯,越来越多地咯咯大笑,越来越多地说“我觉得”,甚至“我自己去找朋友玩儿”。女儿让我们充满幸福。我们也感谢她给了我们“一国两制”的经验。 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