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艰难的诉讼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雅民)

1997年12月10日东京时间下午1时,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十三部在611号法庭第八次开庭,对中国劳工状告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鹿岛花冈绑架中国劳工损害赔偿要求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是:1.驳回原告方所有请求;2.诉讼费用由原告方负担;3.上诉期限定为60天。
此案源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一桩历史事件。1945年前后,一部分日本企业,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与帮助下,将38900多名中国人强行绑架到日本,分派到135个作业点做苦力。其中986名中国人被押至日本东北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在鹿岛组(即现在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逼迫下从事极其艰苦的河道改造工程。山于不堪忍受工头的残酷虐待,花冈作业所的中国人愤然暴动,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到日本投降时,花冈作业所共有418名中国人死亡,其余幸存者也都奄奄一息。时隔50年,以耿谆、王敏等“花冈事件”中死里逃生的中国劳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当年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东京地方法院受理这一案件。历时两年,此案究竟是如何市理的?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原告诉讼代理律师团成员川口和子和多年参与此案调查与诉讼工作的北京人士韩先生。
被告辩护律师宣称“花冈事件”属“战争行为”,搬《中日联合声明》作挡箭牌
长达308页的起诉书,是1995年6月28日,山耿谆、王敏等7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代表,直接送交到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书中详细叙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绑架中国劳工的历史,控诉了在战时经济体制下日本企业奴役和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在起诉书中,原告要求被告向当年花冈作业所每一位中国劳工赔偿550万日元。
1995年12月20日,法庭进行第一次庭内调查,审判长名叫圆部秀穗05名原告代表耿谆、王敏、赵满山、李绍海和死难者家属孙力,在法庭上陈述了当年惨遭迫害的经历。耿谆,河南襄城人,原国民党军第十五军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因腹、背等5处受伤被日军俘获,1944年8月8口被押至花冈作业所任劳工大队长,“花冈事件”后,作为“主犯”被关进秋田监狱,日本军警的严刑拷打使他头部受伤。王敏,河北深泽人,被日本特务机关俘获时任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花冈事件”中,日本监工把烧红的炭火摁在他的脚上,用木棒打碎他的手关节。他的前妻在老家遭日军枪击,身怀六甲而亡,第二个妻子不知他已被抓到日本,为寻找他变卖了所有家产。赵满山,河北保定人,当年与父亲赵义一起,以“私通八路”罪被捕。在花冈作业所,其父仅因开饭时提前伸手拿食物,便遭监工殴打,含恨而死,其本人也在“花冈事件”中惨遭毒打,门牙全被打掉。孙力,替父亲孙基武告状。孙基武本是一中学校长,被日军以参加抗日活动为由抓进宪兵队,受尽电击、灌辣椒水等酷刑。后来,他被押至花冈作业所,暴动时随人群逃进大山,日本军警把他抓回来,强迫他与其他劳工一起,在共乐馆前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结果还是被军警用木棒打死。
但是,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人却没到法庭,仅派宇津吕英雄、伴义圣等4名律师在法庭上听证。当审判长询问被告律师有何问题时,对方递上一份极其简单的“申请驳回”的书面报告。其内容是:1.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2.诉讼费用让原告承担。为何驳回?报告书中连理由都不讲,只是说:“如果法庭需要的话,可以写出申请理山。”审判长当即要求被告出示驳回理由。
1996年2月19日,法庭举行第二次庭内调查。被告律师宇津吕英雄向法庭以书面形式递交了“申请驳回”的理由。其理由如下:1.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签订的《中日邦交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也就是放弃了索赔权。当年的劳工问题属于战争行为,责任在于国家,不能找企业算账,原告无权再提索赔要求。2.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也应是一种国家行为,应由政府来决定。现由法院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尤其是由某一法官来处理这一问题,显然是不适当的。3.时效性问题。日本法律规定:有关侵权行为的索赔案件,有效诉讼期为20年;有关不履行债务案件,有效诉讼期为10年。有效期以案发时间开始计算,“花冈事件”时过50年,早已超过了有效诉讼期,法庭应该驳回原告的请求。
第二次开庭时间不长便告结束。由于法官认为被告的第二“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律师不予考虑。
原告律师的辩护:企业的罪行不容回避
首先,原告律师团拿出重要书证,向法庭说明这是一桩民间民事赔偿案,不涉及双方政府,《中日联合声明》中所提到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不包括中日民间的民事赔偿案。例如,1995年3月6日,在全国人代会上,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回答台湾省代表刘彩品的提问时曾说:"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没有放弃民间的被害赔偿请求权,索赔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中国政府不能阻止。”同年,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借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之机,再次说明《中日联合声明》中所宣布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针对国家政府之间而言,不代表民间团体或个人。新美隆等律师因此在诉讼书里就很有把握地写道:“根据近来中国政府的见解,中国政府在原告们要求被告赔偿的问题上,表示应该得到赔偿的立场十分鲜明。”
接着,原告律师团又以大量人证、物证及书证,说明“企业在侵略之中犯下的罪行,必须由企业自己负责,不能把政府和军队当做逃避罪责的隐身草”。
原告律师团在书面材料中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线拉长,物资紧缺,日本内阁推出了“战时体制”,并明确规定:在战时体制统制经济下,只要企业的营利性与国家的生产扩大相一致,就会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奖励。“鹿岛建设”在日本土木建筑行业是屈指可数的代表性企业,在土木建筑团体中一直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柳条沟事件(即九·一八事变)后,“鹿岛建设”迅速成立“满洲鹿岛”,承接满铁及关东军其他一些特命工程,尔后又深人中国华北,为掠取中国资源承包了大同煤矿开发等系列工程。同时,“鹿岛建设”在日本本土还承包有东海军机场掩体建设、中岛飞机地下工厂和花冈川改造等重大军需工程。
面对庞大工程量,到哪里去找劳力?“鹿岛建设”的目光瞄准中国劳工。战争初期,日本企业就已经开始绑架朝鲜人到日本作劳力。
谋求“移入”中国劳工的企业,远非“鹿岛建设”一家。1939年7月,日本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在给日本厚生、内务大臣的一份“请愿书”中,就曾开门见山地说:“察全国范围的劳动力不足绝非姑息之方可救,愚见以为除自‘支那’(指中国)本土移入劳工之外再无解决之策。”此头一开,各行业团体争先恐后,要求政府“移入”中国劳工。随后,以“鹿岛建设”为主的土木工业协会也就“使用‘支那’苦力问题”,向日本外务、厚生省提出了要求。1942年,日本企划院向土木工业协会咨询劳务来源的问题,得出“役使华人作为现在的劳务来源最为合适”的结论。新美隆说:“由此可见,绑架中国人来日本做工,是在日本企业对政府反复‘请愿’以及企业研究探讨之上得以实现的。”

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推出“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案”的内阁决议。当年,日军在石家庄、济南、北京等地集中营都挂有“俘虏集中营”和“劳工教习所”两块牌子,日军经常外出“扫荡”,进行以“狩猎劳工”为目的的讨伐作战,除军人外,将老百姓也当作俘虏押进“俘虏集中营”。日本企业前来取人时,要向驻军、即所谓的“华北劳工协会”交付一定的费用,每位劳工35日元,犹如买卖奴隶一样进行交易。
战后,“鹿岛建设”曾向日本有关当局提交过“华人劳务者供出状况报告书”,对第一批、也就是有耿谆、王敏等原告在内的那批劳工的供应状况,写出如下报告:“1944年7月21日,在北京万寿山训练所,在军队和协会在场的情况下,着手从最初400人中选出300人的作业。整体来说,体质不良者占绝对多数,严格选择的结果,只剩下130人。通过交涉,又从提供的200人中选择100人,仍然没有达到300之数。于是,再次请求调拨100人从中挑选,好不容易得到批准,才选够了预定名额300人以及预备的15人。尽管这300人是从700人中选了3次才定下来的,但总的来说,体质劣弱07月25日上午8时,全体300人,在企业方面4人、办事处职员10人、更生队员12人、皇军6人的陪同率领下,离开集中营徒步到清华园车站……”原告律师查到了这份文件,把它出示给法庭。新美隆说:“这就是急于获得所要数目的鹿岛与.劳工协会(实质是当地驻军)履行‘合同’的过程。事实证明,包括被告在内的许多日本企业,在强行绑架中国人这件事上,是经过了周密算计,并且主动、积极地加以实行的。”
“花冈事件”后,日本仙台俘虏集中营所长,在给俘虏情报局长的报告中说:“关于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旧称)华人劳工暴动案的动机原因:1.劳务过重。原本每天10小时的作业时间,到了6月20日,号称全县一齐突击作业,延长两个小时,变为12小时,而对此没有增加伙食;2.粮食不足。尽管劳工粮食泛,食不果腹,但鹿岛组干部似有私吞一部分主食的迹象。3.华人受的是牛马般对待。作业中稍停一下,就要挨打,劳工们天天遭受殴打,这么说并不为过。”这份报告战后曾被审判日本战犯的日本横滨军事法庭作为证据而采用,所审战犯不是日本军警,而是鹿岛组在“花冈事件”中的几位监工。最后,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川和清水被处以绞刑。新美隆律师说:“鹿岛组的干部、职员对中国人的暴行、虐待,绝不是独立的个人的个别事例的简单组合,而是鹿岛组企业为猎取利润而进行的一整套有组织、有系统的经营行为。横滨法庭所做的严厉判决,实际上也是对被告本身的一种审判。无需赘言,鹿岛组对.上述非人道的不法行为,还要负使用者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律师提出这样两点反驳理由:
第一,法律的制定,应是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符合人道主义。例如规定“有侵权行为的赔偿案件20年后失效”,应是针对被侵权人明知自己被侵害、在长达20年内有充裕考虑问题的时间、并且有能力向法庭起诉而却没有起诉的行为。但对中国劳工来说,战后中日两国曾经长期没有外交关系,互无往来,作为普通老百姓,如何能够到东京来起诉?中日1972年建交,这时早已过了“时效”所规定的20年,这一责任,不应由中国劳工承担,否则就难以再说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受害者。
第二,1989年12月22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曾发表一封致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公开书简,其中提出3项赔偿要求。双方多次交涉、谈判后,1990年7月5日,以耿谆为首的中国劳工代表与“鹿岛建设”代表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中国人在花冈矿山作业所现场所受苦难,是起因于根据内阁决议所进行的强行绑架、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承认这一事实,认识到自己负有企业责任,向当事的中国人及其遗属表明深切的谢罪之意。”原告律师认为:如果说原告是因为诉讼时效问题而丢失了索赔权的话,那么在被告于1990年7月5日仍然承认“负有企业责任”这一天起,原告就又重新获得了索赔的权利。
法官:应付差使,不按常规允许答辩,拒绝审理
韩先生说:“我始终期待着法庭上双方律师激烈辩论的那种场面,可惜始终没有看到。法官圆部秀穗就像是应付差事一样.以至每次开庭用不了几十分钟,有时甚至是十几分钟便草草收场,所谈内容,迟迟不提实质问题。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法庭上,问题的提出与反对,应主要是在双方律师之间进行,但在审理此案时,原告提出问题后,法官经常是不按常规让被告律师答辩,而是直接就给回绝,以至被告律师无事可做地坐在法庭上。”
原告律师团律师川口和子也有同感,她说:“法庭上有35个旁听席,每次开庭都坐满了人。审判席上有话筒,但这位法官从来不用话筒,说话声音很小,像是怕被人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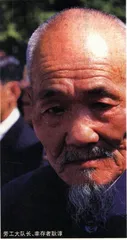
1997年2月3日,法庭举行第七次庭内调查。下午2:20开庭后,法庭内突然增加了许多法警,平日仅有3位,这一天却多达13位。审判长仍像以往一样,不紧不慢小声地提一些问题,问双方各自准备的证据如何?双方律师各自出示证据,各自研究如何对付对方所提出的问题。突然,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开庭后仅15分钟的时候,审判长忽然拿出一张字条,先是说:“那么现在说一下法院的看法。”然后便一口气地说:“驳回原告申请审查证人,结束辩论。关于判决日期,以后再通告。”说完便宣布退庭。
“难道这就结案了?”原告的律师及旁听席上的人们都惊呆了。
原告律师团说:“这样的审理,不仅仅是不充分的审理,也是国际法上的拒绝审理。如此损害诉讼程序,不能不让人十分怀疑是在正常的诉讼程序之外有其他考虑或意图。”
圆部秀穗终止审理的当天下午,原告律师团即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该审判长回避此案的要求。同时,在东京律师会馆,新美隆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法官这一极不公正的暴举。1997年2月5日,即终止审理后第二天,原告律师团又向法院递交了《申请审判官回避理由补充书》,再次强烈要求法院撤换审判官,重审此案。
可惜,要求审判官回避此案的申请被驳回,圆部秀穗仍然主审此案。不仅如此,1997年12月10日,法庭终于就此案作出了令人深感震惊的一审判决。
历时两年多、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诉讼,川口和子律师告诉记者,原告律师团以新美隆为首的18名律师对此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知道,此案状告的虽然仅是“鹿岛建设”一家企业,但其结局将涉及战时整个劳工问题。据日本外务省在一份《报告书》中提供的数字,得知当年共有38935名中国人被武装绑架到日本,参与绑架并奴役这些中国人的,除了“鹿岛建设”外,还有“三井”、“三菱”、“铁工”、“地崎”、“日铁”与“北炭和平”等许多大企业,“鹿岛建设”在此案中的胜负,无疑将关系到其他诸多企业的利益。此外,日本当年所抓的万千劳工,不仅只是中国人,还有朝鲜人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牵一发而动全局,一旦“花冈事件”的劳工们索赔成功,势必还会有同类的诉讼出现。
1997年12月12日,即一审判决宣布后的第二天,中国“花冈事件”的劳工代表耿谆、张T国、孟繁武和赵满山,在以新美隆等日本律师的陪同下,已经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上诉,强烈要求高等法院正视此案,撤回地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但他们对东京高等法院的态度已不作特别大的奢望,因为他们毕竟只代表“花冈事件”的中国劳工,他们在强大的法律机器面前实在势单力薄。 律师咨询法律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