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信片:《泰坦尼克号》:20世纪的“少年往事”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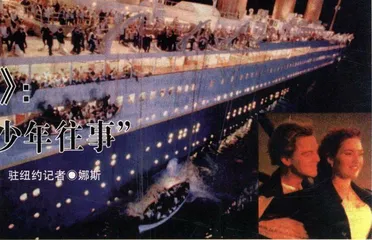
有天,看一篇文章说,1997年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危克号》让女人哭,《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让男人哭。搞得我直紧张,因为我看前者眼睛呈干燥状,看后者倒“热泪盈眶”了一番(跟电影好坏倒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早就发现我看电影掉眼泪总掉得不是地方,也许我这人有防范心理,大张旗鼓造势对我没什么作用,得“旁敲侧击”,“·出其不意”之类的。而《泰坦尼克号》的风格,恰恰不是机智和微妙。它追求的是一鼓作气、简单、明了的情理之中,以电脑时代的最新技术重塑好莱坞的传统辉煌。
集体潜意识
大众文化中风靡一时的“事件性”作品,总归要触及某种深层的集体潜意识。比如解冻时代的中国流行邓丽君,80年代末的城市青年与崔健的《一无所有》。电影史上,《泰坦尼克号》的前辈们如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都诞生于人类初人太空的兴奋年代,《侏罗纪公园》源于我们这个年代DNA技术引起的想象与惶惑。《泰坦尼克号》浪漫历史电影前辈《飘》则是南北战争。
《泰坦尼克号》呢?听说有位中国名导演讲:“搞不懂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电影!”我倒搞不懂这位导演了。这电影有动作特技让楞小子们过瘾,有金童玉女浪漫爱情让少女们刻骨铭心《帅哥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更是女孩心目中的“万人迷”),有一直引起话题不断的历史真事,有豪华场面让人眼花缭乱,十八般武艺样样熟络,且大大方方。如果不把这叫雅俗共赏,你还能把什么叫雅俗共赏?
当然,就题材本身而言,西方观众有些“情结”性的东西,或许是与我们略为隔阂的,这也就是我说的所谓“集体潜意识”。我在看到这部兴师动众的电影之前,读了美国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一篇讨论有关“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各类书籍的评论文章,才使我对这以前从没太感过兴趣的问题有了点概念—
“泰坦尼克号”1912年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建成,重46328吨,9层甲板,整艘船耗资750万美元,双层船壳,16个防人水分隔层。这只“巨无霸”被铸造者称为永不沉没之轮。然而,1912年首航,次日就触冰山,3小时沉没。
“泰坦尼克号”头等舱套房收费4350美元,三等舱30美元,刚好差145倍。头等舱分意大利式、文艺复兴式、乔治亚式、现代及古荷兰式等,还有划艇、自行车、电动马等器材的健身房,泳池、理发店、咖啡厅、吸烟室等一应俱全,其豪华空前。
之所以引述这些东西,是因为它反映着我们这个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兴旺发达时代的高昂的时代心理,或者你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物质积累的兴旺期。总而言之,西方文明的20世纪,始于兴高采烈,信心无比—一如“泰坦尼克号”的启航。科学的进展,机械的发明,钢铁轰隆,声光电影,巨轮渡海,火车过山……然而这一派兴高采烈迎来的却是对“泰坦尼克号”而言的撞冰遇难,对文明而言是两年后爆发的大战。对彼时人们的心理震撼可以想象。“泰坦尼克号”的豪华,“泰坦尼克号”的等级结构,都是世纪初文明的凝聚与写照。它的故事,太容易被人看成某种象征性的预言。
约翰·厄普代克提及的书里,有本讲“泰坦尼克号”反映的文化历史。最初,媒体的报道充满对上流社会的颂歌—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该是“统治阶级自我粉饰”。“泰坦尼克号”的确又满载了各色富豪显贵巨头华妇—他们之中,又的确不少随船遇难(阿斯特、古根海姆等等-鼎鼎大名的姓氏)。媒体在对一等船民歌功颂德的同时,又对下层乘客、异族等横加丑化,说他们如何“慌张,懦弱”。然而统计数字显示,一等舱男性乘客31%幸存,二等舱10%,三等舱14%,总的来说一等舱乘客60%幸存,二等舱44%,三等舱25%。
除了反映“阶级对立”之外,当时的宗教团体则趁机搞宗教宣传,左派报纸杂志则有沉船与“成千上万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深火热生不如死”相比不过是“很轻的悲剧”而已。
到了50年代,一本讲“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小说《难忘的一夜》成了畅销书。战后的人开始回过味儿来,对“泰坦尼克号”加注“新说法”。“象征爱德华时代……对山富贵阶级率领的一个文明的信心的结束。”“接下去的无休止的幻灭感不能只归于“泰坦尼克”,但它是第一个跌宕。在“泰坦尼克”之前,一切平静,在它之后,一切骚动。”
厄普代克认为上面提到的一书对“泰坦尼克号”事件木身缺乏叙述,更多的是书卷气的解读。有关事实本身的书,除了《难忘的一夜》,他介绍了《泰坦尼克:一个梦的结束》。这本书提供多方幸存者的叙述,让人触目惊心。尤其是,慌乱之中没装满人的救生船除一只外,无一返回救人,留下遇难者漂浮冰海,多数不是淹死而是冻死。
“泰坦尼克号”的戏剧性沉船经过自然少不了故事家趋之若鹜。1997年,关于它的小说就有3本,有以男主人公为视角的成长主题小说,有把“泰坦尼克”跟希腊悲剧联系起来的—“泰坦尼克”这名字就寓意非常。“泰坦尼克号”事件充满致命性的非常规因素:它为了躲开冰山掉转方向,反而侧面划过冰山而进水—专家们认为如果迎头撞上冰山倒可能没事(当时好几起撞船事件都是例证);如果船上的瞭望台备有双筒望远镜,船员或许会早望见冰山;如果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号”没有关掉无线电;如果“泰坦尼克”不是新船,连救生艇演习都没有过;如果救生艇更多……厄普代克总结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就像27个月之后的世界大战,悲剧性地可以避免。它是人们滑人的一场灾难,因为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无懈可击和正直。然而,它的令人敬畏的宏伟之感却并不容易在虚构叙事中体现出来。阅读关于船上发生的故事,这好像坐观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热身部分,等着明星—撞船—出现。……“泰坦尼克”故事的庄严教训仍然存在:关乎人,没有什么是不可湮没的(Nothing human is unsinkable)。”
好莱坞版本
正如厄普代克指出的,泰坦尼克号故事也许不适于小说—它的视觉能量也许更适于电影(更接近厄普代克所说的摇滚音乐会?)。詹姆斯·喀迈降的热身节目,是先经营一个充满宿命感的梦幻爱情,让观众卷入。他当然深知,观众事先卷入得越深,对当事者的感受才越近,沉船时的效果才越强烈—光是逼真的特技还不行。这个效果,他当然是达到了。
《泰坦尼克号》票房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它把好莱坞两种类型片方面的传统合起来—动作片历险片加浪漫史诗—加以新技术包装。詹姆斯·喀迈隆是拍科技动作片的高手。他的《魔鬼终结者II号》、《异形》第二集都是有点说头的娱乐品。这两部电影里,还都塑造了“身如铁,志如刚,艺高人胆大”式的女英雄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好莱坞动作片多是男人为主角,女人做花瓶,007系列是典型例证。《泰坦尼克号》的核心故事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的“倾船之恋”,一个她因之而获得解放与重生的故事。统计表明,这对破票房纪录大有帮助。罗丝的故事,起着牵引观众情感的作用。它也讲英雄救美,但它是从女人角度来讲—当然,对男人并不少恭维,讲得男人心情舒畅,讲得女人心醉神迷—加上两位男女明星外表气质演技不俗,凯特·温斯丽融波提切利式古典美和现代女孩奔放自然于一身,迪卡普里奥虽然婴儿脸但是收放自如……
《泰坦尼克号》的另一个成功张力是:它一方面精心筑造世纪初旧日文明的豪华场面,满足我们的幻想,一方面又对上流社会无情讽刺,充满道德批判(头号坏蛋就是个没心没肺的阔少),对劳动人民热情讴歌—杰克和罗丝,好莱坞版本的“保尔与冬妮亚”?对今日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如果马克思还在,该有些新说法。
演《泰坦尼克号》男主角杰克·道森(典出杰克·伦敦?)的迪卡普里奥虽然走到哪里都让少女们尖叫混乱不已,在《泰坦尼克号》之前却偏爱做性格演员,一直拒绝当偶像,演技也的确不俗。可是自从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不想当也不成了。据报道,导演苦苦劝说了他三个月才把他拖上了“泰坦尼克号”这条船。他仍然宣称这类角色不合他本人口味,还在拍片过程中不断问导演:“就不能给我稍微加点缺点?”导演却说:“不行,我就要你是罗丝生命中的一道光!”
的确,《泰坦尼克号》中的很多人物是单音符的—罗丝的那位未婚夫更因表演夸张而被称为仿佛默片电影里跑出来的坏蛋。的确,它台词写得太次。的确,《泰坦尼克号)讲的是通俗故事,它是成功的商业艺术,是好莱坞工艺水准的一流体现,但是可以说,喀迈隆那种大男孩式的、热情洋溢的电影发烧友性格(人称一人电影制作军团—制片、编剧、导演、剪辑都包办),反而让它有种不俗。他为了拍摄“泰坦尼克号”残骸镜头投人的是宗教式狂热。他选取的讲故事的角度也帮了他不少忙—回忆式的叙事与现代人的聆听与想象,给这个故事的虚拟与真实成分的结合提供了最有效的切人角度。它告诉你,这是一个老太太讲的故事,也是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故事,这对它的真实与否有了一种自我解构,也使故事更顺理成章。回忆式的叙事也使它获得了一种世纪末与世纪初的观照—老太太成了这个世纪的象征,回望她的天真时代。这种主观方式更为电脑大显身手提供了空间—影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那些非电脑不得其成的、时间与空间同时变幻的意识流镜头。电脑技术在这里可说是用得恰如其分,而且用得挥洒‘灵气’,提供只属于电影的视觉盛宴。
我的朋友都诧异—这人不是刚还在抨击奥斯卡大片,整天看小电影吗?怎么又讲起《泰坦尼克号》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所能回答的。
最近我正好读了影评人宝琳·科尔多年前的一篇电影随笔,叫《垃圾·艺术与电影》,对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电影的伧俗一面、商业与艺术、大众与小众都有精辟之见,最符合我现在对电影的认识。电影是什么?电影是艺术,电影是工业,电影是商品,电影是技术,电影是娱乐……没有单一的定义。宝琳·科尔给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有太多的艺术形式构成电影,它不是适合纯粹主义者的艺术。拒绝承认电影文化中由人性本身决定的伧俗一面的存在,恐怕不诚实也不现实。电影可能就是同时由垃圾和艺术充斥的一种文化,如果我们拒绝任何垃圾,恐怕干脆就对电影不必有兴趣,因为在很多垃圾电影中可能有那么点儿艺术,在很多号称伟大的艺术电影中,也可能有很多的“垃圾”。我们为什么去影院?享受、解闷、做梦和好奇—恐怕是我们所有人去影院的最初的原因。只有当我们阅历渐多,见识更广,看得多了以后,才会感到我们对重复的不耐烦,我们需要点不一样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人永远是少数,因为还有下一拨大众,还有更多的人习惯于模式,满意于传统。所以,有一些电影只能是小众的电影,但是大众电影的存在,永远是每个人的出发点。《泰坦尼克号》是一部大众电影,但这不是我们对它作判断的唯一理由。 少年往事泰坦尼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