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香港制造》:独立制片的一个标本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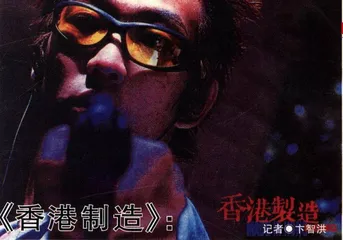
没有一家电影公司会预见到《香港制造》的成功—它在1997年摘取了一连串国际奖项:洛迦诺国际影展特别评审团奖、法国南蒂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奖……;仅在香港票房收入就超过200万元,韩国、北欧等地都积极购买了它的放映权。但在1995年陈果兜售他的剧本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商业性。”
因此,陈果独立制作了他的影片。作为香港一名资深副导演,两年间他悄悄积攒、购买了8万尺用剩的胶片,向朋友借贷50万港币,5个剧组成员无偿工作了4个月,终于在吃掉最后一个港币买的最后一餐盒饭之后,制造出这部(香港制造)。此后的20万港元宣传发行费则是由热心提拔新人的影视巨星刘德华提供。
或许正是这种艰难使整个事件显得激动人心。因为攒下来的胶片多数已过期,很多场景呈现出一种阴森森的青绿色,但偏偏效果极佳。两位主角都是非职业演员,在大街上拍摄也不会引人注目,反而像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作业。而且拍完戏后,他们会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比如男主角是从溜冰场找来的边缘少年,纹身,凹胸,穗状的染发,他从欧洲影展回来后依然彷徨失落,无所事事,唯一的转变是开始去读夜校。
3个公屋区少年的故事使影片稍嫌阴暗。中秋爱上身患绝症的阿萍,阿萍的父亲向中秋的老板借了钱,中秋答应去当杀手为其还债。中秋行动失败,并在数天后遭袭受伤,出院后阿萍已去世,他照顾的白痴阿龙被老板利用带毒品,因失手被杀。中秋愤恨交加,要向全世界报复。然而陈果用一种喜剧片的模式描述了三人帮的奋斗,呈观出一种所谓新人类、新世纪的面貌,最快乐的一段是3人在墓地寻找一块墓碑,以弄清死者自杀的原因。
“这不是一部又长又闷的艺术电影”,陈果说,“它也有娱乐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很商业化的。”陈果的制作方式是实验性的,至少是莽撞大胆的,但影片本身却非实验电影。他想做的只是拍一部属于年轻人的电影,给他们来个总结。“我觉得香港电影从未深入探讨过年轻人问题,有的只是借题发挥,从没有了解过其背景和问题……我四处去找些年轻人谈话,去他们爱玩的地方观察,但香港的青少年不知何时学会‘死撑’这个文化,他们不会将自己最差最黑暗的一面告诉你,你想发掘最深处是不可能的。”
走到这一步陈果已获得成功,《香港制造》和大多数装模作样的香港警匪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评论者指出:“它可以看作是对香港电影业本身的一个批评。”
目前独立制片在世界各国都属方兴未艾之势,前年的《逃离拉斯维加斯》、今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中央车站》都是众所周知的低成本、独立影片。好莱坞更有“以二手车的费用拍故事片”的说法,《迈克·马伦兄弟》一片的制片人曾出书详加解说如何以6000美元作为预算目标,把所有的费用都降低,包括租用设备的费用。理论上说,独立影片制作者应当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某部影片的构思,他为影片筹措资金,在摄制过程中拥有创作控制权,并最终组织销售和发行。因此美国的所谓独立影片(约占影片总数75%)其实并不能笼统算在内,因为不少独立制片公司是在与某个大电影公司建立“制作一发行”关系的情况下开始制作影片的,大公司的商业意志是如此强烈地渗透其中,以至于创作者常常不得不改变初衷。
“独立”一词应该留给那些献身于一个主题,或探索一个问题并且毫不妥协的影片制作者,他们的影片往往只能通过电影节和录像带发行。陈果是其中成功的一例。内地也有人将目光直接对准国际电影节,如实验电影《纸》的导演丁建城。他从著名作家苏童那里以极低价买到版权,从朋友处借到60万元,便开始了艰苦的拍摄。“参加电影节还可能得奖继而投放市场收回投资,直接走市场则必然失败。”前不久已完成影片的丁说。
也许在独立制片与大公司制片之间,在个人与市场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对艺术、人文价值和商业利益的追求与平衡才是关键。而且,即便是最成功的独立影片也不会丝毫触动电影在今天的性质:首先是供消费的商品而非自发的创造物,是娱乐与梦幻而非题目与警钟;甚至独立制作者本人也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尽快与大公司携起手来。独立制片最直接刺激的是那些热爱电影的年轻人,而它的价值也在于为主流商业电影充血,河道不改,而水流常新。37岁的陈果说:“相当一部分观众愿意通过电影严肃地看待社会,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似乎不管整个电影界如何,他都会坚持下去。 陈果香港制造电影节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