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个口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崔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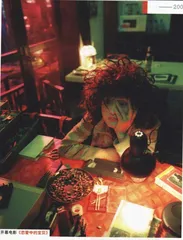
开幕电影《恋爱中的宝贝》
中国电影新气象
今年2月,导演朱文的新作《云的南方》先是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亚洲电影奖”,4月15日更成为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双料赢家:国际竞赛单元“火鸟大奖新秀竞赛”金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
朱文以前当作家当得很封闭,长期下去,他觉得会有碍精神健康;他认识到应该跟别人有良好的沟通。拍电影,起码可让他在一段时间内和别人有交流。相对于作家味道浓厚的朱文处女作《海鲜》,基调稳厚平和的《云的南方》更见对世界和时光的深度理解和成熟思考。
“一个人选择了一种生活,便失去了另一种生活。这一直是我着迷的一个命题。当一种生活成为现实,另一种生活便成了完全的梦。我始终觉得,其中有某种人生的真相。我想讲述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人的不可能的生活。”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导演观众现场交流会上,朱文说,“云南可以说是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的原意是不存在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我拍的却是实在的,这便回到电影的主题:有时候一个人的梦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你的不可能,有些人却可能是家常便饭。”“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人会变得麻木,没有了确实生活的感觉。一旦上路了,你会变得敏锐,仿佛器官都活转过来。”
艺术是不是一定要无边的愤怒?这次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马可·贝洛奇奥(Marco Bellocchio)这次带来新作《夜,早安》:上个世纪70年代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了意大利前总理莫罗的往事,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恐怖分子的想法。“我至今仍然愤怒,但以前那是一股毁灭性的怒气,现在则表现在拒绝建制上,没有摧毁的态度。”他第一部作品的年轻人弑母故事当时觉得必须如此才能在自身中找到自由。当年深信绝对革命的他已经扬弃了阶级斗争,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许我们国内肤浅和表层的艺术批评正是缺乏这种对多元个人化的尊重。引发观众审视理想本质的《香火》是导演宁浩的处女作,赢得亚洲数码录像竞赛金奖。影片中日久失修的古庙佛像塌毁了,年轻僧人一心出城筹款修缮,先是变卖庙宇古董,怎奈单位放假现金难求。僧人继而逐家募化,却惹治安干涉钱款悉数没收。一心向善的僧侣,在城市才开始领略世俗的洗礼。人人追求物质,城乡相距愈远。他甚至开始学会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佛像最终或可修妥,然而安放在心中的佛,却已无影无踪。关于信仰危机的《香火》讲述的是一个僧人的逐渐沦落,宁浩写《香火》剧本时23岁,还没有就读电影学院,去年毕业前,他用15天在家乡山西拍摄的全部镜头,演员全是找的中学同学,他们分文未取。去年《香火》在东京Filmex电影节拿到大奖,他跟同学平分了奖金。为人温和又成熟的宁浩的下一部片子是到内蒙古拍一部儿童片,探索蒙古人的文化和心理面貌。
其他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品还有评价分化的开幕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入围“亚洲数码录像竞赛”单元的《早安北京》(导演:潘剑林);结构主义风格及简约成分得到评审团特别表扬的《唐诗》(导演:张律),和“自主新潮”单元的崔子恩特立独行作品《哎呀呀,去哺乳》。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特别呼吁各界影痴密切留意今日的大陆导演作品,见证创意日趋活泼充盈的内地电影。他认为能造就新气象,主要是跟大环境开放,创作力得到解放有关。至于港人日渐熟悉的韩国电影,王庆锵的评语则是:“市道太好景了,结果大部分作者都走向主流发展。”
全球视野
亚洲地区电影新人新作的发掘一向是香港电影节的强项,对许多其他国际性电影节的亚洲选片都有长远影响。除却已在市场式微的日韩热潮,泰国和印度电影近年来的快速崛起惹人注目,在这次的节目策划中也多有着墨。
在印度人的心理和文化结构中,“命”的观念可谓举足轻重。火鸟大奖新秀竞赛单元中,被“特别表扬”的《风继续吹》是印度导演Partho Sen Gupta的处女作,作为影片的备注,导演从《奥义书》中摘录了一段诗:“你是你最深沉的欲望/你欲望所在,就是意志所在/你意志所在,就是行动所在/你行动所在,就是命运所在。”而影片中国际流行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成了“现代”印度的新价值和新规范,本土文化被抛弃,追问年轻人对权力和物质享受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曾经守望相助的社会何以兴起自私自利的风气。这不仅是当代印度的问题,好像和当代中国,当代亚洲及至当代世界,以及每个个人的问题息息相关。
纪录片人道奖最佳纪录片《S21赤柬杀人机器》的柬埔寨导演潘礼德同样关注更具象寻找个人的微不足道和脆弱不堪:他本人11岁被关进“劳改营”,4年后逃往泰国和法国,后来考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电影意味着我和其他人一起,身体和灵魂。对于那些死者我欠他们我的生命”,出于一种确信和必须拍摄此片,记录了昔日国家暴力机器的自我陈述和反应,“我所有的纪录片工作都建立在聆听上,而不是制造事件。这些细节见证着人性中还有一层尊严在暗中反抗,就在貌似不重要的细节里,我找到很微不足道,脆弱不堪的东西,使这些东西令我们成为我们。一个人不能完全埋没人性。明白一切,几可与饶恕同义。我们总不能尽明了世事,只可努力去做,促使我开始去宽心悼念。正义伸张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审判必应与唤醒记忆同行,以保护未来新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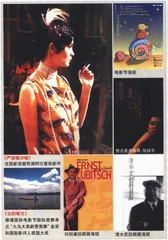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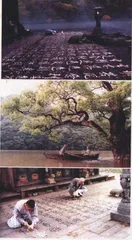
韩国导演金基德专题展,《春夏秋冬》剧照
台湾导演李康生的《不见》在2月份的鹿特丹影展已经拿了大奖,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台湾电影。李康生拍蔡明亮《洞》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久病轻生,后来还看到一个电视新闻:一个小学生每天在出门后就随手扔了爷爷为他准备的早餐,然后跑去麦当劳。巷子里发现了成堆的被丢弃发臭的早餐饭盒,爷爷知道后非常伤心。他决定拍一部有关“不见”的电影:“不见的时候我们也许才开始想念,才开始后悔没有珍惜,而最可怕的是,你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许多美好的事物会忽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了。”片尾儿歌“泥娃娃”中爷爷和小孩子夜里似人似鬼游荡的影子非常诗意,印象深刻。
曾经以《美少年之恋》和《游园惊梦》闻名的另一位台湾导演杨凡此次拍摄的昆曲纪录片作特别放映,连同昆曲爱好者白先勇先生及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作观众现场交流的时候气氛感人,“昆曲是中国最优雅的传统艺术,与现实不妥协的真正艺术。昆曲艺术家们对传统美学的执著与贡献,使我知道艺术两个字是应该义无反顾,一种真善美的追求”。
以前一直义无反顾被批评“远离群众,太知识分子”的81岁法国新浪潮导演阿伦雷奈这次的《严禁嘴对嘴》确是聚全了娱乐歌舞喜剧的流行元素,全心全意向法国20年代歌舞剧致敬。角度丰富的摄影却有些法国式的花头,对比巴西故事片《圣保罗狂情男女》的真实摄影倒是显得刻意无味。
《圣保罗狂情男女》此次博得评委侯孝贤和许鞍华的特别青睐,紧接《云的南方》夺得火鸟大奖新秀竞赛的银奖:影片将虚构的故事当作纪录片来拍,去掉人工矫饰的虚假格调,和陈腔滥调的第三世界贫民窟影像,刻画了圣保罗市的暴力问题:暴力不再是一对社会调查的数字,而变作一种社会分化的结果和生存方式了。导演特别提到:《无主之城》为以前一直倾向夸张化的巴西电影摄影的真实感打造了新标准。
疯狂为人民服务
全球国际性的电影节有将近700个,平均每天有两个电影节在开幕。香港国际电影节堪称其中杰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节目策划和活动设置上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国际而多元: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近300部不同类型的电影作品,十多处放映场地,足足分设29个节目单元。各种专题及特辑还承载着一份重重的历史意味,仿佛象征着一个个时代篇章的终结:《焦点美术指导:张叔平》;《怀念张国荣与梅艳芳》特辑;近年成为全球新焦点的《阿根廷新电影》及韩国广受争议的《焦点导演:金基德》;“大师中的大师”《喜剧之王刘别谦》及百年难得一遇的电影天才《清水宏101年纪念展》;《千娇百媚:林黛小辑》;由香港电影资料馆主办的《小说?戏剧?文艺片》;第九届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得奖作品展。电影节首次举办非主流的前卫电影专题:美国试验电影泰斗《斯坦·布拉奇治纪念特辑》和《彼得·寇贝卡:电影是什么?》回顾展:两位大师一位拍了400部电影,一位只拍了约60分钟;一位非常阳刚,原欲奔放,一位非常形式化,结构井然。
除却上面的各种和节目有关的繁琐工作,电影节还要安排各种免费的电影海报及剧照展览;主题研讨会和导演观众见面会;与各种国际国内机构合作名为“数码电影在欧亚的发行前景”论坛;编辑出版电影节的各种刊物,每日报纸及专业特辑;连同翻译、公关、媒体、赞助、营销、接待、行政、网页维护等各环节:这个让人致敬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竟然只有9名专职工作人员和16名短期雇员,其他的便是踊跃报名的临时义工,堪称不可想象的全心“为人民服务”、“极简主义”模范。并且,从今年起,电影文化不再局限于电影节的每年16天,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将由2004年7月起,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开始举办每月放映,将优质的电影放映和精彩节目推展至全年每一个月:沿承人文传统的香港One World电影节;集日本最新最劲作品的日本动画周;一向是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宠儿:芬兰怪杰大导演阿基·郭利斯马基Aki Kaurismaki的作品大检阅;还有纪念法国电影大师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逝世20周年经典展等等。
电影节目前的预算是1400万元港币,艺术发展局拨付700多万。明年起电影节将正式“非营利性”公司化举办,电影节总监戚家基希望将来能做到票房收入、商业赞助和政府拨款各占1/3。他们深具信心,志在必得,一个二十多年的品牌和努力使然:1977年由香港市政局创办;2000年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2002年开始改由香港艺术发展局独力主办;2005年更将是一个新的开始:香港国际电影节现正进行公司化的筹备,下一届将会是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香港国际电影节,使香港国际电影节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电影界举足轻重的活动。今后的发展计划是公司化后,发行电影,出版更多刊物和建立自己的品牌(电影配乐光盘和T-shirt),都是面向未来的清晰动作。节目以艺术性为主要考虑的原则坚持不变,并且会增加和内地的各方面文化交流合作空间。但是在宣传推广上会更努力接近群众,培养观众,以免曲高和寡。
香港本土电影与社会现实,独立与主流
王庆锵说:“香港是个很聪明,能很快赚钱的地方,一贯不重视文化发展。一个活动,要是不赚钱,在香港就很难生根。”
香港电影去年的产量跌,但是票房升,和经济社会状况紧密相关。因为SARS和本地政治和经济气候上的变化,“2003成为香港真正回归的一年。”中港电影界在政策上已经加强合作,在配额取消限制和戏院经营权等等给与不少优待,但是对于香港影业最大的困难是审批和发行等制度上的协调多于配额限制。
香港“独立”数码录像有三大(艺术中心、影意志、录映太奇)一小(蓝空间)机构,大部分本地制作人仍把菲林置于数码录像之先。另类电影在亚洲的市场愈来愈窄,最重要的是鼓励独立创作和协助独立片发行,配合长线美学教育,从而吸引已日渐丧失观赏非好莱坞片习惯和能力的观众重新进场。但现在两岸三地,越来越多的人对“独立”两个字特别敏感甚至反感,如同节目策划王庆锵,“不能将独立电影看得过高。最终还是要看一部片子好看不好看。独立不独立这是作者的选择,对观众是没有影响的。你用钱来衡量是衡量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不用钱而用本质来衡量,又变成一件很无聊的事。所以独立这样东西你可以作为一个宣传、一个市场的东西,但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电影节标榜好的电影,不标榜独立。”
并且在内地和香港,越来越多的独立电影人步向主流电影工业。《幽媾》的香港导演郭伟伦认为是一个必然现象:“所谓独立电影,其实并不是不能和主流接合的异物,独立人所作的,也不外乎用他们的方式说一个个故事,进入主流工业接受洗礼,可能还会令技巧更成熟,创作出主流之中较另类的电影。至于独立人商业化的程度,则视乎个别作者如何为自己定位。”
这次特展主题的奥地利前卫电影导演彼得·寇贝卡也说:“现在称之为前卫电影、地下电影、独立电影的东西,50年代统统没有。与其说我是一个前卫电影工作者,不如说我是游击队,是贼,为拍摄自己的电影战斗。我拍出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因为我穷,没有制作的条件,但我很快发现,这种限制变成了优点,它令我发现电影的狂喜和呈现循环事件的结构方式。电影是一种可以由个人执行完成的艺术形式。世上有两种电影,一是工业电影,占全世界制作的99.99%;起初制作队伍可能只需30人,然后是50人,今天,片末的制作名单可能多达300人。时间愈倒流,分工便愈简单,我想说,个人电影今天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