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三联有约:与刘欢对话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闫琦)

2004年3月19日晚,筹备已久的刘欢个人演唱会“欢歌2004演唱会”在座无虚席的北京首都体育馆隆重举行
朱伟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先问刘欢平时听得最多的唱片,刘欢说,如果有较少的时间,他会挑选较早的作品,比如莫扎特这样的;真有两三个小时没事做,可能就找“感觉中比较重的,乐队编制比较大,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家里看一个整场的歌剧”。
朱伟:也许是我对流行音乐有一些偏见,我总觉得它是为解决人们情感方面的压抑而宣泄的音乐,而古典音乐相对是精神、灵魂提升的音乐,表现形式上也要比流行音乐丰富。你的演唱能如此长盛不衰,我想是不是与吸取歌剧咏叹调,甚至更早的阉人歌手对声音的表现方法有关?
你是不是从这里吸取了很多东西?
刘欢:对古典音乐的了解肯定对我的音乐有帮助,它到底是人类几百年留下的财富,很多经验是一代代音乐家摸索出来的,西方人很善于做比较细部的涉及到音乐技术问题的探讨。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我以为从来都是并存的,流行音乐是都市里的民间音乐,这种民间的东西随着工业化慢慢集中到都市里,产生了都市民间的东西。20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传播途径的发展,使得流行音乐的水平提升了,并被更多更广泛地传播。由于它很通俗,被更多的人接受了,应该说是普罗艺术的范围。流行音乐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宣泄,其中很多东西是可以深入灵魂的。从世界范围看,我觉得各种艺术是在慢慢融通,这些年以来,国际上所谓的“跨界”是一种最时尚的方式,就是古典的、流行的全部融汇在一起了。“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不知做了多少期,他每次都和很多摇滚歌手、流行歌手,甚至民间的一些土著歌手一起做,这是一个很好的“跨界”。音乐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提供出来的是美好的,艺术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在我的脑子中,从来没有古典与流行之间的界限,说哪种更怎么样,如果有一点差别,那多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艺术本身不该存在形式上的界限。流行音乐这一百年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流行歌曲如同古典音乐一样,可以是感人至深的东西,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甚至是带有时代烙印的。
朱伟:我可能有些偏激,听流行音乐,比如听你的歌,听的时候也会感动,但是百听不厌可能就有困难。但如果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可能反复听过无数遍我也不会感到腻烦,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刘欢:说百听不厌,我的歌肯定还没有做到这个境界,但是我听过的流行歌曲应该有百听不厌的,比如披头士的有些歌曲。他们在60年代的创作,是集中了那个时期整个民间艺术文化爆发出的最高峰。那些东西现在被改编成很多种形式,有弦乐四重奏的,像YESTERDAY,有钢琴
的,有小乐队的等各种不同形式演唱的。至于我们这里的流行音乐,可能还得一阵子才能做到百听不厌。我做第一首流行歌是1983年,我以为,真正流行音乐的发展,应该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20年时间把流行音乐发展成这样,跟欧美人百来年的努力相比,说实话我们这个速度已经很不错了。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出现世纪经典,我觉得有点强求目前国内流行音乐的创作者。
另外还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问题——我们国家的音乐普及程度还是太差了点。10年前有一个统计,美国可以演奏交响乐的乐团有1000多个,最新的数字我还不知道,但是在中国可能连10个都超不过。流行音乐方面差得就更远了,美国流行音乐乐队的歌手组合真是不计其数,我们现在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金兆钧老师有一个观点,在中国做流行音乐,必须做到妇孺皆知你才能活下去,就是因为音乐生活水平太差。其实国外听摇滚也不是大面积的,在美国做POWER POP所谓强力流行的歌曲,像塞伦·迪昂,像玛利亚·凯瑞,来不来就卖千万张以上;听摇滚的人也是少数,卖个几十万张,百来万张就算是不错,但这就足够养活和响应这批摇滚歌手了。可在中国就惨了,买摇滚唱片的弄不好就百来号、千来号人,然后做音乐的也是百来号人、千来号人,这个不死才怪呢。我不是说我的音乐做得好,但现在这种普及程度逼迫大家不能做小群体,这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把整个的音乐生活水平提高上去,喜欢听音乐你得买唱片、得去演唱会。2000年在英国我听到一个数字感到很吃惊,英国人平均每人一年买7本杂志、4本书和3张唱片,当年英国是6300多万人,这个销量是多么惊人。如果正版销售在中国是这个水平的话,那中国的唱片工业早就不是现在的状态了。
朱伟:其实包括像《爱乐》这样的杂志,办了10年,刚开始销量一万册,后来曾经上升到两万册,又降下来,这是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你到国外去,任何一个大学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跟你谈莫扎特,谈舒伯特,这是基本的文化素质问题。说到高档文化消费,其实音乐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想到要吃好饭,却没有想到去听音乐会、买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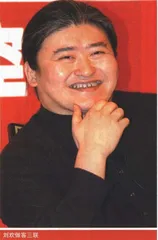
刘欢做客三联
刘欢: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得很长时间才能改变。我跟朋友开玩笑,在中国随便找出10个人,给他500块钱,可以听音乐会,可以吃饭,我估计其中可能有8个人会把它吃了。他们可能不缺这顿饭,但宁可选择吃,这是整体的消费观念问题。
朱伟:我们听古典音乐的过程,好像都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到20世纪现代作品,然后又觉得其实现代的形式感特别容易被消化,于是就回到早期的古典作品?
刘欢: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把19世纪给越过去了,越过去之后,就开始进到现代派,从德彪西到斯特拉文斯基,然后又返回古典去。回到古典可能跟有一段时间完全不能接受19世纪浪漫派的东西有关,因为我忽然觉得这些人太过于自我化了。我觉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家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古典主义音乐家仰视音乐,把音乐当作跟上帝一样崇高的东西,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使者,我把它本来就在的美好体现出来,他自己的情绪不太放到音乐里。但是19世纪正好反过来——完全把音乐当成自己情绪宣泄的工具,我今天心情不好,全体人都得跟着我哭;我今天心情好,大家都来跳舞。到了19世纪末,像柴可夫斯基就做到顶了,那对不起,我一个人的眼泪就是全世界的河流。后来再去听许多现代派,听它的手段是越听越邪乎。人接受现代派我跟大家讲一个糙理儿,其实就是一步步地向自己能够接受的不谐和挑战,如果听到这个不谐和,
还有比这个更不谐和的,最后听到完全是咧着的声才过瘾,好像在较劲一样。于是我才又返回去听最老的东西,听莫扎特以前,听巴赫,听斯卡拉蒂甚至听更早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唱诗班的合唱曲,包括蒙特威尔第与帕莱斯特里纳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纯粹的东西,好像音乐的本质应该是那样的。
朱伟:你对音乐史特别熟悉,讲的几个点都非常关键。比如斯卡拉蒂,他对意大利的音乐十分重要,他的键盘作品非常好。早期音乐中,除了宗教的清唱、合唱外,一件乐器的表达可能都比几件乐器的要好,因为特别单纯。意大利人是让乐器歌唱斯卡拉蒂,到了海顿那儿,把它结构化了。古典主义的结构化到了贝多芬,又把个人情感的冲突比较多的加进去了,它的好处是通过强化冲突,把音乐的表现能力和空间扩大了,也改变了个人与音乐的关系。我还是觉得古典音乐中的一些技术表现实际上用在了你的歌唱中,在流行歌手中大约很少有你这样,能体会
到演唱是一种声音的表现,或者说是表演,通过表演来追求声音的丰富性。它使声音变成情感的相对比较复杂的倾诉。
刘欢:其实在唱歌方面我没有太多道理可说,因为是自己瞎打的过程。流行音乐的演唱本身也没有什么前车之鉴,只是尽量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综合到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状态。这个东西也不能推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我对所有人声的东西都会有兴趣,像歌剧演唱的方法虽没学过,但是喜欢听,甚至包括中国戏曲的一些方法我都比较注意。比如说京剧中老生的唱法,跟青衣不同,不是假声的唱法。以美声的观点看,它是没有方法的,那是怎么形成的?高音上下是通透的,音量不是很大,保持很好的统一性,而且有很好的韵味,这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总是以美声的道理去分析,说人家不科学,是通过高筛选率实现的。以科学方法作分析我也做不到,只是学他们一个部分或者区间。
朱伟:我最近读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其中讲到中国音乐,他说西洋音乐包括所有乐器的音都是规定好的,但是中国音乐包括所有的乐器和演唱,音是自由的,所以乐器在演奏时,这个音和那个音之间的距离,有比西洋乐器更多的丰富性。在演唱中,昆曲、京剧的丰富性都要
比西方音乐丰富。可能你是把有意思的东西琢磨之后,都融汇在了一起。
刘欢:多年摸索中国音乐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研究得太透,否则会掉进去。我记得做《胡雪岩》那首歌时,因为胡是杭州人,导演希望我用评弹曲调,我说这太难了,评弹必须用方言唱,但那就是打算让中国80%的人听不懂。最后折中的办法就是用京剧素材,我找来找去,看哪个曲牌的东西跟西洋简单的一、四、五和声能套上,结果选了一条打散了的反西皮,将就着弄了首歌,觉得还挺顺当。后来又有一次机会想再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心想这次不能对付了,得好好把京剧弄清楚。于是专门去找李维康先生录了几张唱片回来,还弄了几本书,鼓捣了两个星期,坏了,最后写出来的是个京剧。我始终认为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是本质的出发点不同,你试图把这两个东西融合是不可能的,只能是
以某种东西为基础,把另一个东西拿上来有一点点色彩,这或许是能做到的最好的平衡了。谭盾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说中国的很多东西个性极强,一个三管编的管弦乐你再奏一个什么西洋旋律都不怕,我中国那小锣“堂”一声,完了,整个颜色都变了,怎么把这些东西套在一起来结合,那是挺难弄的事。
朱伟:电视剧里你的那些融合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比如你刚才说的是《胡雪岩》和《笑傲江湖》中的主题曲。
刘欢:《笑傲江湖》那歌就没法提了。录完后,看到有媒体说我和王菲唱的那歌是“大象和蚊子的对话”。
朱伟:这可能恰恰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注意到,古典音乐中越是追求宏大的作曲家写到特别纤细抒情的时候,可能是最迷人的。比如写森林絮语,瓦格纳的跟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里的味道就截然不同,瓦格纳的细腻就更感人。瓦格纳的歌剧我特别喜欢《罗恩格林》,它里面的抒情是最美的。
刘欢:那可能是他惟一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歌剧,其他歌剧都是打说出门就把你吓死的。瓦格纳的《指环》我听了两次,如果再听第三次肯定不行。把个音乐编得那么满,8个女高音同时在台上哇啦哇啦,全都是年轻演员,身体特别好才行。为什么现在听得比较少,就是太难演了。那些人写音乐根本不考虑歌手的极限,像威尔第和普契尼这些人写歌唱性歌剧会考虑到演员是否能达到,虽然有点较劲,但还是会考虑循序渐进,到最后给演员很漂亮地闪耀那么一下。瓦格纳不管,没有那个身体你就别演,没有那么大的乐队你也休想。他做那个乐队需要特殊的乐器,没有那么高的高音双簧管,先去意大利定做一个来。就是把乐队的能量性调动到最大。我可能比较保守,我始终更喜欢意大利的歌唱性歌剧,虽然很多时候有点程式化,比如故事进行得好好的,一下就停在那里,四个人就四重唱一下子,前后哪跟哪都不挨着,但听起来还是好听。瓦格纳这种大片的旋律铺满,然后就是一路的进行,他说是有一些个动机,但是说实话不是搞音乐的人听不太明白,动机在音乐里面乱跑,一会儿在个部位,一会儿在那个部位,听起来真的很累。
在两人对话结束后有读者针对现在古典音乐普及困难,问刘欢你觉得大学生接受古典音乐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刘欢说关键在对古典音乐欣赏的理解,“很多年轻人包括我的学生也有来问我古典音乐应该从那里开始听,说听不懂。其实,音乐是不需要我们以过去那种概念来听懂的,而应该感知它是否好听。我女儿现在的唱片有很多是古典的,其实我并没要求她。没去引导有一个好处——孩子会觉得什么东西好听,不去追究听得懂听不懂,觉得这是好听的音乐就可以把它接受下来。我们以前总是把古典音乐弄得很高深,把很多人拒之门外,这是一个误区”。朱伟则认为,“难以进入往往是因为人们的心态太功利——家长希望孩子学乐器掌握一门技术,而很多人是为提高素质而听古典音乐,它把自然地去追求好听淘汰不好听给遮蔽了,所以应该排除功利,从自然的喜欢与不喜欢选择曲目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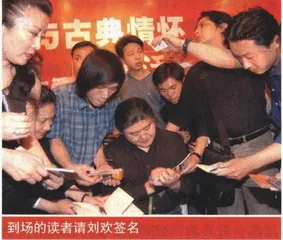
到场的读者请刘欢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