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斗:我与剧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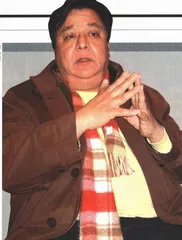
李金斗(戎花 摄)
学相声,从剧场开始
我13岁开始进科班学相声,1960年10月10日正式开课,12月26日我就开始登台,12月31日就开始给国家领导人演出。我为什么能这么快登台呢?因为教学方式好。当时我们是白天学完了,晚上老师带着你去剧场演出;第二天白天再给你排,晚上再学。我们行话叫“熏、过、遛”。“熏”就是听,“过”就是排,“遛”就是演。
这种氛围里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有一回演出的时候,后台去位老师,穿得很破。大家说,呦,这是怎么了?然后大家就一人20元,凑了200块钱给这老师渡难关。这种事情在相声界很多,我的师傅、师爷、师兄都是这样。现在,有人说我义气,其实我只是去效仿。还有一次我们到长春演出,高英培先生演了一个段子叫《石厂长》。现在很受欢迎啊,但当时第一场演出一个包袱都没响,我亲眼看见他给自己一个大嘴巴。他是最喜欢喝酒的,但那天晚上不吃不喝,熬到第二天早上6点,修改好了,来给我们讲,把我们都逗乐了,才肯吃饭。
电视相声,我适应不来
我第一次上电视是1979年,当时也是在剧场里现场直播。但后来我不怎么去电视晚会上演相声了,因为我的水平、语言结构,脾气秉性不适应,只能尽量闪展腾挪。
相声有相声的规律。相声要通过铺垫,一点一点来,我们叫“包袱”。电视呢,就违反了这个规律。因为一个晚会90分钟,不可能给你15分钟,那我们就要用相声的简单手段。简单手段用完了,就必须借鉴别的形式,比如向小品靠啊,往喜剧上靠啊,但那就不是相声了。大伙为什么觉得电视相声不可乐了,就是这种环境决定的。
剧场的形式就比较符合相声的艺术规律。过去的老艺人都讲究剧场。比如豆腐块剧场效果最不好,扇子面的效果最好。同样是大剧院,长安大戏院就比吉祥戏院好。长安大戏院底下有九个大铜缸,里面蓄水,演出时有专门的人不断往里蓄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就可以不用话筒。吉祥戏院没有这个,就必须用话筒。观众也有讲究。卖票、包场、组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卖票的,观众真的有热情来看,大家来,就是想笑。电视相声达不到这种要求。
当然,电视对相声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我们每一个演员应该感谢电视对我们的包装。从我自己来说,如果不是电视对我的包装,也没有李金斗的今天。有人说我是相声艺术家,但我其实就是长得比较特殊,在电视上容易被认出来。大家经常说电视晚会的掌声有点假,这个假其实是对的,因为电视是“做节目”,这个“做”呢,就需要“做手脚”,演员也可能弄虚作假,比如音配像什么的。但在剧场里就是实打实的。没有人领着鼓掌,也没有人事先排练笑声。为什么要到剧场来说相声呢,到了这里,他就会知道,当没有人领掌,没有人领笑,会不会适应。这是对青年演员来说至关重要的,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相声在低谷么?
相声是在低谷么?我觉得这是以讹传讹。你说这是低谷,那什么是高谷啊?你给我讲讲看看。现在我们一年200多场演出,几乎每天,所有的相声演员都不可能在家待着,住着楼房,开着大汽车。这是低谷,那就没高谷了。你不能把相声在电视上的曝光率作为相声在高谷还是低谷的依据。
当然现在相声确实有许多问题。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文化、素质比我们高,长得比我们漂亮,个子也高,但是学得不如我们扎实。大专班的学生,不会说《八扇屏》,不会说《卖布头》,很多人是为了文凭,不是为了相声。
还有就是实践场所太少。相声和京剧这些传统艺术都是这样,需要实践。16岁、二十几岁就成名不可能。现在确实经常上电视红起来的,但那不是在说相声。
当然场所少也是个时代原因。在我小的时候,北京城里演相声的有五六摊。北京曲艺团有两摊、北京青年曲艺队有一摊、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启明茶社,其他就是吉祥啊,长安啊,这些名角荟萃的大剧院。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少了,很多剧场都关了。80年代以后都是从电视里看相声了。年轻演员没有场所,我们应该想办法给他们开始提供场所。
还有就是大家生活方式也变了。过去大家都住在城里,住在剧场周围,下了班就看一眼戏码,吃完饭一家人就去看。现在都拆迁,都搬家,家都住在大兴啊,顺义啊,去剧场也变得很不方便。要想欣赏文艺,就只有买一个电视放在家里。
其实很多相声界现在搞的东西并不稀罕。比如说“相声剧”。相声一向讲究: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的。很多的前辈可以唱戏,可以演话剧。我的老祖赵蔼如先生,演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演得相当好。讲《山东话》的高德明先生当年到山东切面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就是本地卖馒头的山东人。我现在只是照猫画虎,真正的根本没学到。我跟我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但我赶上一好时候,能开汽车。他们只能骑自行车。
所以我觉得,相声现在还谈不上改革,首先是继承。当然每一个演员都会有发展,不可能一样。但很多现在的年轻演员还不会说相声呢,还改什么啊。让他们规规矩矩来剧场说一段相声,说不了,然后说,我改革了,那不是不讲理么?再改,也得叫相声啊。

“周末相声俱乐部”为“相声回归剧场”活动填补了平民市场的空白 (戎花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