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与政治哲学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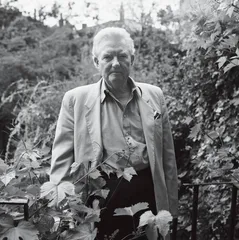 (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 )
(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 )
反对行为主义的理性主义者
2003年3月,《纽约客》记者拉里莎·麦克法夸尔撰写了一篇乔姆斯基传略,概述了乔姆斯基的学术和政治批评历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文中说,乔姆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语言学革命就如同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界发起的革命。人们用他的理论分析音乐、诗歌。在他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诞生了认知科学这门新科学。
现代语言学始于孟加拉高等法院法官威廉·琼斯爵士1786年向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所做的演说。他提出,梵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着共同起源,他激发了若干代学者去比较各种语言的发音和意义,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处。到19世纪末,印欧语系之间的亲缘关系得到证实。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弗兰茨·博厄斯对欧洲人强行把语言塞进拉丁语模式的倾向越来越不满。就因为印欧语系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并不意味着所有语言都是一家人。博厄斯在正在迅速死掉的北美土著语言上找到了机会和使命:他宣称,语言学家不要研究已经死掉的语言或众所周知的活着的语言,应该在美国各地搜集语言。搜集之后发现,北美土著语言跟印欧语系无关,这几百种语言之间也没有关联。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语言学家伦纳德·卢布姆菲尔德把博厄斯的语言学发展成了一门严谨的科学。他将语言中不能做精确与严格处理的、不能直接观察到、也不能进行物理测量的素材排除在外,把语言学限制在纸上的记号和口头的声音。部分是由于把自己限制在严谨的、可处理的范围内,布卢姆菲尔德学派非常成功,在40年代乔姆斯基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很多语言学家甚至觉得几年后这个领域的工作就将结束。
 (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
(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
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句法结构》。这本书的革命意图并没有很快显露出来。起初它被认为是布卢姆菲尔德学派文献的一个有用的附录,把长期被忽视的句法带进他们的视野。但一年后,乔姆斯基开始继续攻击该学派,他说,布卢姆菲尔德学派以为自己把一门人文学科变成了科学,其实他们的研究一点都不科学,科学的意义是解释世界,布卢姆菲尔德学派将自己局限于语言的表面,只是对语言加以描写,认为语言多变、不可预测是受到了表面差异的迷惑。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文化上的人造物,语法源自语言内部,它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在文化多样化的外表之下,语言有着统一的结构,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一结构。语言学家不必像布卢姆菲尔德学派那样,辛苦地搜集数据,如果所有语言在根源上都是一样的,那么研究英语就足够了,语言学研究完全可以在办公室里展开。他也承认这只是一种猜想,至于语言是怎么来的,他也说不清楚。
乔姆斯基长期以来反对极端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信念以及人类特有的一切思维和行动的模式都可以解释为:由条件反射过程逐步建立起来的习惯,学习只不过是习得新的行为。乔姆斯基不喜欢把人类的特点说成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生成的。他相信,人类是受创造性地表达自己欲望的推动,而不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这种粗俗、卑微的目的。他想把语言看做一个完美、统一的体系。
麦克法夸尔说,乔姆斯基拒绝考虑政治动机,他认为讨论个人动机是无意义的,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这既是他的语言学也是他的政治思考的核心,认为人类的心灵在出生时就包含了思想结构,甚至包括道德思想的结构。在他看来,精英们都是自私的,这是由于制度而非他个人的意志决定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乔姆斯基这样一个相信人是自由的人,却持有决定论的观点。他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拒斥人受其环境影响的观念,把影响个人的文化、历史和经历都看做非决定性的。这源自理性主义者的传统:如果理性是人最重要的特征,如果理性是普遍的,那么推论就是,人类应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思路,因为它使得理论家认为,无需注意人的动机,因为他们真正的欲望都已经写在理性的逻辑中了。这样就不存在分歧,非对即错。”
理性的逃亡
2005年,在“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100名公共知识分子网络投票评选中,乔姆斯基排名第一。而在此之前,两位学者在他们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著中都对乔姆斯基提出了尖锐批评。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理查德·波斯纳把乔姆斯基当做“公共知识分子著作的质量问题不可回避之例证”。他在2001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说:“乔姆斯基在其卓尔不群的学术生涯中耗费了无数宝贵的光阴,撰写了浩瀚庞大的政治作品,可是,这些著作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却极其有限,绝大部分荒谬不经。乔姆斯基对原始资料的运用毫不加以批判,并且他的方法论也令人失望不已——他只是简单地进行论题的转换。”
波斯纳指出了乔姆斯基立场中的自相矛盾:在乔姆斯基看来,诉诸武力永远不具正当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清白无辜的。然而,当一个既非美国、亦非美国盟友的国家或者群体诉诸武力时,则有可能被原谅。“乔姆斯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他所信奉的那种信条——他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绝对正确,并且也不试图进行辩护——说明了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把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混淆一起的普遍性错误。”
波斯纳认为,乔姆斯基政治方面的著作中包含错误,他却坚决不认错,这是因为时事评论界不像科学界那样存在学术共同体的约束。“科学社群的规范中规范等级体系居于较高地位,它们是精确无误、思想开阔、无私公平以及逻辑性的典范,而乔姆斯基和古尔德却在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经常地嘲笑这些规范。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他们在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时就如同在悠闲度假。”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使乔姆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人,“成为名人的诱惑使他把从自己的学科得到的名声作为资本,获得一个就公众问题宣传自己观点的舞台”。
约翰逊深入分析了乔姆斯基在使用武力方面的矛盾立场。他说:“在整个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知识分子越来越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时暴力的日益升级所激怒,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知识分子为了得到种族的平等或殖民地的解放,越来越愿意使用暴力,而当他们发现西方的一个民主政府为了保护小国免受一个专制政权的占领而使用暴力时,就特别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知识分子提供的解释是,他们一方面反对制度化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在证明个体的、私人的反抗暴力的正义性。”
一个学院里的语言学家怎么会对美国政府的运作无所不知,怎么能获得关于美国每一届政府隐秘的动机的第一手材料呢?《反乔姆斯基读本》一书认为,他办不到。约翰逊则指出了乔姆斯基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联。他说:“乔姆斯基认为,他关于语言普遍律的著作本身,就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不道德的主要证据。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人心生来是一张白纸,那么人如同一块块黏土,可以把他们塑造成我们喜欢的任何形状,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政权、公司经理、专家治国论者的适合的主体。但人并非生来是一张白纸,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心理结构,对文化和社会的模式有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模式对他们是自然的,所以国家的种种改造人的努力最终必然失败,但在失败的过程中,它们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并包含可怕的残酷性。美国企图把它的意愿与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模式强加在印度支那人民的身上,就是这种残酷性的范例。乔姆斯基的论证,从天生的结构开始,如果它有根据的话,完全可以说,它构成了对任何一种社会工程的总辩驳。”约翰逊说,乔姆斯基对自己的立场贯彻得不彻底,他批评美国改造别的国家的意图,但没有反对美国之外的专制国家实施的社会工程,“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乔姆斯基已经完全不准备同那些富有理性的人进行严肃的争论了”,约翰逊称此为“理性的逃亡”。■ 读书语言学哲学政治乔姆斯基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