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的“乡绅”之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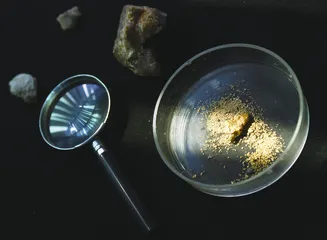 ( 老栗家的老院子现在是“老栗电影基金”办公室
)
( 老栗家的老院子现在是“老栗电影基金”办公室
)
退隐心
2000年秋天,栗宪庭搬到了小堡村。一个直接原因是他和廖雯的女儿即将出生,城里的房子太小不够住了。同一时期,他萌生了“引退艺术界”的念头。廖雯开玩笑说,“女儿的出生把老栗给废了”,而栗宪庭精神上的自我“废黜”则另有其因。
之前的半年,他和廖雯一直在美国旅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AAC)提供的研究资金让他们遍访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名艺术家。“我等于是最后一次向西方告别。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去了世界很多地方,由开始的兴奋发现我对西方的了解就是异国情调。1999年下半年我在美国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当代艺术都是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那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那时,中国当代艺术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栗宪庭觉得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就想彻底退出艺术界,反省自己,“去想想我做过的事情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无益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新的价值”。
在小堡村,栗宪庭的那个农家小院,从1995年到2000年一直借给艺术家住,先后有罗氏兄弟、郝秀丽、孙国娟、伊德尔等人住过。2000年夏天,他花了几个月,把原来的房子全部拆掉翻新。小院是解放前建成的,当初栗宪庭看房的时候,就看中了它的破败和雕花的窗格。在他的拾掇下,小院旧貌换新颜,红砖墙木头门,凉棚板凳荷花池,门墩肥狗胖丫头。栗宪庭此时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开始对做饭、整理房子越来越充满热情,对事业和艺术越来越失去兴趣,尤其一想起写文章就心烦,所以才有了廖雯说的那句话。
然而在小堡村,栗宪庭并没有找到他的桃花源。本来想远离艺术潮流,却因为他的落户,大量艺术家开始往宋庄聚集。每天不请自来的艺术家比城市生活时期更加络绎不绝,新来的年轻艺术家,到了宋庄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他家的门。喝醉的艺术家半夜三四点来敲门把他拽起来,和他聊艺术。“我在宋庄10年的生活中,没有比10年前更安静。”年轻艺术家创作和生活上的艰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栗宪庭觉得安静的生活可能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根本就无法存在,生活又成了每天三陪:陪人聊天,陪人喝茶,陪人逛工作室。在他家采访时,碰到几拨客人,多少体现了栗宪庭这些年的日常交往:一个摄影策展人来和老栗商量他们共同策划的一个摄影展,一个青年艺术家来请栗宪庭给他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字,一队日本欧巴桑来参观特意看望栗宪庭,岳敏君的助手送来一兜他家院里结的柿子,还有不同艺术院校的女学生在那儿闲待着,帮着烧水沏茶。
 ( 老栗家有静谧之感的院子
)
( 老栗家有静谧之感的院子
)
“我这人一生的弱点,就是很难面对这些问题说不,搞得我现在很累。”栗宪庭说。1997年就开始在小堡村居住、经常去栗宪庭家串门的艺术家伊德尔说:“老栗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有话语权,来到村庄以后,人们自然而然,无论艺术还是生活问题都会想到他。而他骨子里又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恭俭礼让,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1997年,伊德尔从内蒙古刚来北京时,住在通州比小堡村还偏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天,廖雯带朋友去他那里看画,感觉到交通不便,主动对他说起她家在小堡村有个空院子,请他过去住。伊德尔最初就想住到小堡村,但是那会儿根本不允许艺术家租房子。他在老栗家的小院一直住到2000年。
在早期圆明园和宋庄初期,做职业艺术家是一种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则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2000年以后,索家村和费家村等艺术家村落也在兴起,而选择宋庄一个是因为房租便宜,当时花1600块钱就可以租个小院住一年;另外因为栗宪庭的到来,无疑令生活上和精神上无着无落的年轻艺术家们更有安全感。“艺术家在宋庄聚集,是艺术商品化的结果,都想来宋庄寻找机会。”栗宪庭说,“客观上还因为近些年各地艺术院校的扩招,都是盲目追求升学率造成的。”考上了大学,但不知道是不是把那些本身对艺术没有热情、更别提天赋的孩子给害了。很多人怀着憧憬,但在现实生活里没什么出路,没有实用的专业技能,也没有什么钱,仅仅为了体验生活,去接近艺术,宋庄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
 ( 宋庄镇新居民——画家张庭群(右)和周燕
)
( 宋庄镇新居民——画家张庭群(右)和周燕
)
“人生无常,随遇而为。”栗宪庭给朋友写的一幅字,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境。“成名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视野内了,我关心年轻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很多年轻的艺术家请他去看他们的作品,期望得到这位批评家的指导和推荐。问他:“要是看到明显没有天赋的学生,你会建议他卷铺盖回家吗?”栗宪庭说,“我一般不太会刺激别人,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为你自己画画,忠于你自己的心灵。没有钱,你去打工,也不要去画行画,也不要跟着风走”。与此同时,他发现大量的艺术家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令他忧虑:“我能为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在宋庄渐渐形成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艺术家聚居群落的过程中,栗宪庭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个长远发展模式。
乡绅时代
 ( 艺术家欧阳春 )
( 艺术家欧阳春 )
今天,宋庄的高速发展是栗宪庭始料莫及的。“刚来到宋庄那几年,我老想我是什么?我从一个编辑到批评家到策展人,那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以前一直在反对传统文化,后来发现社会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就牵扯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就是用你的想法和智慧来解决问题。”
从2003年起,栗宪庭和小堡村支书崔大柏的接触密切起来,小堡村于是开始了全面改造,铺马路,铺地下水管道。“传统和现代化不一定是对立的,但是中国致富有一个情结——我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我为什么不能把一个传统的房子改成现代化?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太多了。”栗宪庭说。
当人们试图在栗宪庭身上寻找宋庄发展的答案时,他总是这样说:“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碰上了一个疯子!”“疯子”就指崔大柏。崔大柏是土生土长的小堡村人,说话时总爱提到“一切从村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他决定所有发展思路的基点。被叫做“疯子”,一是因为他胆子大,胆子大是因为他没有比当小堡村支书更高的权力欲望,而且他有决断力,这个村级干部的远见和魄力经常令人惊讶。栗宪庭和崔大柏的相遇,真正形成了宋庄文化产业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崔大柏在农民和艺术家之间起着一个奇妙的平衡作用。“当初奇形怪状的艺术家进村儿,农民就天天反映,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先观察一段,他们本质的东西怎么样?为人怎么样?是不是对我们村儿起到了正面的经济拉动作用?那些早来的艺术家也相当不错,‘非典’时捐点钱,农民一得到实惠,就不关心那些奇形怪状了。”听李学来谈到崔大柏当初和房地产开发商制定的规划方案,他都很真诚地为村民的利益考虑,“崔书记给开发商制定了‘四个一’政策,就是‘一楼一户,一户一店,一户一险,一户一股’。‘一险’和‘一股’是让开发商分给农民的保险和股票”。但后来崔大柏采纳了老栗的建议,保留了原生态的农家小院。这些年来,来找他的房地产商一拨又一拨,他没再动过出售土地的念头。“一旦上马房地产,土地再也没有改变的机会。一次性收回钱,只能当时得到些好处,其实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土地增值的空间更大,我始终不主张占自己的土地搞房地产,因为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崔大柏说。
2004年,小堡村人均收入是9000多元,当年通州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是6000多元。而这一年,一个时代背景是艺术市场的兴起,崔大柏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产业。他算过一笔账,一个画家在小堡生活一年的费用包括吃饭买画具等等,大约是6万块钱,400个艺术家,就带来2000多万元的消费。崔大柏说起为什么他可以和老栗的很多想法一拍即合时说,“第一,从我们农村干部来讲,我们觉得他人挺好。第二是为我们当地农民创造了可支配收入。如果公安局来了清人,我们就说人不在,如果不违法,我们就把他们留在小堡,因为他们改变了小堡的经济格局。最基本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我们之间存在的高度默契,完全是不可复制的”。
“他是父母官,代表权力,但我要影响权力。”栗宪庭说,“我觉得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必须去影响能把这件事做成的人。崔大柏聪明,而且有思想,他对农村的政策很有想法。”“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我还是要为农民考虑,这是双方的利益。比如我要说服他不要盖楼,因为楼房逼仄的空间不适合艺术家的生活,那他就会远离你这儿,那10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能接受这个原生态的意见。”改造完小堡村,崔大柏带着栗宪庭去看地,宋庄文化产业链从这个时候开始悄悄形成。
崔大柏手里有两块空地,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他带栗宪庭来到湖边,指着湖区周围的430亩空地说,“你给我做个文化公园吧”。“我说你要文化公园干什么,我给你出个方案。我把艺术家的聚居形成一潭水,那必须让它流动起来才能不腐。这就涉及两个机制,一个是建画廊,艺术家必须有卖画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艺术赞助,反对艺术商品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不让他卖画,他怎么活?要想吸引好的画廊,那就必须有好的艺术家,而有了好的画廊,有名的艺术家才可能到这个区域里来。”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农民因为听到说国家颁布法律不准占用耕地建房,起诉在小堡盖房的艺术家,一时间几乎形成一股风气,而只要官司打起来,艺术家就得走人。崔大柏也想通过重新规划一块地给艺术家住留住他们。
栗宪庭很快将艺术园区规划方案交给了崔大柏,为了让上级领导们能看明白,建筑师采用了房地产惯常使用的俯视的立体视角。“在国家提出文化产业之前,我们就开始规划文化产业区。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稳定农民的收入,增加影响力。我们后来又意识到,文化产业要是想长足发展,光靠租房这部分产业是不够的。”崔大柏说,“和老栗反复协商后,觉得还要有产业服务、画廊、美术馆和拍卖行,老栗关注的是这种文化现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有一个学术地位,我们考虑的是拉动本村的经济发展。”艺术家园区包括有非营利展览空间——宋庄美术馆,于2005年5月动工。当时小堡村的村年收入为800万元,崔大柏拿出了两年的村收入共计1750万元投入到美术馆的建设中。围绕宋庄美术馆的一个有十几个画廊的区域,外围有100多个正在建设中的艺术家工作室区。后来这个园区逐渐成为宋庄艺术家群落的中心,它与宋庄十几个自然村落居住的艺术家,形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另一块空地是废旧的饲料厂,当时老栗和廖雯考虑到宋庄的女艺术家生活上的不方便和安全隐患,把它改建成了“嫘苑”,经过科学设计的复式工作室,以最便宜的租金租给女艺术家。“我给他们的要求一定要质量好,一定要有暖气,不准用轻钢顶。”嫘苑的建成,构成了小堡村艺术家另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就是改造工厂。后来崔大柏一手建立的“国防工事艺术区”,也是复制这个模式。在小堡村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老栗参与改造的农家小院。村里出一部分钱,房主出一部分钱,老栗出改造设计。他清楚艺术家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一个大院子隔成两个互不干扰的空间,给艺术家的空间要大,敞亮。改造出来后,几乎每家农民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后来旁边村都按照小堡村的模式扩展了。加上后来的自建工作室,这就是来宋庄生活的艺术家可以选择的三种生活模式。最便宜住在村里的农家小院,年租金在去年是1万元左右。
村声
和静园艺术馆是紧邻宋庄美术馆西边的一栋清水泥建筑,主人李冰毕业于鲁美,后来下海做茶生意做得很成功。2005年,他花600万人民币打包收购了濒临倒闭的中国最早的3家私人美术馆之一的东宇美术馆的所有收藏品,其中包括了张晓刚、岳敏君、方力均、王广义等最重要的4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79幅作品。拿到这些画后,李冰就想做一个10年回顾展,因为东宇开幕的时候,老栗给他们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艺术市场需要自己创造》,里面流露出一个观念,意识到西方艺术市场在玩中国艺术。这年秋天,他找到了栗宪庭,栗宪庭就和他商量能不能在宋庄盖个美术馆。李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把准备投资酒吧的1000多万元撤出来投入美术馆的建设。李冰没想过卖掉这些画,老栗也建议他不要卖,至今这些作品像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静静地挂在和静园美术馆。李冰说:“我就是冲老栗来的,我看出他是个大修行人。要是没有老栗,我不会在这儿盖美术馆。他的人格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永远给别人架梯子的人,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欲望越来越平淡。”
“他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的家长,生活中不懂的事情都问他。”张庭群说。2002年9月他来到宋庄,之前他把刚从四川美院毕业时的作品发到老栗的信箱,老栗回信说,“你可以来看一下,看看你是不是适合这里”。到了以后,老栗又对他讲,北方冬天很冷,你还是回去吧。但那个冬天他没走,留在了小堡村,一住就是6个年头。3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和妻子画家周燕住在小堡村租来的农家小院里。他们一共搬过6次家,房租从80元一个月,到150元、200元、330元……第二个房子是老栗介绍的一个艺术家帮他找的。至于怎么画画,老栗没有给他多少指导。现在他和周燕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房子是老栗和他们一起设计的,盖房子时,不到30岁的两个画家尚需要父母的资助。老栗在规划艺术家园区时,把离他家最近的一块地划给了他们。张庭群看上去就是个老实孩子,在宋庄生活颇有一些受欺负的故事,老栗给过他很多照顾。“过年过节都在老栗家包饺子,经常有几十个人,每年都到他们家求对联,他经常做面给我们吃。”张庭群说。栗宪庭的家对张庭群们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资源平台,在那里可以认识其他艺术家和经营画廊的人,老栗也有意识地这样安排。现在张庭群和周燕签约的画廊都是栗宪庭给介绍的。
艺术家欧阳春代表这样一类艺术家——和老栗来往不是很密切,但是直接享受到了宋庄方式的好处。村里主马路修好后,为艺术家服务的相关产业也一下被带动起来。“小堡村为艺术家服务的相关产业是最发达的。”欧阳春说,“我打个电话,比如我要2米×3米的框子,什么样的画布,什么样的颜色,哪个国家的颜料,马上车给你送来。宋庄的艺术家也影响了当地人的思考方式,从农民到干部,都在逐步接受这个模式,村里人越来越习惯艺术家的存在了。每年村里一帮保安收卫生费,一个人200元,2002年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横,把门砸得要塌了似的,但是敲门声一年比一年轻了,说话一年比一年客气。到我离开搬去艺术家园区时,已经开始叫我老师了。”
艺术家和包工头闹纠纷,老栗要帮着调解;夫妻打架,也跑到老栗家说理。尽管他真不愿意管这一地鸡毛的事儿。采访的时候,多次听到人提到老栗对他们的影响。欧阳春说,“老栗让宋庄这种方式固定下来了,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宋庄的生态和他有密切关系,形成生态,艺术家才能长久地生活下去。老栗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合力,他把艺术家团结起来,给很多艺术家在生活中创造了条件,其中包括优秀的艺术家,也包括很窘迫的艺术家”。
但凡形成艺术家聚居地的地方,都是寻找一种群居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宋庄的艺术家层次很多,有少数优秀的艺术家,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坏的特别坏,某艺术家感叹骗走他多幅绘画的骗子仍然在宋庄生活得好好的,因为没有签合同,老栗对付这样的混子也毫无办法,毕竟不是黑社会。小堡村治保主任李学来说,几乎从2004年开始,村里的治安案件90%以上和艺术家有关。“净是醉酒闹事的,我经常接到他们酒后打来的电话。一天一个艺术家喝醉酒了,拼命喊救命,我说你在哪儿?他说在大兴庄,已经出了我的管片范围,但后来想想于心不忍,就去大兴庄看,一看他开车撞树了。后来安排警车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完又送回家。”李学来现在已经和艺术家们渐渐打成一片,采访的时候,他正陪着方力均的老爹聊天。
栗宪庭对来园区的艺术家说,不要把这个艺术家园区当财产,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生活方式。“我原来不想建这个房子,崔大柏一定要把我放在这儿。”他坐在位于湖边的房子里说。开始这块地老栗想给崔健,第二次是给的夏小万,一共给了4个人都没给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旁边有高压电线。崔大柏最后急了说,“这块地就是栗老师的,谁都不要动”。他花钱买了一大批砖,指定一个包工头说开工就开工了,院子里的3棵树见证了他们所有的规划会议。“我一直有走的想法,到现在也有走的想法。想想,水至清则无鱼,这儿也进来很多很烂的艺术家。规划园区的时候,我说安排艺术家的这个权力,我一定要,我没有给他们提过这种要求。所有艺术家我来审查,我来谈话,很烂的艺术家、很商业的艺术家都别来,但实际上只有1/3是我安排的。”栗宪庭说。■ 廖雯栗宪庭乡绅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