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音乐的自觉中国意识 ——作曲家们说
作者:王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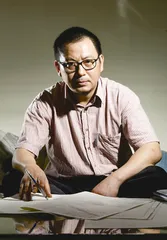
郭文景(作曲家,《文字》作者)
什么时候接受任务,真的想不起来了,一年前的事情了。
我算是介入比较早的,当时我不想参与,可是陈其钢老师说让我做“活字印刷”部分,我觉得很有挑战性,而且很难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就答应了。那时候和张艺谋导演见面,我们商量怎么做这部分音乐,他只知道不要什么,但是要什么还不知道,不要的是所有的朗诵方式都不要,但是确定了有近3000人的人声元素。于是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试验,开始还试验过朗诵《老子》,后来又改了,成了表现《论语》,而《论语》中朗读什么也是一改再改。
一开始我用京剧小生来念诵,导演听了觉得太高亢,要换,换成一种大调子,雄浑的那种,正好和我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相类似。我觉得中国太多的东西被遗忘了,包括活字印刷,包括春秋时代特有的气质,那种气质是雄浑、高昂的,又大气磅礴。调子确定下来后,就是寻找过程,一件西洋乐器都没有用,我找了西藏的钹,那种乐器只有在藏戏或者宗教场合才出现,声音特别高昂。后来又找了很多鼓,包括一人高的大鼓,又找来几乎所有的北京京剧演员中的黑头,一共50多个,不断扩展、重复,几乎是能达到的最好效果。
录音的时候很麻烦,尽管请的是录制技术非常好的外国录音师,可是他们理解不了,总是不能做到我要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元素,反倒是开始录素材的中国录音师很兴奋。结果一直在磨,那外国录音师离开北京的前一天,还在帮我干活,不过最后还是把我想要的粗犷之气给冲淡了。

录音的时候,人人都很兴奋,那些鼓师、钹师都互相拍照留念,从来都是少数几个人演出,都不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同一场合里。那种竹简的效果是两种竹板打出来的,我们也找来一大群打竹板的和打竹节子的,非常复杂地把他们安排在一起,这种方式他们自己都觉得闻所未闻。
黑头的念白开始有很强的京剧感,但我们不要这种感觉,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磨,最后属于正常说话和戏剧说话之间的平衡,有力量和韧劲。

“活字”之后接下来戏曲那段不是我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写上我的名字。那段本来是表现秦朝风格的,一直是赵季平老师的作品,可是后来因为表演用的皮影效果不好,不能用,彩排后拿下来了。演员们都排练了一年了,这种事情碰上了没办法。
这次经历了多次修改,不是音乐本身,而是一些别的东西,看在导演的分上,我也不断做了修改,修改的过程很痛苦,我是为张艺谋才这么做的。当然,录音方式的挑战表明这还是值得做的一件事。今年4月份,开始彩排,我根据演员动作再去决定各段各节长度,精确到了秒。这种广场音乐的形式不够精美,也是我的第一次广场作品,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东西了,但是效果很好,我非常满意,是创作的一种尝试。
叶小钢(作曲家,《星光》作者)
我印象最深的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80台钢琴一起演奏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极其有想象力,当时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办奥运会,我也要参与,没想到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时我听说组委会要求公平竞争,作曲家要PK,从参与原则来说我觉得没错,可我不愿意去参加。我忙,骄傲,尽管早就收到了组委会给的导演阐述,还是不去PK,可又隐约觉得,这件事不会绕过我。我一看音乐文本,就明白是要什么东西,也就是我今天呈现出来的东西,一点弯路都不会走。
果然,春节后,矜持的陈其钢终于来电话,请我出山,写现代这部分的开篇。我找到了我的学生邹航,他帮我做电子音乐,这部分他很出色,可是他很紧张,原来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被“枪毙”了。我告诉他不用紧张,把我自己一天内写好的东西给他,让他做电子音乐部分,做出导演要求的那种满天星光、未来世界的感觉。他花了几天时间做好了,送去后,很快我接到导演组电话,说是张艺谋要和我通电话。张艺谋对我说:“感觉真不错,你介入得最晚,可是最靠谱。”
我这么自信,还是因为我平时的功底,加上平时积累了无数经验,知道他们要什么,也明白自己应该找什么样的合作者,这都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素质。陈其钢告诉我,很多音乐都被要求重写了,可是我没有,我听得出他很焦虑的声音终于放松了点,能减轻他的负担,我很高兴,毕竟我们是老同学。纠正一下,当时的1977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四大才子”里面没有他,是外界的误传。
后来张艺谋问我什么时候能写完,我想只要一天就行了,可是出于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不认真的考虑,还是对他说要一周。其实一点都不费力,麻烦的是后来把版本加长,从6分钟到8分钟,这比较麻烦。就和创作一幅画一样,6尺加到了8尺,总是有点难度。
因为早就心照不宣是郎朗演奏,所以我在钢琴部分炫耀了技巧,写得很难,录音时他对我说:“你想弹死我啊,那么难。”我们说说笑笑就录完了,乐队也高兴,觉得很享受,不像有些作品又难又复杂,效果又不好。我的音乐像丝绸一样光滑,有朝气,好像给世界加上了一层膜,但又没有侵略性,很温暖,有拥抱人的感觉,这是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吴军(中央音乐学院老师,《倒计时》、《丝路》、《自然》作者,《歌唱祖国》的改编者)
我得到通知非常晚,本来想这是知名作曲家的事情,没我们年轻人什么事情,就回成都过年了。结果大年初一接到电话,说让我回来,要在年轻作者当中挑选一些人,结果年没过完就回去开会了。见到陈其钢老师,把丝路那段想要的东西简单给我们阐述了一下,让我们几个人PK。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好,可是我比较能领会想要的东西,当时就有了一半的构思,两三天就写出来了。
给我们的文案是个很模棱两可的东西,因为一是没确定,二是不能泄密,但我觉得这模糊的东西还很对我胃口。当时就想,一定要用最传统的中国方式来表现,不管是丝路上的荒凉和辉煌,还是海上丝路的博大和宽广,结果一点包袱都没有,而且陈其钢老师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不能有私利来做这件事,那样做不好。结果3天就完成了,几天后得到通知,说是我的作品在5件作品中中选了,后来才知道,前后有30多个人为《丝路》作曲。
当时作品是5分多钟,后来让我加长,我很兴奋,本来海上丝路那段就有段小高潮没加进去,正好。这件作品之后,陈老师叫我加入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组,我有点犹豫,当时正好在忙,后来还是同意了。一是觉得陈老师人非常好,我尊重他的音乐创作和为人,他非常公正,要帮他完成一部分工作;二是觉得,这是为国家出力的好时候。结果去了事情更多起来,要写开幕式倒计时音乐,导演告诉我要体现神秘、天外之音的感觉,而且要用中国元素。可是我后来看见彩排后觉得不需要那么多音乐,只有前面的28秒需要,后面的几分钟基本上用打击乐就可以完成了。击缶的效果已经很好,所以那段音乐创作很简单。
比较难的工作是修改《歌唱祖国》,把一首让人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进行曲式歌曲改成抒情,听着简单,其实很困难。最初的创意是用做薄的乐队,基本上用童声来歌唱,甚至不用乐队,认为那样会更感动人、更温柔。后来还是加上了乐队和和声,加了点铜管和木管乐器。当时创作时正好是西藏自治区发生骚乱的时期,凌晨4点编完,一写完就大哭,发现自己太爱自己的国家了。据说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都哭了,这也是所有工作中我自己最满足的,艰难程度和编配一首歌曲完全不一样。
《丝路》中用“阳关三叠”是按要求进行的,我想要把古琴曲配以和声、伴奏,赋予它环境背景和历史感,当时用了鼓、驼铃,本来还想用羌笛,但是后来这种乐器已经失传了——它是用老鹰骨头做的,最后用了箫,还有人声,还有埙。当时脑海里想的画面没有后来开幕式上展现出来的绚丽,更有旅者的感觉,苍凉而又有文化延伸的感觉。即使是做后来的航海舰队,我也用的是小调音乐,没有用大调,因为我心目中那是含蓄而中国的东西,但是也有磅礴的效果。
虽然是命题作文,可我不感觉很烦恼,命题做文章更难,可是也有好处,更有指向性。我没有写过这么大的东西,加上陈老师要求很严格,基本上提供的是成品,但是整个创作过程我都很兴奋,几夜不睡觉是常事,包括后来写“太极”的后半部分,也始终保持了同样的状态和想法,用西洋乐器来展现中国特有的东西。
我自始至终的创作都很中国,因为这是我们承办者的态度,我们写西洋的东西,写不过威廉姆斯,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创作。4个月的工作,给了我再生的感觉,觉得为国家尽力了,尽管得到的报酬很少,但是,这种用音乐语言来传播中国文化的机会,特别是纯粹的、人性化的音乐,一个人一生中大概也就只有一次机会吧!■(文 / 王恺) 丝路张艺谋意识自觉开幕式陈其钢艺术音乐作曲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