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冠一怒,不为红颜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对战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对战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文 / 刘晨
是夜,月黑风高,一男顶着猪头,张牙舞爪,与同伴蹑足向黑黢黢的城堡走去。俄顷,对面来一卒,狼皮貂帽,鬼鬼祟祟。哇!啊!一两个回合的象声词后,猪头男和他的同伴捉住小卒,耍猴儿似逗他,围着他跳舞,嗷嗷大叫,吓唬他。玩够了,一边说着“我们不杀你”,一边从他嘴里盘问军情。这倒霉蛋筛糠似的,一会儿就全招了。不给糖就捣乱!演到这儿,与美国万圣节之夜装神弄鬼的儿童游戏无异。
但成年人阴险狡诈起来,可以令人发指。交待完毕,小卒求这哥俩放他一条生路,谁知猪头男的同伴手起刀落,眨眼间小卒身首异处,可怜他头滚在地上,嘴里还结结巴巴。
这一幕发生在希腊的“黑暗时代”。猪头男者,奥德修斯也,同行者,狄俄墨得斯。被他俩先辱后杀的倒霉蛋叫多隆,意思是“无名小卒”。这场戏出自《伊利亚特》第十回,古典学家给它取了个别名,叫“无名小卒事略”,特调侃。彼时特洛伊战争已近尾声,两军僵持不下,希腊主将阿喀琉斯偏在这节骨眼儿上负气出走。希腊人攻城不利,一筹莫展,遂派狄、奥深夜刺探特洛伊军情。这哥俩剁了多隆的脑袋,潜入敌营,杀死酣眠中的色雷斯国王不说,还偷走了人家的宝马。
最不仗义的事偏偏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干的,这是《伊利亚特》里最诡异的一段,冷酷而血腥。信奉完美主义的古典学家马丁·利奇菲尔德·韦斯特(M.L.West)认为该书“不纯”,遂得新论:荷马“原”诗并无此书;也即,果然有一个诗人亲笔“写”就的版本。此论一出,颠覆了近百年的荷马学。毕竟,史诗由最初的歌谣经数世纪口口相传才落纸成文之说,几乎已成定论。但对韦斯特来说,找到一个活生生的荷马比什么都重要。2012年,史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把韦斯特的学说推向极致,删掉第十回书,提炼出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纯度”的《伊利亚特》英译本。
讲到这儿,该把这出戏的主要人物介绍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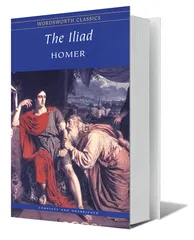 《伊利亚特》
《伊利亚特》
阿伽门农:迈锡尼国王,海伦的小叔子,性格桀骜不驯。海伦被拐走后,阿伽门农带着“亲嫂不回,何以家为”的决心,率希腊盟军远征特洛伊。因此上演出波澜壮阔的《伊利亚特》。
阿喀琉斯:他的脚后跟就不说了。希腊英雄数第一,力拔山兮气盖世。
普特洛克勒斯:阿喀琉斯的结拜兄弟,披其战甲出征,为特洛伊人识破,死在赫克托尔矛下。
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伊萨卡国王,献“木马计”破特洛伊,人称“诡智王”。荷马之后3000年,他被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爵士热情讴歌,又阴魂不散地穿越到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上开史诗先河,下启现代意识。但此人也有虚伪甚至残忍的一面。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打仗,为此使尽坑蒙拐骗的阴招。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带着“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决心,耗尽一个凡人所有的智慧、勇敢、忍耐才得以重返故土。因此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奥德赛》。
狄俄墨得斯:阿戈斯国王,智勇双全。海伦当年待字闺中,他是求婚者之一,美人既已许配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希腊诸豪杰遂立下盟约:化情敌之干戈,成兄弟之玉帛,同仇敌忾。遂携80战舰加入希腊盟军,讨伐特洛伊。他和奥德修斯是把兄弟,但比后者更富正义感,克己自制,又先知先觉,阿喀琉斯出走后,希腊全军上下乱成一团,他却淡定地说:“随他去吧,迟早回来。”后荷马神话中,只有他和墨涅拉俄斯得以永生,其他的英雄死了也就死了。
赫克托尔:帕里斯之兄,特洛伊王子,热爱和平,胸怀坦荡,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男人的楷模。身为特洛伊统帅,亦是希腊人眼中的“无极猛士”,阿喀琉斯的死对头。
多隆:胆小如鼠,但跑得贼快,自告奋勇前往希腊军营刺探。
帕里斯就不说了,金玉其外的小混混,偶因荷尔蒙发作,招致特洛伊十年浩劫。
回到“无名小卒事略”。《伊利亚特》实在是一部很有弹性的史诗,拿掉这一段,仍气壮山河。实际上好多著名段子,譬如海伦私奔、特洛伊木马、阿喀琉斯之死,诗里都没提。在西方最早的文学评论《诗学》里,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荷马压根儿就没打算讲述整个特洛伊战争,而是选择了最后一年最后几个星期的故事,这既是高潮也是尾声。诗的主题已在开篇点破:阿喀琉斯之怒。希腊词μ?νιν,不是一般的怒,是“盛怒”。剧情刚开始,阿喀琉斯就退出了战场。全诗24回,前20回阿喀琉斯一直在生气。
为何发这么大火?都是因为阿伽门农虏走阿波罗祭司的爱女,被天神勒令归还,耿耿于怀,又损人不利己地抢走了阿喀琉斯的女奴。抢女奴跟抢女王,并无本质区别,连海伦也不过是个幌子,女人本是名誉和地位的象征,是战利品。阿喀琉斯说了:特洛伊人又没得罪我,只因我在“漫长而平庸”与“短暂而辉煌”的两种人生之间选了后者,才帮你们打仗。可这“短暂”的意义竟被阿伽门农夺走,实乃奇耻大辱,故退出战场,以“无为”制“有为”。
这一怒,多少英雄战死沙场。荷马描绘死亡的手法不下60种,洛可可式的!这冲冠一怒,貌似为红颜,实则为名誉。然而名誉,终究也是虚幻。痛失亡友,阿喀琉斯才大彻大悟,重回战场,为“短暂而辉煌”践约。
这一怒,引来多少爱恨情仇。第三回,海伦站在特洛伊城墙上看着为她殊死奋战的希腊同乡,纵千金难买一笑。第14回,不可思议的一幕性爱:赫拉要分宙斯的心,精心打扮,勾引丈夫,云雨中,身子底下鲜花盛开。第六回,决战前赫克托尔回家探望妻儿,妻子求他远离战场,他明知特洛伊气数已尽,仍要奋战到底。但他最不能忍受的,乃是娇妻沦为希腊人的奴隶:“有人看见你伤心落泪,他就会说:‘这就是赫克托尔的妻子,驯马的特洛伊人中,他最英勇善战。’你的心中会涌上新的悲伤。”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最终,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决斗,壮烈赴死。全诗在赫克托尔的盛大葬礼处戛然而止。
都是英雄好汉。《伊利亚特》歌颂荣耀、乡愁、命运,唯独不论成王败寇。
历来的英译本,都纠结在“达”、“雅”之间。成诗于晚期青铜时代的《伊利亚特》,得益于爱奥尼克语和其他希腊方言的抑扬格,酣畅、直白、朴素、崇高。译者或重语速,或重辞藻,拟古则艰涩,通俗则降格,顾此失彼。而荷马又是谁?他是目盲还是文盲?是众多无名游吟诗人之一,还是某个文学组织的法人代表,甚或只是后世文人的一念三千?好比红学家为120回本和80回本《红楼梦》争论不休,搞不清谁是脂砚斋,靠荷马吃饭的学者也惘然不辨荷马是“何”马。随着“高纯”英译本的问世,所有的争论都变得非花非雾。但我更关心的,乃是这争议湍流中的砥柱:一种直面人性本真的英雄传统。特洛伊陷落后,奥德修斯与狄俄墨得斯各奔东西,或泛舟地中海,或得道成神。可在大诗人但丁那里,他俩都下了地狱,在第八层受烈火煎熬,永世不得翻身。中世纪基督教背景下的道德审判,与上古希腊人性观之水火不容,由此可见一斑。而比起大写的希腊“黑暗时代”,今人是更文明、更仁慈了吗? 阿喀琉斯特洛伊古希腊伊利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