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日夜书》
作者:孙若茜(文 / 孙若茜)
 ( 韩少功 )
( 韩少功 )
今年第二期《收获》杂志,刊登了韩少功的新作《日夜书》。该杂志的主编程永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这样的描述:“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他描摹了‘左’、‘中’、‘右’各类人形成的自然状态。小说叫《日夜书》,这跟小说蕴含的思想吻合,有白天就有黑夜,有正面就有反面,有左就有右。”
书中这样写那些从白马湖走出来的知青们的怀旧:“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情绪是暧昧复杂。作者在书中对这些同辈人亦是既同情、赞美,又反思、批判,交错的感受都像日与夜、黑与白,难以分解。
对于这些解读,韩少功都表示并不反对。但选定书名,有时作者并没有很深的谋划,依照他的说法,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如果有人说这个书名无甚深意,不过是对时光流逝的一种感慨,当然也可以。”
这部小说的人物背景是知青身份,主要描述当时的知青在当下的生活。责任编辑丁元昌告诉记者,作者在书中反省了知青一代,借用知青群像,更多透视了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正因为叙事重点在这个时代,韩少功也强调《日夜书》不能仅被看作知青小说:“小说不只是关注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工人、个体户和官员,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是一代人的命运。”
近日,长篇小说《日夜书》的单行本出版,韩少功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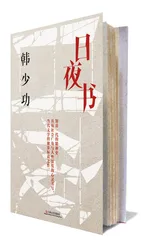 ( 他的新书《日夜书》 )
( 他的新书《日夜书》 )
三联生活周刊:曾有评论说,你从未离开过“知青现场”,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生活层面,选择借由知青群像来透视当下,仅仅是因为熟悉吗?
韩少功:我最熟悉的是一些同辈人。如果我不写这些人,反而去唐朝或火星搞“穿越”,那倒是有点奇怪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关注“知青”、“老三届”什么的,恰恰相反,有评论家指出过,我以前的作品里,知青身份倒是出现得很少,因此我几乎不像个“知青作家”。我不知道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作品似乎更多是借用知青的身份来反省当下?当时的知青在当下的生活,他们的问题和面对的危机,也都在当下。
韩少功:我很高兴你未给这本书戴上“知青文学”的帽子。事实上,哪怕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样一些更大的帽子,或者更专业性和更审美化的帽子,也常常被作品撑破、漫溢、超越,算不上天经地义的。分类贴标签,也许是评论家可以理解的方便,但作家们通常不会自缚手脚,总是跟着自己的感受走,不是跟着一份产品目录走。《红楼梦》、《水浒传》能放到这份产品目录的什么位置?曹禺的《雷雨》算不算“都市家庭剧”?
三联生活周刊:在诸多精神危机、道德危机面前,你似乎都点到为止。你所想要给读者呈现的当下,是一种怎样的面貌?什么是你最想表达的?
韩少功:就认识社会和人生而言,小说通常只是原料供货商,并不负责提炼加工,提出问题但不一定解答问题。我在这本书里力图展示具体生活中的一些精神痛点和生存困境,让读者重视这些问号,也期待理论家们来回应这些问号,如此而已。如果说明确态度,我只是明确反对那种对这些问号的掩盖和麻木。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中有个人物“笑月”,在最后几部分占很大的分量,书的结尾用时光倒流的叙述从她现实的灰暗描绘到儿时的明亮,给整本书留了个光明的尾巴。她对于知青一代的批评甚至诅咒,是否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有关知青的反省?
韩少功:“笑月”对两位父辈人物的激愤,不一定是针对所有父辈,但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我有责任记录这种关系,与读者共同思考,但并未做出是非的裁决。也许裁决本就不是小说的责任,至少不是小说最擅长的功能。我甚至根本不认为这是“代沟”,因为“笑月”的很多同辈人肯定不会认同她的吸毒、搞怪、破罐子破摔。至于小说最后一章中的“我”,可能是“笑月”,也可能不是。那种对人世间的惊喜感不足为怪。生活既是“地狱”也是“天堂”,这通常只取决于你如何看。如果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面,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生活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往的作品,常常在形式上有很多的设计和尝试,而这本小说在这方面则显得更加随意,只是不时地出现跳转和闪回,这么安排有怎样的考虑?
韩少功:这本书通过人物的命运故事展开多种对话关系: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强者与弱者、前辈与后人、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为了凸显这些对话关系,较多地使用跳转和闪回的手法也许合适,可以增强反差的比对。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应该说基本完整和清晰,因此这本书的结构特点,可能更接近有些评论家的说法:“放射状”,就是说几条故事线索有合有分,但并不强求一种人为的集中扭结,在小说中夹杂了一些散文元素。要集中,要扭结,也不是不可以。到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也许会附上一两种情节备选方案,让那些对传统小说模式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完成另一个版本。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有多处关于一个问题纯粹的探讨和议论,比如“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身体与器官”,以及没有加注标题的死亡等等,在这些段落中,情节和人物好像成了用以解说的案例?
韩少功:这些都牵涉到人的“身体”,其实是人文界近些年来十分流行的话题。我采用这种故事专题组合的方式,不过是要行使文学的发言权,揭破身体里潜藏的社会和历史,即“人们未必自觉的文化纵深”。人类有文字、高智能、文化传播、社会组织已几千年了,有些人仍把人看成“发情机器”、“刷卡动物”以及“自私的基因”,实在是过于小儿科。文学如果盲从这个新的意识形态神话,实在有负于“文学作为人学”的职守。作家最应该警觉这一套伪心理学和伪生理学的陈词滥调。我忍不住说上几句,包括回应米兰·昆德拉关于性的一些说法,算是撞上了吧,属于见招拆招的正当防卫。 读书文学小说日夜韩少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