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恩斯的小说
作者:苗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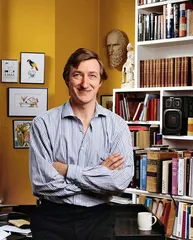 朱利安·巴恩斯
朱利安·巴恩斯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郭教授,你翻译了三本麦克尤恩的著作,又翻译了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这两个作家在英国地位相当,为什么巴恩斯的知名度在中国会弱一点?
郭国良:麦克尤恩和巴恩斯,应该是同一个级别的作家,可以说是世界当代文学中的一流的作家。我有幸翻译了这两位大家的作品。麦克尤恩的代表作应该是《赎罪》,他早期的作品比较恐怖一点,阴暗一点。但是到了《赎罪》,我觉得他的风格完全变了,他的思想非常开阔,《赎罪》触及我们人性道德的高度追求,这和早期的麦克尤恩不太一样。他最近的这一本《追日》,涉及当下一些重大的问题,不是只关注所谓内心,人性当中恶的一面,他在思索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大问题。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视野非常开阔。
巴恩斯的小说没有很大的背景,他关注的还是我们人性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写作风格也不太一样。麦克尤恩机智弱一些,幽默也少一点,走的不是幽默的路子。这两个作家都继续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但巴恩斯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大一些。麦克尤恩玩的技巧少一些。
陆建德: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两个作家还是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非常节省笔墨,有大量的嘲讽,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里的嘲讽也是很厉害的,英国文学里面的幽默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善于把握历史题材,对历史的爱好我觉得好像是英国作家共同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小说并不长,但它的内容又非常丰富。我想请两位谈谈小说长与短,还有重大和轻巧之间的关系。
陆建德:巴恩斯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字谜,然后设置很多的技巧,如果光是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把小说变成一个纯思辨的问题,这样的小说是一个不小的失败。小说还是要用细腻的语言体现生活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能明白的那个东西。读者要去探索很多灰暗不明的地带。这个小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们能够看到叙述者本人在探索自己。巴恩斯一直在注意表面的历史跟实际历史的偏差,他认为历史跟小说非常相近,历史是写出来的,是人为建构出来。比如巴恩斯的小说《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里边谈诺亚方舟,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白蚁,躲到木头里面专门吃木头,藏到诺亚方舟里面去了。他好像从偷渡者的视角来看,从很多不可靠的叙述来做文章。他不断地对历史提问,处处都渗透着他对叙述、对记忆、对官方的怀疑,然后给出自己的叙述。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本小说理论也叫《终结的感觉》,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终结的感觉》这本小说理论说的是什么?
陆建德:《终结的感觉》可以理解为巴恩斯对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1919~2010)的追忆。克莫德的批评著作《终结的感觉:小说理论研究》讨论的是末世论思维与阅读、写作小说的关系。克莫德认为,对终局的预测反过来会影响到对初始和中间阶段的理解,或者说,故事的结尾使得前面发生的一切具有意义。他是从《圣经》叙述出发,《圣经》有一个世界末日到了,然后大家要面对最后的审判。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世界末日的观念,我自己觉得好像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好像我们没有这种叙述,最后的日子到了,他会看原来发生的事情怎么样。
这本小说里是这样——我们觉得叙述者托尼可能是到了生命的终点,整个过程是他的回忆,到最终回忆的时候,原来一些他不太能看明白的事情,慢慢地隐隐约约地呈现出一种模式来,让他看得稍微清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我问郭老师一个问题,现在好多人都会一些英语,可能会对译本提出意见,并且建议说,尽可能看原版小说,你对此有何看法?
郭国良:现在的翻译者面临的挑战性越来越强,原来我们依赖翻译的书,现在能看得到原本。读英语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把英文读通的,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多。能够理解和把握小说的,也不是特别多。另外一个方面,译本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通过翻译,不仅仅把这个小说翻译过来,实际上也是融入世界。出了一本小说,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文字里面就多了一些文化的价值。我觉得翻译译本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可能的话好的东西都是应该翻译过来,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部分。英语永远是英语的和中文几乎发生不了任何关系,翻译成中文以后跟更多的读者有关系。现在对翻译的质疑也很多,译者肯定也要经受考验,经受质疑,有的时候这样的质疑也是蛮厉害的。我确实把翻译当做一个事业来做。我非常荣幸能够翻巴恩斯、麦克尤恩,近些年我基本上把精力放在布克奖得主的翻译上。尽快接触到当代英语世界里面一些最好的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有时候很纠结,比如巴恩斯本人是很聪明的,但是中文有没有体现出来这种聪明,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把握,希望读者朋友多多地提意见,能够不断地完善。
陆建德:我觉得媒体对现在的翻译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现在的翻译不如老一辈,说到老一辈的好像就是我们要高山仰止。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有这种态度。现在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专门从事翻译的工作者,他们做的东西跟老一辈的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像《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充满文化密码的小说到底读者应不应该花时间读它?
陆建德:阅读艰深的作品,梳理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样的读者相对是少数。但是这种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必须有人做。就好像中国有一些特别难的作品,我们觉得是无法翻译,但是还要翻译,它们有它的地位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大的趋势还是回到了讲故事的传统,曾经有一度,像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法国有一些新小说理论家说小说已经死了,故事已经死了,不要再讲故事了,我们要重新撰写。但是我觉得那一阵插曲很快过去,没有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故事还是回来了,我还是希望作家来讲平凡人的平凡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郭老师能否再给我们推荐一位作家?
郭国良:英国好的作家非常多,这个岛国每年的小说量是非常多的,他们的小说还是生气勃勃的。在这样众多的英国小说家当中,我今天特意推荐一下斯威夫特,一个作品是得了布克奖的《杯酒留痕》,还有一个是《水之乡》,如果大家没有读过这两个小说的话,我隆重推荐,尤其是《水之乡》,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学习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会不会对自己有帮助?巴恩斯是学法国文学的,又是英国的作家,他有没有一些法国味?
陆建德:英国小说的批判传统是非常抵制法国的理论,这是英国的保守,也是英国学者比较可爱的一面,他不太会被其他的东西影响。但是英国也是一个出怪人的国家,他们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6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过非常激进的小说家,用完全新颖的方式写书。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有很多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比如鲁迅、茅盾、巴金。并不是说中国文学一定要把外国文学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才会出好作品,这是不一定的。但立足中国本土也需要在想象中把自己从本土里面拉出来,然后跟自己保持距离,跳出来看看怎么样,这样的话会给本土的传统带来一种新鲜的冲击力。
郭国良:我补充一句,法国文学的影响在巴恩斯的小说文本中有体现,他在小说中大量地运用法语,原版当中直接用法语。 文学小说作家陆建德终结的感觉翻译理论郭国良赎罪语言翻译巴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