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子
作者:苗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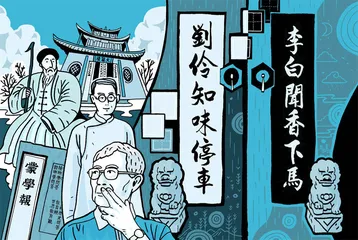 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学六个汉字,天地人,你我他。汉字下面有拼音。遥想1897年9月,蒙学公会在上海成立,创办《蒙学报》。《蒙学报》并不是一个主打言论的报纸,而是按期连载蒙学用书。每册开篇都有“识字法”,图文并茂,第一课也是讲“天地人”三个字,配图是地球,地球上有赤道、有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注解上写着,人立地球上。第六课讲“风云雨”三个字,这一课分为三栏,中间一栏是解说,“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上升”,用几十个字来阐释大气环流生成云和雨的原理,下面一栏的配图是日常所见的风雨现象,上面一栏的配图是“恒风方向图”,已经是很专业的知识。晚清新式蒙学的课本,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语文能力,二是灌输科学知识,不管孩子是否能理解大气循环,先一股脑儿放在这里。
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学六个汉字,天地人,你我他。汉字下面有拼音。遥想1897年9月,蒙学公会在上海成立,创办《蒙学报》。《蒙学报》并不是一个主打言论的报纸,而是按期连载蒙学用书。每册开篇都有“识字法”,图文并茂,第一课也是讲“天地人”三个字,配图是地球,地球上有赤道、有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注解上写着,人立地球上。第六课讲“风云雨”三个字,这一课分为三栏,中间一栏是解说,“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上升”,用几十个字来阐释大气环流生成云和雨的原理,下面一栏的配图是日常所见的风雨现象,上面一栏的配图是“恒风方向图”,已经是很专业的知识。晚清新式蒙学的课本,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语文能力,二是灌输科学知识,不管孩子是否能理解大气循环,先一股脑儿放在这里。
现在的语文课本,大概专注于语文能力。第二课已经有对仗出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古今。”配了一张傅抱石的画。到第五课,是“对韵歌”,课文是这样的:“云对雨,雪对风。花对树,鸟对虫。山清对水秀,柳绿对桃红。”这是《声律启蒙》开头的简化版。
我听过凯叔朗诵的《声律启蒙》,凯叔先读,一个童声跟读,那韵律节奏,听着真是舒服——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这是一东韵。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这是二冬韵。东韵和冬韵有什么区别,我闹不清楚。大学课堂上,老师讲过一点儿音韵学,当时听不明白,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但对对子,我还是很喜欢的。年少时,流行“剪报”,报纸上看到好文章,就剪下来,贴到一个本子上。我肯定剪过一个讲昆明大观楼长联的文章,“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长联一共180字,我当年以为,这就是文笔,就是才华。
后来我才知道有更厉害的炫技,不一定要自己写。俞樾给杭州一座财神庙写过两副对联,其中之一是,“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则财恒足矣,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又从而招之”。这叫“集四书联”,上联那两句出自《礼记》。下联中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出自《论语》;“又从而招之”这一句出自《孟子》。明清学子,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从中找句子凑对。梁启超从宋词中凑过一对,先是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再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李泽厚晚年以一个集句联自况,上联是“悲晨曦之昔夕,感人生之长勤”,出自陶潜的《闲情赋》。下联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出自陆机的《文赋》。这样的集句对,肯定要多读书才行。
文人写出来的好对子更多。作家废名给他的老师周作人写过一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1937年,废名因抗战避难于家乡,在乡村小学里教书,春节前去紫云阁看望父亲,紫云阁的道姑请废名写一副春联,废名写的是,“万紫千红皆不外明灯一盏,高山皓月也都在破衲半山”。这一联也挺好,但更像是应酬,比不上给周作人那一联。
中国古时候不讲语法,对对子就是帮助小孩子理解词性,什么是虚字,什么是实字。1932年,陈寅恪对学生讲过一次“对对子的意义”——妙对巧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间要“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如能上下联并非同一意思,而能合成一文理,方可见脑筋灵活,思想高明。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说:“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借之选拔高才之士也。”我知道“孙行者”对“祖冲之”,“高晓松”对“矮大紧”,等儿子学完第五课“对韵歌”,就跟他聊对子,其间我出了一个上联是“高圆圆”,我自己以现代汉语反义词的方法对以“矮尖尖”,我儿沉思片刻,以自己的小名对曰,“大壮壮”。真是不错的对偶,比我强。
1907年5月10日,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城里遇到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加入了沙畹的考察队伍,雇用一位拓片专家、一位摄影师和一个仆人,一行五人去考察碑碣石刻。考察途中,阿列克谢耶夫记录了很多对联,他说:“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有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他记下一家酒铺门口的对联,“李白闻香下马,刘伶知味停车”。这两个酒鬼到今天还为我国的白酒事业做着贡献,江油有李白故里酒厂,出产“诗仙阁”,而“刘伶醉”是保定名酒。
这一副对联也表明,典故总与对偶相伴,你得知道李白、刘伶是谁。有一本蒙学书叫《龙文鞭影》,其中的句子是这样的,“书校薛涛,禅参琴操”,这是对偶也是典故,涉及两个女子,薛涛和琴操。再举一个例子,“羊子七载,东方三冬”,乐羊子出外求学,学了一年半,思念妻子,就回家了。妻子拿着刀走到织机前跟他说,你看我织布,一点一点才能织出一匹布,如果把织机砍断,以前的功夫就白费了,你学习也应该持之以恒。乐羊子听了,继续外出求学,七年没回家。这是《后汉书》中的一个故事。下一句是《汉书》中的东方朔,东方朔说自己13岁开始学写字,学了三年,读史作文已足够用了。大学问家杨振宁先生,说自己4岁时跟着妈妈识字,一年认识了三千个汉字,此后一辈子所认得的方块字,不超过当时的两倍。杨振宁5岁跟一位老先生读书,读的就是《龙文鞭影》,把这本书背得烂熟。
我是最近才翻了翻《龙文鞭影》,才知道“龙文”是一匹好马,看到鞭子的影子就不待扬鞭自奋蹄,拿现在的育儿术语来说叫“自驱型”(self-driven),龙文就是一匹自动驾驶的好马。像我这样在白话文教育下长大的人,信奉胡适先生的“八不主义”,肯定是不用典故,不讲对仗的。但是呢,我又回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学过的语法,有一节课讲偏正词组,又叫偏正短语,是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包括定中词组与状中词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叫定中词组,修饰动词的叫状中词组。我抄一下百度百科吧——名词前的修饰成分是定语,动词、形容词前的修饰成分是状语;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关系是偏和正的关系。偏正词组之外又有主谓词组、动宾词组等。我觉得,这就是西方的语法套在汉语上带来的麻烦,你知道“老师讲课”是一个主谓词组,还不如背“杜甫诗史,崔光文宗”呢。学语言还是应该在语言中学,对对子就是个语言游戏,比语法好玩多了。
陈寅恪先生说:“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系统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为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老先生又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老先生还说:“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做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性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最近我还读了一本书,叫《国文课》,徐晋如先生写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文脉十五讲”,徐先生认为,中文文脉被新文化运动给断了,中国文学起源于庙堂,是士大夫的文学。以高古雅正为原则,其创作主体是士大夫,是君子,它的受众是读书人,浅俗是它的第一天敌。像胡适这样没文化的人,不懂中国文学的好。徐晋如说,骈体文是中国文学所独有的文体,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民族有骈体文,中国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骈体文,也必然会产生格律诗。中国文字从读音上就分平仄,从字性上又分虚实动静,最宜于对仗。从哲学上看,有阴必有阳,阴阳相生相济,对仗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美学实践。
我们很容易理解汉字的这种特点,对联就体现了汉字的这种特点,单音节,有平仄,有虚实之分,有仪式感。然而,骈文、律诗中的对偶,比对联要求高。前清的举人、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夏仁虎说:“骈体文之对偶,以采色言,不是红对绿;以音节言,不是仄对平。其根本对法,是事对事,典对典。苟隶事运典,皆得其偶,然后再求之声与色。色可不拘,声则不能不讲。六律之调,不必一宫一徵,而金石铿锵,自然悦耳。此中甘苦,固难以语初学,然亦非甚难,第多读汉魏之文,久自能得之耳。”
说来惭愧,我刚刚知道我们北师大还有夏仁虎这么一位教授,他说“难以语初学”,多读汉魏之文,自然能明白对偶的好。我找来几篇汉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太难了,里面有太多的生字。我想,小孩子还是认识三五千汉字就够了,像杨振宁先生那样,认识三五千汉字,再学英文,然后去研究数学和物理吧。知道“于是乎”就行了,至于后面的“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还是算了吧,这比英语难多了。
汪曾祺先生说,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文言的句子。他举《老残游记》中的一句话为例——“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看到这句子,我宛如听见说书人的口吻,这句话太生动了,其中“秋山红叶,老圃黄花”这个对偶也非常简单,不像骈体文似的,还有什么典故,然而,单这八个字也没啥意思,还是要揉在白话里才显得生动。中学生写作文要是能来上这么一句,估计能多得两分。
对偶会不会束缚思想,这事儿我一时琢磨不明白。不过,我看到过一段八卦。日本有个学者叫大桥讷庵,非常喜欢朱子和王阳明,主张攘夷。有人问他,所谓华夷内外之辩,乃是汉土之私称,在汉人看来,我们小日本不也是夷狄吗?大桥讷庵说,华夷这名目的确出自汉土,本来尚义之国是华,尚利之国是夷。我国真天子在也,古来纲常伦理名也,实乃华夏中国。汉土之国唯待我天皇为“对偶之国”,他说:“此乃我国与汉土风俗人情甚近,且我天祖天孙之道符合汉土圣人之教学。圣人之学已备,至于细目条件,文物制度之类,皆以彼为模范。故稍异于众列,被待为对偶之国,乃事理适当之至。”
我小时候就吃过义利食品厂的果子面包,后来才知道这食品厂的“义利”两字出自《大学》,“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义和利,这算是一对儿。但你要说,尚义之国是华,尚利之国是夷,英吉利这样的地方满是唯利是图之辈,需要在“英吉利”仨字之前加上口子旁或犬字旁,以表示他们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level的,那也是很天真的做法。至于说“对偶之国”,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岂是你蕞尔小国日本所能比对的。
(参考书目: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陈寅恪语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三联书店2017年版;徐晋如《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