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日记》:另一种语言
作者:贾鉴 在她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中,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仓促中为刚出生的儿子起名“果戈理”,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作家。儿子夹在双重身份的冲突中艰难成长,他的名字就像一个符咒,幽默而心酸。“果戈理”是个借来的名字,且遥远得与主人公的生活毫无关系。移民世界的“词与物”的脱节是《同名人》的核心问题,十年后,拉希莉用意大利语写成的《罗马日记》,以自传形式更直接地展开对该主题的反思:她为何逃离熟悉的语言?意大利语对她意味着什么?一种新语言能将作家送往自由之地吗?
在她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中,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仓促中为刚出生的儿子起名“果戈理”,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作家。儿子夹在双重身份的冲突中艰难成长,他的名字就像一个符咒,幽默而心酸。“果戈理”是个借来的名字,且遥远得与主人公的生活毫无关系。移民世界的“词与物”的脱节是《同名人》的核心问题,十年后,拉希莉用意大利语写成的《罗马日记》,以自传形式更直接地展开对该主题的反思:她为何逃离熟悉的语言?意大利语对她意味着什么?一种新语言能将作家送往自由之地吗?
除非不得已,否则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为何中途冒险改道外语写作?对于拉希莉而言,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野心的问题,而是与移民后代的文化境遇这一重大背景密切相关。拉希莉出生、成长于英美;父母要求她在家里说孟加拉语,以记住自己的祖国;后来,她成为英语作家,但她的外表又不时被用来提醒她的“外国人”身份。身处这一杂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论孟加拉语还是英语,她觉得都像外语,都不真正属于她。两种语言撕扯导致她的焦虑,甚至发展为对“自身源头的虚空”的恐惧。她赋予这两种语言太多心理症候层面的象征意味,有时显得太戏剧性了。
第一次意大利之旅,拉希莉爱上了意大利语的声音之美。声音唤起某种直觉理解,超越了附加在另两种语言身上的道德内涵,超越了语言中已经僵化了的视觉维度。当意大利语赠予的最初惊喜感消失后,同样会变得越来越“可视”,但她解释说,那是她语言旅程中的第三个点,为她伸展出一条独立之路;再或者,三种语言构成一个三角框架,内部的空白有待填满,也许她想的是一幅自我肖像吧。边框为她留出新的藏身之所,也为她再次刻画自我形象提供了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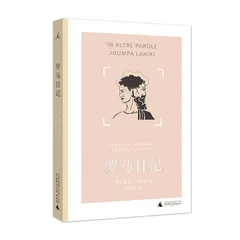 《罗马日记》围绕语言及语际转换问题展开思考,包含诸多次级主题,看似散漫,但仍能读出一个较完整的精神成长故事。在拉希莉笔下,从初期的采集词语,到学习造句,再到尝试用新语言演讲和写作,最终写成这本日记,她在新语言中每一步跨越都是一场历险,有时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意大利语的每个词仿佛都拥有独特生命,那些特殊句型或时态都不只是造句模板而是唤醒记忆的通道;语际转换帮她洞察了旧语言被埋没的光彩,研习意大利经典作家的语言也是对自我认知限度的探查。整个过程中,意大利语不再是工具,而是写作所探究的直接对象,是首先需要理解和领悟的主体。拉希莉非常恰当地将孩童成长的比喻扩展为统摄全书的结构,语言的新生、壮大过程仿佛拥有了自然力。
《罗马日记》围绕语言及语际转换问题展开思考,包含诸多次级主题,看似散漫,但仍能读出一个较完整的精神成长故事。在拉希莉笔下,从初期的采集词语,到学习造句,再到尝试用新语言演讲和写作,最终写成这本日记,她在新语言中每一步跨越都是一场历险,有时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意大利语的每个词仿佛都拥有独特生命,那些特殊句型或时态都不只是造句模板而是唤醒记忆的通道;语际转换帮她洞察了旧语言被埋没的光彩,研习意大利经典作家的语言也是对自我认知限度的探查。整个过程中,意大利语不再是工具,而是写作所探究的直接对象,是首先需要理解和领悟的主体。拉希莉非常恰当地将孩童成长的比喻扩展为统摄全书的结构,语言的新生、壮大过程仿佛拥有了自然力。
书中还有另一类重要的有关地点和建筑的比喻,它们不仅具有结构功能(接榫),而且拓展了主题的思辨空间。拉希莉反复谈到她对孟加拉语和英语的“逃离”,它不仅仅指物理空间上的迁居,在语言层面,“逃离”是奥维德式的既描写达芙妮又描写月桂树的兼容表达,是一个人变形为两个人,是同时处于自由和限制的写作状态。在拉希莉的世界中,意大利语不是终点,它是作家永远在语言之路上奔波的象征。当然,语言变形需要极强的平衡力,如果将“同时处于……”变形为“颠倒”,语言或许面临陷入虚空的危险。
在“威尼斯”一节,拉希莉写道:“威尼斯几乎所有元素都是倒置的,有时候难以区分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幻觉和幽灵。一切都显得不太稳定,一切都可以变化。街道并不坚固。房子好像漂浮着。浓雾可以使建筑隐形。高水位能淹没广场。运河的倒影里,有一座不存在的城市。”威尼斯是语言的幻觉本质的隐喻,不过,威尼斯是一座常常使人的语言意识迷失其中的城市,它启示那些从内部盯视语言太久之人制造出夸张的语言玄学:限制也是自由,距离也是接近,陌生也是熟悉,隐匿也是显现……反之亦然。这类可颠倒的表达在《罗马日记》中到处可见,它们不是对差异的思辨而是抹除差异,它们只是一系列精致的语言和思维的翻新游戏。
语言如世界本身一样不透明,一样充满缺憾。拉希莉期盼在意大利语中解除束缚,重构自我,她能重构什么?重构她在英语中的成功?在罗马街头,她的外国人形象不同样醒目地提醒着她的局外人身份?正如她意识到的,语言以及语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充满隐形的高墙,意大利语的新鲜感穿不透它们。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并未宣示语言的强悍能力,它暗示了语言不能到达之地的广大。
进一步说,上述语言困境还涉及“言说”(更像方法)与“语言”(更像实体)的区别,幸好,拉希莉大部分时间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思想。《罗马日记》包含一种不太显眼但也不曾消失的“中间”意识,当她将语言比作有待建造然后跨越过去的小桥时,暗示的正是这一意识。本书意大利版原名是“另一种语言”,翻译成“罗马日记”倒更符合它的“中间”属性:半私密半公共,徘徊在自我犹疑与渴望沟通之间,徘徊在言语和语言的重叠地带。在日记的中段和结尾,拉希莉插入两个自己用意大利语写的故事,这种形式本身使日记处于纪实与虚构的中间位置。
结尾部分的《半明半暗》(又一种中间性的情绪),讲述了一个有关旅行,有关消失的恐惧,有关未来之真相的故事,与中段故事《交换》对照着读颇有意味:“交换”的勉强实现掩盖不了语言交换的失败,语言如那件怪诞的毛衣,依然是一个外在物;《半明半暗》中的“他”(拉希莉期待的更具隐匿性的人称面具)则最终抵达了语言之外的理解和爱意。海涅有两句诗,用来解释日记的结尾非常贴切:“至爱者的面庞/就是我用的语法。” 拉希莉罗马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