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大观——中唐律赋创作兴盛之探析
作者: 熊建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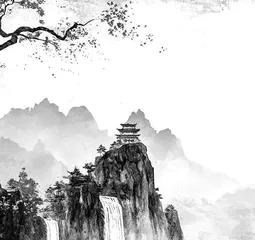
唐人新创之律赋,经过初唐的发展演变,其体制到中唐时已经十分成熟。这时的律赋,一改前代诸种赋体的面貌,相比于汉大赋的鸿篇巨制,体制更加短小,全篇以四百字左右为宜,而其对题下限韵的要求、对偶句类型的多样化又比骈赋更加严格。然而,正是律赋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首要选择,也就成为官方定制。世人想要进入仕途就不得不进行律赋的研习及创作。在这种官方政治的导向下,上至白居易、元稹等文坛大家,下至普通士子,都进行律赋创作,以至大量的律赋作品随之孕育而生,造就了中唐律赋创作蔚为大观的态势。本文从历代对唐律赋的评价简述、中唐律赋创作的特点、中唐律赋名家作品分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窥探中唐律赋蔚为大观之一斑。
一、历代对唐律赋的评价简述
开始对中唐律赋创作的兴盛的探讨之前,有必要把历代对唐律赋的评价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对唐赋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明代李梦阳、清代程廷祚等人为代表的持“唐无赋”的观点。李梦阳在其《潜虬山人日记》中评价道:“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程廷祚在其《骚赋论》中也表达了跟李梦阳大致相同的观点:“东汉以后,始有今五言诗。五言之诗大行于魏、晋而赋亡。此又其与诗相代谢之故也。唐以后无赋,其所谓赋者,非赋也。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尽变与东京,沿流于魏、晋,六朝以下,无讥焉。”第二种评价则是对唐赋持正面看法的,如清人王芑孙,今人马积高等。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对唐赋的历史地位给予了肯定和赞扬:“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马积高在《赋史》中阐述了跟王芑孙相同的肯定态度:“至于近代以后,则主要是人们对它缺乏了解,只看到唐赋以律赋为多,而律赋又多为科举功令的产物,便轻易地把它否定了。其实唐赋不仅数量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即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也超过前此任何一代。”上述李、程二人对唐赋持否定态度是出于其“祖骚宗汉”的复古文学思想的需要,在这种思想前提下,作为“新体”的律赋自然被他们加以贬抑,从而导致了对整个唐赋进行否定的偏执观点。相反,王、马二人则是看到了律赋所内含的价值,从而对唐赋持肯定的态度。总的来说,上述两种对唐赋的看法可以说是因律赋所致,其原因在于整个有唐一代,律赋作品的数量占据了唐赋的半壁江山。据叶幼明《辞赋通论》的统计,《全唐文》中的赋类作品高达1622篇,其中律赋有950篇,约占59%。李梦阳、程廷祚等对唐赋持否定观点的人或许正是因为唐代的律赋远比其他赋体多,而律赋又与其文学思想相背,所以他们也就视整个唐赋而不见,这种因唐赋中律赋数量多而对唐赋进行否定的做法是失之偏颇的。
二、中唐律赋创作的特点
大历、贞元年间,律赋成为科举考试首场考试内容,可以从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中得出这一结论:“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靿中得赋稿示之……”“先榜”即首场考试的意思,李程所示之赋稿就是其登第的律赋作品《日五色赋》。至此,科举考试首场试律赋就成了定制,一直延续到晚唐。在这种科场文化的导向下,创作律赋成为天下士子认真学习的目标,造就了许多律赋篇章,诸多律赋名家也随之登场。清人李调元在其《赋话》中就阐述了这种现象:“唐初进士试于考功,尤重帖经试策,亦有易以箴论表赞而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樊然竟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时名,蒋防、谢观,如骖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为宗。其旁骛别趋,元、白为公……”从李调元这段话中,可以总结出中唐律赋创作的特点:律赋名家、名篇众多,律赋内容雅正。
(一)律赋名家、名篇众多
因为律赋名家多、名篇多,且各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不同,于是这一时期的律赋就有了流派之分。尹占华在《律赋论稿》中将其分为四个流派:“博雅典正派、清绮俊丽派、俊肆豪硕派、平直朴拙派。”博雅典正派代表人物有李程、王起、张仲素,清绮俊丽派有贾餗、白行简、蒋防,俊肆豪硕派有元稹、白居易,平直朴拙派有欧阳詹、吕温、皇浦湜、侯喜。现列举各派别作家的代表律赋作品如下(选自简宗悟、李时铭《全唐赋》),以期观觇中唐律赋创作的大致样貌:李程《日五色赋》、王起《庭燎赋》、张仲素《鉴止水赋》、贾餗《至日圆丘祀昊天上帝赋》、白行简《五色露赋》、蒋防《萤光照字赋》、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欧阳詹《石韫玉赋》、吕温《河出荣光赋》、皇浦湜《东还赋》、侯喜《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上述作家,王起、李程二人专攻律赋,其二人的诗文作品较少,律赋作品独多。李程《日五色赋》中的首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可谓是有唐一代律赋破题的标杆,李程也凭借此作成功及第。王起现存律赋数量最多,其《庭燎赋》深受后人所推崇。李调元在《赋话》中称《庭燎赋》“华而重,典而清,三唐人不知谁与抗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白居易、元稹二人不守常规,以其高深的才力给律赋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李调元称二人之律赋为“旁骛别趋”。白行简、蒋防二人尤擅传奇,其律赋篇章中多见传奇手法。以传奇手法写律赋,不仅丰富了律赋的句式,也加深了律赋的创作主题内涵。
(二)律赋内容雅正
律赋作为官方选材的考试文体,其主题难离述祖颂德、歌颂王治等范畴,所以其内容大都以雅正为宗。王应麟在《玉海》中说:“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这段话是指多用经史子集等经典著作中的语言来进行律赋写作,在中唐律赋中以经典中的句子为题、为韵,化用经典中的句子成文,或直接引用经典中的词语等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是使律赋内容达到雅正的必要做法。现就对中唐律赋中为使内容雅正而引用经典中的内容为题这一现象进行举例(内容出自戴圣著,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大历二年,试律赋《射隼高墉赋》的题目出自《周易·系辞》;大历十四年,试律赋《寅宾出日赋》的题目出自《尚书·尧典》;贞元五年,试律赋《南风之薰赋》的题目出自《礼记·乐记》;贞元十七年,试律赋《乐德教胄子赋》的题目出自《尚书·舜典》;元和五年,试律赋《洪钟待撞赋》的题目出自《礼记·学记》。
由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律赋的题目都出自经史子集。使用经中的语句为题,就为整篇律赋的创作打下了雅正基调,士子在创作时也就围绕该主题选择经中的相关句子进行遣词造句。在封建王朝,儒家思想几乎是历朝维护统治的思想基础,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急需重新稳定时局,所以在科举考试时有意从经典中寻找题目,以达到社会治理的期望。
三、中唐律赋名家作品分析
中唐律赋虽为律赋创作的高峰期,而像韩愈等文坛大家则对律赋评价不高,但另一个文坛大家对律赋的评价则极高,该大家就是白居易,现选取他的《性习相近远赋》(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为例,对其赋的句式进行分析。该赋作于贞元十六年进士科考试,是一篇试赋,该篇赋的破题、承题、押韵、句式等律赋的基本体式成了当时士人争相学习效仿的模板。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白居易此赋在中唐律赋中名气很大,其中对偶句的使用很有代表性,因此选其为例进行分析,以便了解此阶段律赋创作的基本样貌。现录其原文如下(选自简宗悟、李时铭《全唐赋》):
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
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稽其本,谋其始。观所恒,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
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兮,道愈远而。
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亦犹一源派别,随浑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辨惑于成性之所。
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诫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匪乎率道为本。
见善则迁。观诚伪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习性之说,吾将以为教先。
唐人佚名《赋谱》将律赋的句法分为:“壮”(三字句)、“紧”(四字句)、“长”(五字至九字的对句)、“隔”(隔句对)、“漫”(不对偶的散句)、“发”(原夫、是故之类)、“送”(也、而已、哉之类)七种。隔句对又分为“轻”(上四字下六字对上四字下六字)、“重”(上六字下四字对上六字下四字)、“疏”(上三字下不限字数对上三字下限字数)、“密”(上五字以上下六字以上对上五字以上下六字以上)、“平”(上下各四字或五字对上下各四字或五字)、“杂”(上四字下五七八字相对或上五七八字下四字相对)六种。现根据《赋谱》对《性习相近远赋》进行句法分析:壮句,如“下自人,上达君;谋其始;观所恒,察所以”;紧句,如“其旨可显,其义可举;见善则迁”;长句,如“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辨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观诚伪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隔句,如“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亦犹一源派别,随浑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漫句,如“慎之义;诚哉,习性之说,吾将以为教先”;发语,如“原夫;且夫;然则”。
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隔句对共有十二处,该赋中长隔对的频繁使用避免了全篇句式的单一,同时也让律赋节奏充满抑扬顿挫之感。在句法上,该赋打破了通篇“四六”的局限,别具匠心。隔对句的大量使用算得上是律赋的第二特征,而经过科举考试的规范,中唐律赋隔对句的使用大都与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相当,都于严整中富于变化,整篇文章节奏感、音韵感十足。因此,我们可以从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了解到中唐律赋创作的基本体式。
中唐律赋创作的兴盛,固然离不开官方的科举政策的推动,也正因律赋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导致后世学人对其评价不高,甚至有人认为律赋是专为科举考试而特地创制出的文体,这种观点是极其片面的。赋这种文体发展到唐代而律赋兴起,理应获得与诗在唐代发展到律诗兴盛时相同的评价。律赋作为有唐一代之文学代表性文体,在中唐进入发展的鼎盛期,其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