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左翼和平主义根源
作者: 黄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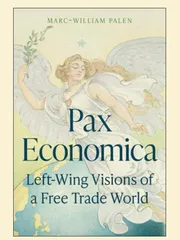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自4月5日起向全球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4月9日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增收额外关税。此前,特朗普已将所有中国内地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0%。中国展开还击,中美关税战迅速升温。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增至125%,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最高可能增至245%。
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的实质是单边保护性关税。特朗普提出这项政策的理由,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视为美国“被占便宜”的证据,试图通过关税壁垒来纠正逆差。事实上,贸易逆差只是表明一国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并不等于损失,更不等于商品出口国获利。现代经济学主张,贸易是互利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体福利,而不是追求账面对等。美国绝非国际贸易中的受害者。进口廉价的外国商品不仅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且美国因具有贸易逆差,吸引全球资本投资美元资产,形成了资本账户盈余。
相反的,提高关税会抬高物价、引发通胀,扰乱全球供应链。1930年,美国实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导致众多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其连锁反应不仅令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而且加剧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殖民扩张,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公然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谴责。那么,自由贸易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的宗旨是否仅限于经济领域,抑或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英国历史学家帕伦(Marc-WilliamPalen)的《经济和平:左翼对自由贸易世界的愿景》一书对此作出了详实的论述,他指出,自由贸易原则的发起和确立,源自19世纪的左翼人士。
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先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便提出自由贸易的理念,但直到1820年代,伴随着英国社会对《谷物法》的强烈反对,自由贸易才逐渐发展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谷物法》是一项对进口谷物征收高关税的法律,它使穷人的食物价格高企,却让地主阶级大发其财。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反对谷物法”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废除保护性关税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曼彻斯特学派看来,自由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全球粮食供应、降低粮食价格来消除饥荒。如果英国能够取消对廉价外国谷物的保护性关税,就可以让每个家庭都有面包吃。换言之,自由贸易比其他任何经济理念都更关注普通民众的经济福祉,主张通过开放的贸易通道,促使各地生产者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
1846年,英国首相皮尔在压力之下宣布废除《谷物法》,普通民众得到了便宜的面包,贵族地主阶层则深受打击。此后,英国逐步削减或是完全取消进口关税,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
对于科布登及其同侪而言,自由贸易不仅可以改善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而且能够削弱各个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甚至有朝一日淡化国家边界,促成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1846年1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我在自由贸易原则中,看到了一个将会在道德世界中发挥作用的万有引力原则,它会把人们拉拢在一起,排除种族、信仰和语言的对立,将我们团结在永恒和平的纽带中。”
在当时,英国是全球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帝国。其他工业化国家似乎理应效仿英国,拥抱自由贸易。但事实恰恰相反。从186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一批工业化国家开始推动经济民族主义,旨在对抗英国的工业化优势,遏制自由贸易的威胁。
自从美国建国伊始,汉密尔顿等政治人物就主张实行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防止英国产品冲击本土制造业。1846年,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影响下,美国也减少并简化了关税。然而,1861年,美国重新启用了严厉的关税制度,成为第一个逆转自由贸易趋势的主要大国。
美国在18 6 0 年代之所以从一度奉行自由贸易转向反对自由贸易政策,除了出于具体的现实考量,思想上的转变主要受到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影响。李斯特生于1789年,卒于1846年,是一位具有强烈反英情绪的德裔美国经济学家。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倡导自由贸易,实质上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工业优势,压制新兴国家的产业发展。李斯特不仅积极鼓吹保护主义,还提出了内容更为广泛的经济民族主义(亦可称为重商主义)。这种经济理念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壁垒、扶植本国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并积极进入和拓展原本封闭的殖民地市场,从而强化国家经济实力。
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一方面旨在阻止英国通过自由贸易来强化其帝国实力;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战略,在保护本国新兴工业的同时实行帝国扩张,尤其是通过进入和拓展原本封闭的殖民地市场来获取原材料,输出过剩资本和商品,以支持作为“帝国”中心区域的本土工业发展。
到19世纪末,法国、德国、日本、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也都采取了类似于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非英国的自由贸易路线。与经济民族主义如影随形的,是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战争与帝国扩张。例如,法国入侵中南半岛,最终建立了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在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美国击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并实际控制古巴;沙皇俄国通过军事征服,将整个中亚地区纳入版图。
既然当时独占鳌头的英国借助自由贸易强化其帝国霸权,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则依靠经济民族主义推进对外扩张,那么,自由贸易与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只是殊途同归,本质并无区别?帕伦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自由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助推了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但从更广阔、更深远的历史脉络来看,它与19世纪末兴起的一场反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延续科布登的理想,一批左翼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者—亨利·乔治(Hen r y G eorge)、马克·吐温、列夫·托尔斯泰、安部矶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J·A·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劳拉·简·亚当斯(Laura Jane Addams)等人—将自由贸易视为推进民主、反对奴隶制度、倡导普选权与公民权利、反抗帝国主义、追求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他们所推动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性社会运动,汇聚了自由派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及“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等多元社会力量,共同追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大同”理想。
倡导这场社会运动的左翼人士认为,自由贸易是通往世界和平的路径。他们主张,若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由极端民族主义引发的仇恨乃至战争将难以为继。毕竟,又有谁愿意向自己的贸易伙伴开战?自由贸易,堪称人类最和平的活动之一。
这些左翼人士敏锐地指出,殖民主义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正是经济民族主义对市场与原材料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积极抢占和瓜分殖民地,关键动机在于对独占资源与市场的诉求,意在通过排他性的剥削与控制,扶持“帝国”本土工业的发展。因此,为了遏制殖民扩张的冲动,有必要建立超越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以制衡工业化国家对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的迷恋,从而推动自由贸易与世界和平。
193 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标志着自1861年以来在美国兴起的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达到了顶点。然而,这一高关税政策加剧了全球紧张局势以及经济大萧条,迫使美国改弦易辙。1934年,罗斯福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开始逐步转向自由贸易。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在他的连续12年任期内,赫尔(Cordell Hull)始终担任国务卿。赫尔终其一生都是科布登的自由贸易理念的追随者,也是民主党长久以来支持低关税传统的坚定继承者。作为国务卿,赫尔主导了“睦邻政策”,推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从军事干预转向经贸合作,为西半球的和平与互信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历史转折期,赫尔积极推动建立联合国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希望这两个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协定能够通过贸易带动繁荣,进而促成全人类的团结与世界和平。赫尔因为这项卓越贡献荣获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左翼人士历经一个世纪所推动的自由贸易与和平运动似乎即将开花结果,大功告成。然而,随着“冷战”来临,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底色的新帝国主义迅速卷土重来。在“冷战”期间建立的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军事干预,以及对全球左翼民主运动的恐惧与压制。
“冷战”背景下,美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由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者倡导,并在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推动下得以广泛传播和制度化。这种源自右翼的自由贸易理念,也逐渐主导了当代学术界与舆论界对“自由贸易”的普遍认知。
然而,这一版本的自由贸易与19世纪左翼人士基于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存在天壤之别。右翼的自由贸易理念并不关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也无意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在实践中它往往沦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实现经济霸权的工具。
里根政府以倡导自由贸易为旗帜,却始终保留着“制定规则与修改规则”的权力。一旦国家利益受损,便毫不犹豫地诉诸保护主义政策。例如,在应对美日贸易失衡时,里根政府对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自愿出口限制”与配额制度,以维护美国本土产业的利益。
如果说保护主义在里根时期尚属权宜之计,那么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则跃升为核心战略。“对等关税”的实质,不过是披着公平外衣的“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逻辑—迫使他国接受由美国制定的经济规则,否则就给予对方惩罚。特朗普政府不仅公然践踏自由贸易原则,更毫不掩饰地展现出对领土吞并的野心与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其恶劣行径,正是19世纪的左翼人士发起自由贸易运动时誓言要根除的顽疾。
面对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多边、双边自贸体系,削减贸易壁垒和成本,提高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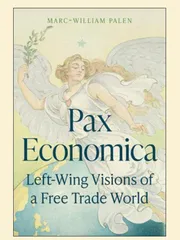
《经济和平:左翼对自由贸易世界的愿景》
作者:[英] 马克-威廉·帕伦(Marc-William Palen)
出版社: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定价:35美元
本书揭示了自由贸易原则的左翼和平主义根源,以及在“二战”以后它的原初宗旨所遭遇的背叛。
马克-威廉·帕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讲师
解读/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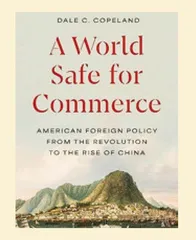
《一个安全的商业世界: 从独立革命到中国崛起的美国外交政策》
作者:[美] 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如何通过商业政策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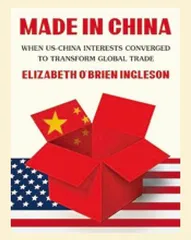
《中国制造:美中如何联手改写全球贸易》
作者:[澳大利亚] 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莱森(Elizabeth O’BrienIngleson)
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回顾了1970年代的中美关系缓和与美国的去工业化如何重构了全球贸易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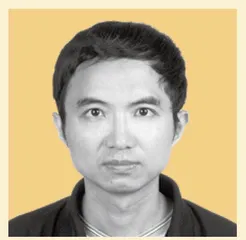
黄湘
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现旅居美国,著有《美国裂变》《审势:洞察世界的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