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启示录
作者: 黄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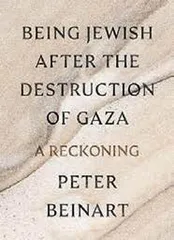
《加沙之后的世界:一部历史》
作者:[印度] 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
出版社: Penguin Press
出版时间:2025年2月
定价:28美元
本书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暴行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背后有着白人殖民者制定的全球种族等级秩序的支持。
潘卡伊·米什拉是印度作家和学者
2025年5月16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将100万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永久迁往利比亚。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这一报道并不属实,但它绝非无稽之谈。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大规模突袭,并劫持人质,以色列随即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并发动地面攻势,造成重大平民伤亡。进入2024年,加沙地区基础设施近乎瘫痪,人道灾难加剧。今年5月,以色列发起新一轮代号为“基甸战车”的军事行动,意图长期控制整个加沙地带,使其不再是一个“人类聚居区”,而是成为一块可以被清空的战略空地。
与此同时,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卡塔尔商业圆桌会议上宣称,美国可以“接管”加沙并将其变成“自由区”,即开发针对有钱人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前提是将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迁往别国安置。在约旦和埃及已公开表示拒绝接收被迁移人口的背景下,关于特朗普计划将100万巴勒斯坦人永久迁往利比亚的报道,显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对以色列的政治批评等同于反犹太主义,以此为由,大举整肃曾经在大学校园里参加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活动的人士,许多国际学生的绿卡和签证因此被吊销。更有甚者,虽然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展示巴勒斯坦国旗,但在公开场合挥舞巴勒斯坦国旗却很可能被执法部门以“扰乱秩序”或“非法集会”等理由而阻止。
事实上,对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全球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不仅美国,许多西方大国普遍表示支持以色列;众多发展中国家则予以强烈谴责,指控其实施种族灭绝。
如何看待这种两极分化?如何理解在加沙发生的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Mishra)的《加沙之后的世界:一部历史》为此提供了一把必要的钥匙。
米什拉指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全球社会面临两场灾难。第一场灾难是以色列以“自卫”的名义,对加沙实施蓄意屠杀与毁灭。第二场灾难则是西方国家的以色列支持者试图掩盖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不仅对以色列的屠杀避而不谈,也刻意掩饰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众所周知,犹太人曾经在纳粹德国遭遇大屠杀。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的突袭与劫持人质事件,确实激起了不少犹太人对另一场大屠杀的恐惧。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不会放过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目标一向就是让整个加沙地带变得无法居住,使得居住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要么被消灭,要么被迫逃离这片土地。
自那时起,以色列领导人多次公然且反复宣称要“消灭”加沙,公众默许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受害者与“无法共存的邪恶”画等号—事实上,大多数受害者完全无辜,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据报道,以色列狙击手多次瞄准儿童的头部开枪。加沙的食物和药品供应被封锁,其学校、大学、博物馆、教堂、清真寺甚至墓地都被有计划地摧毁;在加沙记录以色列暴行的记者,被一个接一个地杀害。
与以往的战争杀戮不同,以色列对加沙的杀戮等于是在网络上即时直播的。无数加沙人,包括许多知名作家和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呼救,称自己和亲人即将被杀害,几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在炮火中丧生。而以色列士兵毫不掩饰地在TikTok上炫耀他们的战果。
西方主流媒体对此刻意选择视而不见。它们或者禁用敏感词,例如《纽约时报》编辑在内部备忘录中指示员工避免使用“难民营”“被占领土”和“种族清洗”等词汇;或者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从而让人难以看清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例如BBC一篇报道的标题写道:“加沙一名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孤独死亡”,而事实是以色列士兵用一只攻击犬袭击了一名巴勒斯坦残疾人;或者公然为以色列辩护,例如《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主张“杀害儿童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加沙所发生的一切,揭示了当今全球秩序的一个冷酷现实:即使是在信息透明的网络时代,以色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力也几乎完全被西方大国容忍且未受惩罚。这一冷酷现实,是在怎样的制度与观念背景下形成的?
很多论者都曾经指出,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反复强化“大屠杀受害者”身份来占据道德高地,给所有为巴勒斯坦发声的人都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
米什拉则看得更透彻,他指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一直以“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份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支持,是因为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叙事和社会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和“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的明确区分。
“Holocaust”(大屠杀)一词,自从1950年代起,逐步固化为专有名词,用以指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实施的大规模系统性屠杀。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是“完全焚烧”,在近现代英语中逐渐泛化为“大规模毁灭,尤其是火焰造成的毁灭”。它之所以会固化为专有名词,原因在于以色列和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机构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从而使得犹太人垄断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群体的地位。
然而,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并非是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惨痛经历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被构建出来,服务于以色列的政治目标。
“二战”结束以后,以色列建国者对大屠杀幸存者长期漠不关心。大屠杀叙事的真正流行始于1960年代,当时的以色列领导人将大屠杀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依据,宣扬以色列是唯一能保障犹太人安全的国家,并将阿拉伯人描绘成纳粹德国的合作者。与此同时,美国犹太社群害怕有可能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与以色列的紧密联系上,在犹太知识精英的影响下,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概念,并深受保守派政客青睐,塑造了美国政坛长期近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氛围。
从1948年到1977年,作为左派政党的工党在以色列长期执政,虽然以色列在此期间实行了大规模扩张,但是还没有明目张胆地将吞并巴勒斯坦地区确立为政治目标。1977年,右派民族主义政党利库德集团上台,其领导人贝京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积极推动犹太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扩张,并且通过与美国犹太社群和美国政治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确保其政策得到支持。
贝京的主要策略就是将大屠杀塑造成以色列的核心历史经验,并以“决不再发生”(NeverAgain)作为口号,宣称以色列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以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次发生。
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堪称贝京的政治继承者,但是更为变本加厉。内塔尼亚胡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的政府,很多政策已经超出了以色列作为世俗国家的定位,包括与极端宗教政党深度结盟,弱化世俗与民主制衡机制,取消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将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视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纵容军队与国家机构的宗教化趋势,等等。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美国和欧洲的全力支持下,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并且几乎完全不受惩罚。
米什拉指出,所有民族国家都会构建自我合法化的叙事,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那样,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如此深刻地被过去的一场历史事件所塑造。以色列通过刻意培养对祖先苦难的记忆,向年轻人灌输特定的历史观,使他们相信:大屠杀使以色列摆脱了一切道德限制,正如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无需再顾虑任何道德层面的束缚,可以不择手段拯救自己。
通过关于大屠杀的历史叙事,以色列的国家暴力在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里享有近乎绝对的豁免权。然而,在米什拉看来,大屠杀绝不是像西方主流媒体和舆论机构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恰恰相反,纳粹不过是殖民主义的延伸,希特勒只是将来自西方世界的白人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民众的暴行引入欧洲大陆,大屠杀是白人殖民者在全球各地犯下的种族灭绝暴行的自然延续。
在长达数百年的西方殖民时代,列强共同维系着一个全球性的种族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下,亚洲人和非洲人被屠杀、恐吓、监禁与排斥,被视为理所当然。白人殖民者无需宣战,便可任意掠夺、压迫乃至摧毁被殖民地区的广大民众;而一旦发动战争,他们更是无须遵守任何战争规则。
在西方主流历史叙事中,纳粹德国的失败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象征着人类历史上极端邪恶势力的覆灭。但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记忆中,“去殖民化”才是20世纪的核心进程—它标志着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持久的系统性暴力的终结。
然而,巴勒斯坦却是20世纪“去殖民化“进程的一个缺口。在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中,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被牺牲在犹太人的民族自决权祭坛之上。
1945年,在“二战”刚刚结束、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在谋求民族自决之际,英国作家奥威尔指出,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肤色问题”。印度的圣雄甘地对此持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从1917年大英帝国支持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开始,巴勒斯坦问题就已经是一个“肤色问题”。当时巴勒斯坦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犹太人只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看来,欧洲犹太人属于“白人”,在列强共同维系的全球种族等级秩序中,他们理应比“非白人”的巴勒斯坦人拥有更多权利,甚至是成为后者的“主人”。
时至今日,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依然是一个“肤色问题”。因此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毁灭性战争,以白人为主的西方大国普遍支持以色列,而许多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谴责以色列。
然而,加沙的浩劫终究还是撼动了全球各地的良知,也唤醒了西方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方社会内部,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了对以色列政策的强烈质疑与反对。而第三世界的年轻一代,愈发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视为更广泛的殖民主义余孽的一部分—唯有彻底颠覆白人殖民者制定的全球种族等级秩序,才能终结以色列被西方话语赋予的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受害者地位,以及由此得到的绝对豁免权。
正是在上述转折意义上,米什拉相信,加沙战争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事件。2023年10月7日“撕裂了时间”,使得“加沙战争之前的世界”成为另一个时代。
解读/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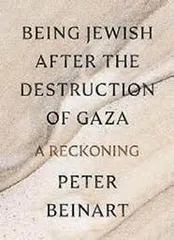
《加沙被毁后的犹太身份:一次清算》
作者:[美]彼得·贝纳特(PeterBeinart)
出版社:Knopf
作者身为犹太人,呼吁犹太同胞在加沙被毁之后深刻反思以色列的道德责任以及犹太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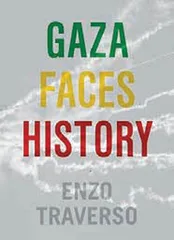
《加沙直面历史》
作者:[意大利]恩佐·特拉维尔索(EnzoTraverso)
出版社:OtherPress
本书指出,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是一场以反对反犹主义名义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它颠覆了西方世界的许多基本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