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运与装潢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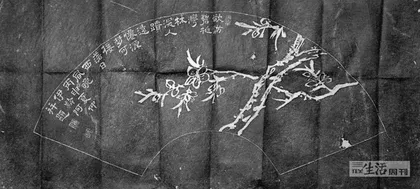 开局添办南三阁的前三年(1782~1784),北四阁全书陆续完竣,四库馆总纂、总阅受到各种奖励,人员变动也较大。
开局添办南三阁的前三年(1782~1784),北四阁全书陆续完竣,四库馆总纂、总阅受到各种奖励,人员变动也较大。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孙士毅擢升山东布政使,离开四库馆,重回政坛主舞台;同月稍晚,纪昀由内阁学士调任兵部右侍郎,成为正式的六部卿贰;下个月,陆锡熊升为大理寺卿,正三品;再过两个月才轮到陆费墀,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可知武英殿丢失底本的阴影已经消散。而因陆费墀在办理文渊阁、文溯阁的入藏排架过程中实在得法得力,弘历对之的好感大增,四十九年正月转礼部右侍郎,二月于南巡途中,复命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传谕:“陆费墀既为侍郎,着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纪昀早就是左侍郎了,却在总纂的位置上一直不动,又哪里敢去说理呢?
作为一个予取予夺的大皇帝,弘历的选人授职不免随意,而多数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时正续办南三阁,虽分为四局,而枢纽则在武英殿,陆费墀长期掌管该殿的实际运转,自属有用之人,也是办理南三阁的核心人员。
有了前面纂办四库的经验教训,增办南三阁全书,远比北四阁的“摸着石头过河”显得更有章法。而没有想到的是,采取按字数付酬的方式后,誊录的效率竟然比之前提高了一倍。先前每人每天写上1000字就显得很用功了,而今每天妥妥能完成2000字。由此也带来了新问题:所聘1000名书手原规划每天缮写100万字,为此选调57名翰林和中书充当校对,按每人每天校阅2万字,应属绰绰有余;现在每天缮成200万字,为保证审稿质量,校对的字数不宜再增添,便出现了大量书稿的积压。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总裁永瑢等奏报此事,提出要增加校对,其中写道:
查臣等前经挑选字画端楷之书手一千名,现在分头缮写,计每人每日写字二千,每月可得书四千本。又经奏定分校之翰林、中书等五十七员,照例每人每日校字二万,计每月仅校得书一千一百余本。彼此核算,每一月所写之书,一二月尚难校清,递积递多,须八年之久方能完竣。在书手等佣书为活,朝夕所需计字给价,势难等久侍。以未经校对之书,不知可用与否,即行给价,殊非慎重帑项之道。将来书手各散,数年后抽换填补,在在棘手,是速写之需急校,事势显然。惟是京员中可任分校者甚少,或本员现有馆属,或本衙门各有应办事件,搜罗再四,实无其人。若照前四部派官总校,则恩□未得屡邀,且铨法更多壅滞。臣等公同商酌,此三分书原为加恩士子而设,拟即于生监中募有情愿校对者,择其文理明通,每人派以三年内校书五千余本,得二十一人足敷办理。如果三部应期全竣,仰恳皇上天恩,钦赐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但不得入吏部举班选用,以碍铨法,亦不许大挑滥邀官职。其有潦草错误者,按季汇送吏部查核,照七品官讨俸之例缴充本馆公用,按年报销,似此劝惩互施,庶期迅速告竣。如蒙圣恩俞允,容臣等陆续召募,有人,即行□书校对,一面将姓名履历咨明吏、礼二部存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四)
上奏此类事情,应提前进行馆内协商,推测和珅也会在面奏时详加说明。该奏以数字说话,字数、册数、誊录和校对的人数皆严丝合缝,当天就得旨批准。
誊录是四库馆流动最大的群体,从抄手到字页的淘汰率都较高,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永瑢也就不给父皇说那些个烦心事了。四库总裁提出的方案是:从生监中考募21名分校,效力三年,事竣后恩赐举人,可以参加会试。这对跋涉于漫漫科举路上的读书人颇具吸引力,报名者必会很多。看来给钱还是敌不过科举做官的诱惑,见军机处方略馆招收誊录又回到老法子,永瑢等赶紧跟进。至于奏本所说不得列入吏部举班,不许参加大挑等,若能考中进士,也就不在话下了。
其时兴办南三阁已展开约一年半,按永瑢的算法,约有三分之一的卷册应已抄成,完成校对的也不会少太多。而校对后仍要逐级送审,但与北四阁差别甚大,总阅官、总裁官皆为抽阅,总纂官似乎已去忙别的了;照例是必须呈进御览的,可到皇上那儿充其量也就是翻翻而已,与之前的睁大眼睛挑错完全不同。为求快捷省便,也为了避免搬运过程的毁损,送审书册皆皇八子永璇所说的“草钉之本”,即完成线订,未加绢质封面。就在这份奏折中,四库馆臣还提出一种新的装潢和发运模式:将“草钉之本”装箱由水路运往江浙两省,附上一套书册封面与书匣式样,以及用纸用绢的材料要求,令其在当地找人照式制作和装裱。这样一来发运较为简便,而江苏浙江皆不乏能工巧匠,办理起来很从容,费用自然也不需要朝廷负担了。
江苏的文汇阁、文宗阁,奉旨交给两淮盐政办理。而朝廷规定盐政“岁一更代”,是以奏请建阁的是寅著,未建成就换了伊龄阿。一年一换制也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就会让一些可信赖的内务府官员接着干,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多次连任。伊龄阿办事能力甚强,也颇得皇上器重,先后三任两淮盐政,合起来共有八年。四十九年初夏,淮关监督全德调任两淮盐政,接的就是新升总管内务府大臣的伊龄阿。全德,八旗汉军人,做事认真,前任已升为直接的上级,可他仍列款奏报伊龄阿交接不清,虽经查明各有原因,已搞得很不愉快。不久后,因运盐河道出现问题,弘历对其大加责斥,顺便说到全德任苏州织造时承办之事办得很好,“调任两淮盐政以来,所办活计两三次不如式,且甚粗糙”,警告他“嗣后于所办活计务宜加意留心,如式成做”。推想全德对承办二阁全书的装裱盛匣,必会加倍小心。
与江苏一样,文澜阁全书的领运装潢也由盐政衙门负责,乃因两浙盐政例为浙江巡抚兼任,也就落在巡抚福崧肩头。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初七,军机处致函浙江巡抚等人,内容关乎已装订成册之南三阁全书的领运,曰:“照得续办三分四库全书处具奏,所有存贮装成书籍,行令遇有便员来京,赴馆请领等因一折,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咨照前来。相应抄录原折,行知遵照办理可也。”这应该不是军机处第一次转发四库馆的领书咨文,也不会仅发给浙江,江苏的两淮盐政全德仍然在任,也会接到领运的通知。至于函件没有提到“装潢”——包括书册的加装绢面、题写书名,也包括制作书匣与匣面写刻文字,因前面早就说过,已不言而喻。而此件到达的下个月,福崧因贪腐革职查办,内务府总管大臣、前两淮盐政伊龄阿接任浙江巡抚,兼办此事,应是驾轻就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