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为何层出不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黎黍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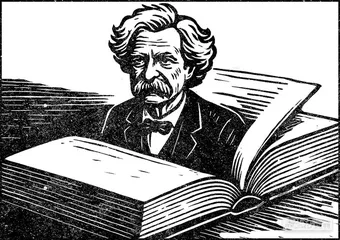 我儿子上初二,晚饭时偶尔会跟我传达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比如“司马迁在监狱里写《史记》”。听到这里,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司马迁在监狱里还有条件写书吗?他到底被关押了几年?他写《史记》一共用了多少年?他妻子叫什么?他有子女吗?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问人工智能,或者去看司马迁年谱、司马迁的自传和传记。
我儿子上初二,晚饭时偶尔会跟我传达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比如“司马迁在监狱里写《史记》”。听到这里,我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司马迁在监狱里还有条件写书吗?他到底被关押了几年?他写《史记》一共用了多少年?他妻子叫什么?他有子女吗?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问人工智能,或者去看司马迁年谱、司马迁的自传和传记。
人工智能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牵连被关了一两年,在监狱里可能没有条件著述,但在狱中他可能已在构思或整理思路。至于他的后人,“《汉书》记载他有一个儿子叫司马林”,这就是胡扯了,司马迁的传记一般都说他儿子的名字不可考,他的女儿也没有留下名字,但她有一个儿子叫杨恽,正是他最早把司马迁的书传布开来。
人工智能不仅搞不清历史人物的生平,更搞不清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的品格是怎样炼成的。美国书评人帕鲁尔·塞加尔说:“传记感兴趣的是传主的性格及其形成过程、错综复杂的动机,他如何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产生洞见,洞见又怎样塑造了他的心理,心理又怎样酿成了他的命运。同一个人的传记之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我们对动机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各种性格理论流行或消退。D.H.劳伦斯的怒火究竟源自何处?是他严苛的童年?对压抑的蔑视?还是因为他体内的结核杆菌?这些年来,劳伦斯的传记作者对这三者都提出过合理推断。”
传记作者试图从干巴巴的书信与档案堆中,召唤出一个真实的人,“如今的传记已不再试图把主体塞进一个解释的紧身衣里,不再硬要将一切矛盾调和为统一的自我,而是承认他们的生活和自我是即兴的、不确定的,是在脆弱的现在时中做出的选择,而非命定的安排。如果说历史让我们像撞击后四散的台球一般,让自由意志成为笑话;那么,传记作家便是那位把球一个个捡起来、吹去尘土、认真研究个体轨迹的人”。
美国人对马克·吐温的认识正是这样不断地推陈出新。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幽默作家、演说高手,善于交际,与多位美国总统交往甚密,但他也“略带抑郁、复仇心切、迷信,而且老于世故”。再比如,马克·吐温经常被贴上现实主义者的标签,其实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幻想家。“如果说威廉·巴勒斯的一生是他各种嗜好的总和,诺曼·梅勒的一生是他各种争吵的总和,那么要讲述马克·吐温的一生,只需要列出他对巨额财富的幻想和他的各种发财计划。”19世纪90年代初,马克·吐温曾去参观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工作室。特斯拉建造了一个可以让人感到愉悦的振动平台,据说不仅能治病,偶尔还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排便。马克·吐温在平台上站了一会儿后,特斯拉小心翼翼地推了他一下,让他下来,马克·吐温兴致勃勃,一再拒绝,然后突然惊慌地僵住了——可能把裤子弄脏了。
美国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刚写了一部1000来页的马克·吐温传,却认为马克·吐温是一个二流小说家——不如伊迪丝·华顿、托马斯·哈代和威廉·詹姆士。对此马克·吐温或许不会生气,他曾经说:“高雅文学是美酒,而我的文学只是水。但每个人都喜欢水。”这句话机智、坦率,也展现了他的禁欲风格,虽然他好像总是离不开一身白色的西装和他的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