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天使在人间
作者: 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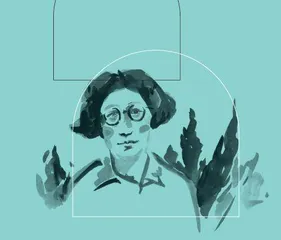
一 楔子
西蒙娜·薇依,曾译西蒙娜·韦伊。作为姓氏,似乎“韦伊”更准确些,因为她还有个著名的哥哥——安德烈·韦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国际数学家大会设有十九个大分支,安德烈·韦伊至少对其中的八个分支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是奥本海默、哥德尔的同事,曾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1906 年生于巴黎,1998 年病逝于美国新泽西,他比妹妹活得长久。很多年后,他谈起妹妹的天赋时说:“我只是一个数学家。”自叹弗如。
西蒙娜·薇依若是知道她死后暴得大名,被偶像化、神化,一定会不高兴。她一生反对偶像崇拜,未想身后被顶礼膜拜,很多信徒来到她哥哥家,只为看一眼长得酷似她的侄女,摸摸她、碰碰她……她哥哥说:“我妹妹一生研究偶像,可不是为了最终成为偶像。”确实,她无意于声名,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最惬意的事莫过于融入人群,用她的朋友梯蓬的话讲,“作为无名者生活在一群不相识的人当中”,具体说,就是生活在劳苦大众中,她对底层人天生有亲近感。
二十八岁那年,她作诗《普罗米修斯》,末句是“孤独而无名,他把肉身交付不幸”。无论从何种角度,这都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后来把这首诗寄给保罗·瓦莱里,大诗人回信道:“强健有力,饱满而生动,除了对您表示赞美,我无话可说。这首诗显示了一种内在的和谐与严谨,这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为人所忽视,也是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们常常意识不到的。”也不知是不是敷衍她,隔年她又寄了一首诗给他,却没得到回音。
值得一提的是,她一生作诗不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保留这些不为人知的小诗,她情愿舍弃自己的所有作品,包括政论、思想随笔、哲学文稿、神学笔记……她没时间写诗,甚至她都没时间写作。
她的代表作之一《重负与神恩》,是她的哲学家朋友梯蓬根据她的笔记整理而成。在编者序里,梯蓬为了将这部非凡之作公布于世而深感痛苦,他认为这有违她的本意,这和卡夫卡与布洛德的关系何其相似。序言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知识分子:“至于那些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知识分子,我对他们相当了解,除了极个别外,他们属于充满幻想的一类人,一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都很糟糕。”
他又说:“那么多的当代作家丧失廉耻,热衷自传和忏悔……这始终令我震惊不已。”西蒙娜·薇依就是那“极个别”,事实上她的身份很难定论,她当然是知识分子,包括行止、思维方式,但她始终不在那个群体里,能逃则逃,她一直跟工农群众在一起。
她对写作认真而严格,曾致信梯蓬:“要像做翻译那样去写作。翻译一篇外文作品时,我们不会设法增添什么,相反,会虔诚地、逐字逐句地什么也不增加。”她留给梯蓬的手稿:十几本练习簿,她的思想日记,夹杂着数种语言的摘录,以及她的批注……语言简洁,富有洞见,梯蓬读后致信她:这些笔记让他非常激动!
她回信道:“对于我头脑中涌现的想法,我别无他求,只希望有良好的寄托。我很高兴这些想法寄于您的笔下,经改观以反映您的形象……您可以认为,这些笔记就完全属于您了。”这封信写于1942 年,彼时二战正酣,她带着父母逃亡美国,那时她并不知道一年后她将辞世。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她预感自己会死,她不乏赴死的决心,这方面她很像谭嗣同。在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说过这样惊人的话:“我怕自己会错过死亡。”
鉴于此,梯蓬才写道,她渴望从自己的作品里消失,渴望自己销声匿迹。她对自己的天赋才华不屑一顾,因为她深知真正的伟大在于一无所是。他把薇依的文字和帕斯卡尔并置,后来,“当代帕斯卡尔”就成了她的别称。她的作品被列入伟大作品之列,梯蓬认为,评论这些作品只会削弱它的价值。本文当然无意于此,实在说,也力有不逮。
苏珊·桑塔格说:“在西蒙娜·薇依赢得的成千上万读者中,能真正分享她思想的人,只是少数。”确实,她的写作涉猎驳杂,从劳工状况到殖民问题,从数学到宗教,神学到政治,历史到哲学……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质的、心灵的,统统汇入她的笔底,她有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哪怕在许多晦涩的篇章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人,她立于人类精神巅峰处那令人眩晕的光芒,而她本人,则是极低极低的,几乎等同尘土。
也有人认为,她的魅力并不在认知,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智者多了去,而像她这样知行合一的人则少之又少;她最大的魅力在于人格,尤其是在“上帝已死”的二十世纪,整个西方都坍塌了,烽烟四起,遍地狼藉,毫无征兆生出她这么个人来,试图从废墟上站起,和上帝重新建立联系,以拯救困苦中的人类,她在中学时就被戏称为“圣女”,自然她对上帝也有疑虑,那么,就当她是天使吧,她活在人间,简直太辛苦!
西蒙娜· 薇依(1909—1943),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大师,著有《重负与神恩》《超自然认识》《在期待之中》《古希腊之源》等。在西方神秘主义思想史上,西蒙娜· 薇依占有独特地位,她特立独行,自甘苦行,永远站在穷苦人民一边。
需要说明的是,她死于战时伦敦,生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未有书籍问世。四年后的1947 年,她的友人梯蓬整理出版她的第一本笔记《重负与神恩》,震惊世人。此后她的著作源源问世,其中加缪功不可没,当时他供职于伽利玛出版社,自1949 年开始,该社出版她的著作共计十一部。
也正是1949 年, 另一位西蒙娜——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问世。两位西蒙娜都生于巴黎,都是富家女,可能两家住得不远,小时候都常去卢森堡公园玩儿。1928 年,两人同时考上大学,薇依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波伏瓦就久闻她大名,诸如聪颖睿智、爱穿奇装异服,这特点她也有,就将其视作同道。她又听说,当薇依听闻一场大饥荒正在中国肆虐,难过得泪流满面,她便心生敬仰,决定会会薇依去。两人是在巴黎大学见的面,当时薇依正在散步,波伏瓦截住了她,上前搭话,两人直奔主题,都不带客套的。薇依宣称,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进行一场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的革命。波伏瓦以同样专断的口吻反驳道: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寻找意义。下面是波伏瓦的记述:
她以轻蔑的神情打量着我,说:“很清楚,你从来没挨过饿。”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我明白,她把我归到“小资产阶级贵族”那类人当中去了,我为此很气愤……我自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
两位年轻女士就这么分手了,当然本来也不是一类人。波伏瓦说:“她的才智、苦修、勇气和奉献精神,我都很佩服,但我不能把她看作我的同道。”是啊,波伏瓦和她的伴侣萨特属于那类单纯的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探寻人类的痛苦和不幸。有论者指出:波伏瓦的基本面是独立、自由……她追求自我实现。而薇依的理想则是无私和自我消弭,她追求成为“奴仆”,正如波伏瓦追求当“主人”一样——哪怕不当别人的主人,也要当自己的主人,她是女权主义之母。而薇依甚至都不认可“女权主义”,有一次有人邀请主持女性话题的研讨会,她拒绝了:“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两位西蒙娜,一位是加缪的熟人,后来闹掰了;另一位他视作偶像。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见过面,薇依生前几乎不交结知识分子,她每天忙得要死。倒是她死后,加缪跟她的家人常有联络,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为了躲避记者,他藏到她父母家里,跟两个老人家闲扯,那里还有她的房间,桌子上有她用过的墨水瓶,窗外就是卢森堡公园。
米沃什认为,她和加缪具有某种隐匿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清洁派信徒,都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加缪甚至加入过“法共”,虽然后来退党了。更重要的是,两人一样的坚定而纯洁,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者”——这一点,女性主义者可能会不同意,因为加缪有不少女朋友。
不用说,米沃什也是她的粉。1980 年他在“诺奖”感言里向她致敬:“她的作品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和加缪一样,米沃什对另一位西蒙娜抱有相当的成见——但愿不是因为那劳什子的“女权主义”。在《米沃什词典》“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个词条下,他写道:“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她死去也没有减弱。现在她迅速滑入了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作茧自缚于法兰西小天地里的她,甚至不知道外人怎么评价她。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所表现的下作……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让她写出《名士风流》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于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女权主义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这个下流的母夜叉。”
米沃什避难巴黎期间,也常去薇依父母家里,在那里度过了无数个下午。他是她的波兰语译者,1958 年他翻译出版了薇依文集,在译本序里他坦承,他不敢标榜自己是薇依思想的信奉者,因为他是个肉欲沉重的信徒,足可见得他的谦卑。
某种程度上,西蒙娜·薇依确实让人谦卑,乃至自卑,因为她身上展现的“神性”多于人性,然而她毕竟是肉身,作为“人”存活于世三十四年,也有痛苦、软弱、彷徨时。她在知识圈有很多著名的男粉,之所以说这句,在于男人很少粉女人。当然了,粉玛丽莲·梦露也是粉,但是较之粉薇依,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粉,男人虽然分得清,却不妨碍他们两个都粉。
在一篇《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的文章里,米沃什写道:“薇依是法兰西对当今世界的一份珍贵礼物。这样一位作家出现在二十世纪,本就匪夷所思,但有时候,恰恰是不可能发生的发生了。”
二 童年
1909 年,西蒙娜·薇依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一年,她哥哥安德烈三岁;萨特、雷蒙·阿隆四岁;波伏瓦、梅洛- 庞蒂一岁;数年后,这几位都将成为她的校友、同行;从亨利四世中学到巴黎高师,这是绝大多数法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这一年,还有一个叫汉娜·阿伦特的德国女孩三岁。至于米沃什和加缪,尚是一团虚无,前者两年后出生,后者更晚,四年后才孕育成形。
西蒙娜·薇依的圣徒气质,自童年时代就有显现,可以说,这是她天性里的东西,此外,环境和教育也是重要的考量,还有她的柔弱体质,动辄生病,三岁时命悬一线。她遗传了父亲的偏头疼,又有厌食症,成年后,她是名副其实的“饥饿艺术家”。有人解读成她有自虐倾向,或者为了穷人而节衣缩食。她当然心系穷人,但生理层面的因素也需考量。这样说,但愿不会亵渎她。
她是个太难养育的孩子,除此之外,这个年轻的家庭别无缺憾——父母恩爱,兄妹情深,一家四口常常出去度假。她父亲是医生,人称毕利,母亲米莫是有钱人家的小姐,祖上是从俄罗斯迁来的,盛世时,光年轻夫妇就雇了十七个仆人伺候。有一回家里来了个亲戚,送西蒙娜一只戒指,她拒绝了,说:“我不喜欢奢侈品!”把一家人都笑翻了。童年的诸多趣事,都可以用来解释这女孩的性格和品质,五岁时她就开始洗冷水澡,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自言自语:“你在发抖,老骨头。”说的是土耳其语,不用说,这是八岁的哥哥教她的,安德烈爱自学。
薇依家的两个孩子,自小就表现了天才倾向,但如果只能二选一,那一定是哥哥而不是妹妹。安德烈八岁就解几何、十岁自学希腊语,西蒙娜也学,但明显更用功,而不像哥哥那样一点就通。邻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就说:“哥哥是天才,妹妹是美女。”这话西蒙娜不爱听,虽然她确实长着一张天使面孔,少女时代她被一个星探盯上了,劝她演电影,被她父母当场回绝,哪能呢?薇依家一向以智力为重。
西蒙娜的不幸在于,她确实有个天才哥哥,把她碾压了,使她长期处于自卑中。她后来致信友人说:“十四岁那年,我很认真地想到死,原因是我资质平庸,而我哥哥天资超人。”她认为哥哥的智商不输帕斯卡尔,这倒好,一家子出了两个帕斯卡尔。
另一方面,薇依夫人也全身心致力于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心性、体格、品质……她致信友人:“每天五点到七点,我得陪西蒙娜做功课,她写字太慢,如果不管她,便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老师告诉我,西蒙娜极有天赋,也很温顺。但在我看来,她的发展极不平衡,某些事上过于超前,另一些事上她又惊人地愚钝。我发现她做事优柔寡断,缺乏自信,我得尽快同她的习性作斗争,我怕以后西蒙娜会受它牵累。安德烈就不同了,对他来说,学习或考试是一种真正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