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命”与拉丁美洲愿景的冲撞
作者: 黄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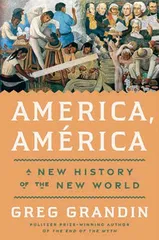
《美国,美洲:新世界的一部新历史》
作者:[美] 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
出版社: Penguin Press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定价:35美元
本书剖析了美国自诩的“天命”与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愿景之间的矛盾与冲撞。
今年1月,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将自己视为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一个增加我们财富、扩展我们领土……并将我们的国旗带向崭新而美丽的地平线的国家。”所谓的“崭新而美丽的地平线”,只能通过夺取属于其他国家的土地来实现。特朗普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吞并格陵兰岛,并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
许多人觉得这只是特朗普个人口出狂言,无须认真对待。但实际上,特朗普是在重新激活美国古已有之,只是在“二战”之后有所抑制的吞并野心。特朗普强调美国具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美国人曾穿越数千英里,挺进那片崎岖、未经开化的荒野。他们跨越沙漠,攀登高山,勇闯无尽险境,赢得了狂野西部。”
然而,“未经开化的荒野”其实是印第安人原住民的故乡,而所谓的“沙漠”与“高山”曾经是墨西哥的领土。美国是通过驱逐、囚禁,消灭印第安人,以及入侵、肢解墨西哥,并吞并其部分领土,来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
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天,特朗普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自16世纪中期以来一直被称为“墨西哥湾”的那片海域改名为“Gulf of America”。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America”就是美国(USA)的同义词,这个新名称的意思就是“美国湾”。但是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America”指的是美洲,包括南美洲和北美洲,因此“Gulf of America”的意思是“美洲湾”。Google地图中文版就使用了“美洲湾”这个译名。
特朗普试图通过新命名来彰显美国对于那片位于美国、墨西哥、古巴之间的海域的主导地位,但因为“America”一词的多义性,他的这项举措变成了自说自话。
“América”是英文“America”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的对应词,用这个词表示“美洲”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来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世界的视角,或者说,一种来自拉丁美洲的视角。美国历史学家格兰丁(Greg Grandin)的《美国,美洲:新世界的一部新历史》一书,正是基于对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视角并置,深刻剖析了美国自诩的“天命”与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愿景之间的矛盾与冲撞。
拉丁美洲的形成,源于自15世纪末开始的西班牙对新大陆的残酷征服。这场征服伴随着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导致了90%的原住民人口的灭绝。它在西班牙天主教内部激发了深刻的道德危机与思想批判,由此涌现出一批以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为代表的反对者,他们断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是不公正的、非法的,是“理应被打入地狱之火的罪行”。他们进而得出结论,世界上所有人—无论其宗教、习俗或肤色—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权利。
这些人在当时未能阻止杀戮与奴役,却推动了一场法律与伦理思想的革命,令下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美洲原住民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生来就是“奴隶”。
相比之下,北美的情况截然不同。清教徒抵达新英格兰海岸时,发现当地原住民社区已被传染病摧毁,大片土地几乎无人居住。殖民者因此心安理得地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占领这片土地。他们幻想自己是新时代的亚当、诺亚、摩西,踏上了另一片空旷的“迦南之地”。
与西班牙人纠结于征服的正义性不同,新英格兰的殖民者发展出了一套为掠夺土地辩护的法律哲学。他们认为,只要一片土地是“无主之地”,就可以合法占领。所谓“无主之地”并不是指无人居住,而是指未曾开垦耕种。英国哲学家洛克声称,财产权的基础在于将人的劳动与土地结合,因此,未经开垦的土地就是可以随意占有的。这一定义完美地符合殖民者的利益。
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进程中,发动独立战争的起义者将自己的解放运动视为对西班牙征服罪行的赎罪。他们认为西班牙的征服是不公正的,对美洲原住民和黑人奴隶的奴役是不可辩护的。以拉丁美洲各国独立战争最著名的领导人玻利瓦尔(SimónBolívar)为例,他本人的血统基本上是欧洲白人,但是他明确批判当年的西班牙侵略者是掠夺者,称其殖民体系血腥而罪恶。拉丁美洲新生的独立国家在原则上承诺给予所有居住者公民身份,令印欧混血人群、印第安人、非洲裔等族群不再受到体制化的奴役。
美国革命则完全缺乏这种意识。美国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宣称,美国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征服的”,殖民是一种“开拓”行为,没有任何过错。美国独立战争的肇因是反抗英国政府对于北美殖民者的压迫,完全缺乏像玻利瓦尔那样考虑将有色人种纳入共同体的设想。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1763年发布《皇家公告》,为了防止北美殖民者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划为印第安人保留地,禁止殖民者越过这一界线定居或购买土地。北美殖民者认为这项公告侵犯了他们向西扩张的权利,遏制了他们对于无限扩张土地的渴望。不止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曾经表示,他们看不到美国扩张的任何界限,只要将印第安人驱逐到落基山脉以西,他们很快就能用白人填满空出来的土地。
对于美国的统治集团而言,边疆被视为一片“无主之地”,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将其据为己有。至于原住民群体,他们被普遍描绘为落后、懒惰、野蛮的未开化民族,不仅被认为不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也常常遭到否定与抹杀。所谓“进步”逐渐成为“领土扩张”的同义词,持续不断地通过暴力征服新的土地,被视为白人文明的不断“进步”
在美国,残酷奴役黑人的奴隶制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道德危机,导致了内战的爆发。然而,美国在领土扩张进程中对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驱逐和清洗,并未像奴隶制那样引发强烈的道德危机,而是被视为美国优越文明的“昭昭天命”。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不过是再度激活这一套话术而已。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战争从1808年持续到了1826年。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宣言,号称“门罗主义”,核心内容包括:反对欧洲干涉美洲事务;美国也不干涉欧洲事务;美国对美洲的旧殖民与新独立国家区分对待,承认欧洲已经存在的殖民地,比如英属加拿大,但坚决反对欧洲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或是恢复被推翻的殖民统治。
起初,许多为拉丁美洲各国独立而战的起义者称赞门罗主义,将其解读为支持他们革命斗争的声明。玻利瓦尔宣称:“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郑重宣告,任何欧洲大陆强权针对美洲、支持西班牙的措施,都将会被美国视为针对自己的敌对行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玻利瓦尔对美国渐生怀疑。他写道:“上帝似乎注定让美国以自由之名,将灾难降临美洲。”
确实,美国的立场是将门罗主义视为干预拉丁美洲的自行授权。1845年,美国吞并德克萨斯;18 4 6 年至1848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战后美国获得包括今天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大部分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在内的大片墨西哥北部领土,约占墨西哥原国土的一半。1853年,美国再以购地方式从墨西哥取得现今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南部。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后,美国吞并波多黎各,并建立对名义上独立的古巴的实际控制。1903年,美国支持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并取得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美国还频繁军事干预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多米尼加等国,支持亲美政权或直接军事占领。“冷战”期间,美国在1954年主导危地马拉政变,1973年支持智利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建立右翼军政府。
美国从未假装尊重他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一贯拒绝签署禁止征服的决议和条约,始终希望为自己保留选择的余地。美国的逻辑是,它对于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征服和干预,是在向那些落后和不民主的地区传播文明和自由。
另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拒绝了美国的“征服逻辑”,同时也拒绝了欧洲的“权力均衡”学说,他们认为这两种思维方式只会导致战争。与这两者相反,他们主张以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拉丁美洲各国独立战争时期,哥伦比亚外交官瓜尔(Pedro Gual)于1822年提出了“按现有状态占有”的原则,主张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边界在各殖民地独立之后应予保留和尊重。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也曾经发生过一些边界冲突,但这一原则在总体上得以维持。
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之后,系统地发展出了一套后来为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奠定基础的核心原则:拒绝承认对所谓“无主土地”的征服权,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在国际事务中一律平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禁止侵略战争,并倡导通过公正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等等。
1889年,第一次泛美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这是美洲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多国会议,旨在促进美洲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拉丁美洲国家团结一致,投票支持禁止征服的决议,美国则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美国代表甚至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从那时起,美国就惯于在多边会议中反对多数派作出的决议,直至今日。
美国在不断发动对外入侵的同时,也参与了国际体系的建设。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入主白宫时提出了面向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尊重拉丁美洲各国主权,强调西半球贸易与合作、反对武力干涉。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在睦邻政策的基础上塑造了联合国的核心理念。事实上,“睦邻政策”的提出,正是对拉丁美洲各国国际关系理念的借鉴与吸收。
然而,美国在制定全球规则时,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美国政府拒绝签署诸多条约,包括联合国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公约、保护被强迫失踪者的公约,对某些条约虽然签署却从未批准,例如《美洲人权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而且会在条约变得不符合美国利益时立即退出,例如,自1986年起,美国宣布不再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是否接受国际法院裁决由美国自行决定。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在名义上一直支持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美国,显然已彻底撕下了这层遮羞布,使19世纪盛行的征服逻辑死灰复燃。他试图重新夺回对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言论,正是这一倾向的鲜明例证。在美国自诩有权不断吞并领土的“昭昭天命”,与拉丁美洲国家所提倡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愿景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二者的碰撞,或将为西半球的历史进程揭开新的篇章。
解读/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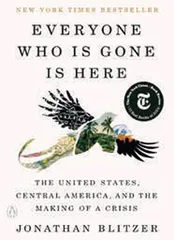
《消失的人都在这里:美国、中美洲与危机的形成》
作者:[美]乔纳森·布利兹(Jonathan Blitzer)
出版社:Penguin Press
本书讲述了美国对于中美洲腐败政权的支持,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众被迫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加之美国百弊丛生的移民程序,最终造成了美国的边境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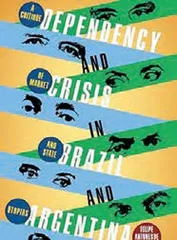
《巴西与阿根廷的依附与危机:市场与国家乌托邦的批判》
作者:[美]乔纳森·布利兹(Jonathan Blitzer)
出版社:Penguin Press
本书剖析了巴西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结构改革循环,并运用依附理论针对两国的发展提出了另一种政治经济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