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论》:辩证方法论的准备和实践的检验成果
作者: 孙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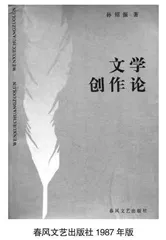
方法论的准备期和艺术营养期
说起《文学创作论》的写作,一是偶然中有必然,二是困境中的无奈转化为意外的成功。它和我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命运的转折紧密相关。
1960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读研究生,这绝对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投考北大中文系,就是奔着当作家的目的。当时我已经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过诗和散文,现在看来很幼稚的,可是居然收到了三封读者来信,一封还来自新疆。本来有“孙悟空”的雅号,又加上一个“高尔基”。我当时最高的志向就是当一名作家,小小的也成。但是,自己缺乏工农兵的生活,没有希望。恰好一本苏联小说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风行起来,那本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作者本是化学工程师,在边疆建设中有了生活体验,就成了名作家。我当时的化学成绩特好,至今还能背得出化学元素周期表。我最崇拜的就是编出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这个人真是太伟大了,居然能把全宇宙所有生物、无生物非常有序地概括在一张表格上。真是太令人惊叹了。这样精致的秩序,连上帝、佛祖都没有提供。莎士比亚说,人的名字听起来是多么骄傲,我觉得应该是,门捷列夫的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要当作家,就考化学系,将来建功立业,再实现作家理想。
1952年开始全国高校统一考试,我1955年高中毕业,根本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来指导我如何报名,彷徨了很久不知道如何是好。晃晃荡荡走到教师办公室门口,我很敬重的卞纪良老师(他是当时很重磅的《英语四用词典》的编者之一)问我填了表没有,我说,不知道怎么填呀!他说,你肯定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时,老师是的话有如圣旨。我就怀着当作家的梦,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但是一开学,系主任杨晦先生就宣布本系的培养目标不是作家,而是学问专家。我不免失望,可看到学长们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大都在高校、研究所,或者文化机关,觉得也还不错。分专业填表时,我填了新闻专业,心想毕业后可以大走四方,接触工农兵的生活,还是可以当作家的。但是系里没有批准,留在了语言文学专业。我心想当学者,当大学教师也挺荣幸。但是,古代汉语辅导课,来了个讲师,四十多岁,面色都有些憔悴了,一学期就上了两次辅导课。我暗想当这样的大学教师,是不是有点青春虚度呀?生命只有一次,就这么一点贡献,太对不起自己了。当时比我早一年入学的刘绍棠,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就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在全国算是有一点名气的作家。他就从北大退学,当专业作家去了。
我在中学时期对作家就十分仰慕。仗着自己数理化成绩比较好,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课外阅读文学作品上,可以说是狼吞虎咽,同时还钻研文学评论。回忆起来,好像绝大部分是失望的。那些评论中所谓的人物刻画,大都是情节复述,讲到艺术特色,就是三言两语,还不着边际。我想作者们之所以讲不出名堂来,就是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可是中学政治课本发下来,教师还没有来。我就自学,不满足,找政治理论刊物补充,可昆山中学图书馆没有理论刊物,只好每周星期天步行到昆山图书馆,阅读一本叫《学习》的政治理论杂志。
读了一年左右,觉得自己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了,颇为自得。此时,政治教师来了,刚在苏州培训了四个月,除了照本宣科,讲不出什么名堂。我把注意力转向文学理论,连胡风很艰涩的《现实主义之路》《从源头到洪流》都读了,似懂非懂。但是,有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很实在,他举的好多例子,我至今也忘不了。如,屠格涅夫写一个老太婆死了,只用了一个细节:一只苍蝇从她蓝色的眼膜上从容地爬过去。另外一个例子大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铜板掉下来,很抽象,要写出它叮叮当当沿着台阶滚过去。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还读了巴人的《文学初步》,其中讲到王独清的《我从咖啡中出来》那首诗,也挺好。不过他后来改成了《文学论稿》上下两册,太理论化了,读来很是隔膜。当时只要有一点触及文学艺术奥秘的文意,我都过目不忘。有一篇苏联的《给工农通讯员的一封信》,讲叙述和描写的不同,举的例子至今还历历在目:第涅伯河在地理书上是很简单的,就是发源于瓦乐代丘陵,流经乌克兰南部,注入黑海。而在果戈里的小说中,则是第涅伯河静静地流着,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岸边大车上坐着的姑娘和她的红头巾。读这样的文章,我感到很过瘾。当时阅读的胃口很大,连苏联的大学文艺理论课本,季莫菲耶夫的三大本《文学理论》都买来读了,半懂不懂,囫囵吞枣,困惑多于收获。
进入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课却是季莫菲耶夫的弟子、基辅大学副教授毕达可夫留下的讲义,那种机械僵硬的反映生活论,令人失望。1956年百花齐放时期,请了北大文学研究所的权威教授蔡仪讲美学。起初很轰动,因教室太小,就转移到了办公楼上的小礼堂。但是一学期听下来,只记得四个字“美是典型”,黄金为什么是美的?因为其金属属性在人的感觉中是典型的。那时,君临整个文坛的乃是俄国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到了大学二年级,有点反思的本钱了,已经得知这个观念来自他1860年的大学毕业论文。我的反叛思想后来写在一篇论文的开头:
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花是土壤,我们会遭到嘲笑,因为混淆了花和土壤最起码的区别,或者用哲学的语言说是掩盖了花之所以为花的特殊矛盾。同样,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回答说酒是粮食,我们也会遭到嘲笑,因为粮食不是酒,这个回答没有触及粮食如何能转化为酒的奥秘。然而,在文艺理论领域中,当人们问及形象是什么、美是什么时,我们却不惜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去重复这样一个命题:美是生活。
当然,在实际行文中不会这样简单地托出一个线性因果关系,但是,不管经过多少曲折的环节,所强调的却是生活与形象的统一性,生活起决定作用,作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思维定势效应甚至影响到一些作家写的创作经验。当他写了一个好作品,他就说这是由于深入了生活;当他写了一个失败的作品,他就说因为脱离了生活。从唐诗的繁荣到现代文学的崛起,凡是要作理论的描述和说明,思维似乎就只有一条途径可循——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性,作家反映生活不能不带有被动性。光知道粮食可以酿酒的人成不了酿酒的能手或酿造理论家,可是,反复强调形象就是生活,不厌其烦地混淆生活与形象的区别、漠视作家的主体性的人,却往往成了永远“正确”的文艺理论家。如果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运用自然科学的逆推理方法,从相反方面提出问题,说酒就是酒,它在本质上不再是粮食,形象就是形象,它在质的规定性上已不是生活(虽然它可以在另一个层次上和生活有同一性),虽说这不过是讲出了起码的常识,反而有可能遭到嘲笑,被认为是奇谈怪论。
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比之把形象和生活的统一放在纲领性地位的人要聪明一些。创作之所以称得上是创作,就是从摆脱对生活的被动依附开始的。只有摆脱了被动状态,重视生活与艺术的矛盾,作家才可能获得创作所必需的内在的自由。a
主流理论这样令人厌倦,我就去读朱光潜先生的的文章,读了不少,对我很有冲击力。我从宿舍32斋四楼可以看到他的小洋房,就写信给系里,要求请朱光潜先生讲美学,结果石沉大海。我觉得许多风行一时的评论家对艺术奥秘大而化之,原因在于没有思想。我深深感到北大中文系缺乏一门系统的哲学课。我并不指望系里马上就开出哲学课程,就非常注意报刊上的哲学文章。当时,在学样的大马路上,北海公园的仿膳斋,时常看到长须飘拂的冯友兰先生,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哲学文章,我常常站在阅报栏前一口气读完。记得他解释《易经》八卦的乾与坤的辩证转化,很通俗有趣。还有一篇讲的是对中国传统观念不能光批判,应该“抽象继承”。如忠孝观念可以取其文,而输入时代的新内涵。这些,对我的思想都有触动。当时李希凡因为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学术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我想他大学刚毕业不久就能写出轰动全国的文章,一定是因为他的哲学基础坚实,就写信给他请教如何学哲学,结果是杳无音讯,我就自己发奋钻研。不知是谁推荐我读恩格斯的《费德里希·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的终结》,那个难度可真是太大了,光是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就比原文还长。功课很紧,俄苏文学史不过一个学期,光是长篇小说,就有屠格涅夫五部、托尔斯泰三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起码三部,还有肖洛霍夫三部,还没有算上普希金的诗和诗体小说。我的求知欲又旺盛,必修俄语之外坚持读英语,还选修了法语,还要关注报刊上的论争。就决定午睡不脱鞋子,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一翻身,就掉下来,马上起身去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稍有一点时间,就抓紧啃读恩格斯的那本书,时时有啃不动之感。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b,被普鲁士国王和臣民认为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辩护,但是“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c。看不懂,就反复看,一有机会就看,看了不下十次,有一次是靠在暖气管边上,终于看懂了:这就是说对立面,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反面转化。有了这个观点,我的思路就打开了。矛盾、对立、统一、转化,这个观念虽然当时还不是很明确,但奠定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成了我看待生活和文学的方法论。
我的研究生专业属于现代文学专业,我在1957年前后被改成助教,调到华侨大学。我带着北大那种自由学风,胸无城府,直言无忌,冒犯了只念过一两年大学的系主任。上了一年的课,就从讲台上跌落下来,近十年的时间只能给一位讲师改作业。两三个星期只改二十篇作文。从印尼归来的华侨,每篇只有四百字,工作量非常小,我一天就可高质量地完成。当时每一秒都是我的。我可以自由阅读,满足我永不餍足的求知欲。我在华侨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回忆文章这样写:
上世纪六十年代,怀着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虔诚……我就更加致力于于矛盾统一、辩证法的钻研,系统阅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有好几年,我基本上不读文学方面的著作,只订一本《哲学研究》。虽然读过恩格斯的《费德利希·费尔马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是,找不到一本权威的辩证法的经典。看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马克思没有写过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全在他的《资本论》中。d
我就去钻研《资本论》,那比读恩格斯要艰巨得多,花了两三年工夫,应该说,至少读通了前两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没有从葡萄牙、西班牙平分世界的殖民开始,也没有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毛纺业的发展导致“羊吃人”的惨剧,更没有历数欧洲殖民主义贩卖黑奴的罪恶历史,而是抓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常见、最普通的范畴——“商品”,揭示其内在矛盾: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转化为抽象劳动的交换价值。交换过程中以社会平均劳动量为准,总体来说是等价交换,但是,对于工人的劳动力来说,则是不等价的,资本的本质乃是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工人的贫困化,资本利润越大,工人越贫困,购买力越小,商品生产的竞争力却越强。商品为社会所用,而生产资料为私人逐利所决定,商品生产乃盲目扩大化,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故资本主义从萌芽、发展、兴盛,最后走向反面。原因不在外部,而是在“商品”这一范畴内部矛盾的转化,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逻辑和历史达到高度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博大精深的严密体系深深震撼了我,原来理论可以这样精密,逻辑是这样严整,系统是这样自洽。
在心灵深度震撼之时,我还读了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资本论》权威著作,结合张世英先生的《小逻辑解释》,还硬啃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在哲学上有了坚定的立场,那就是:自然、社会、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其动力乃是内在矛盾,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向反面转化。当时并没有想到日后做学问,只是为自己的世界观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高度而自慰,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直在发展。我在回忆中这样说: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我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注解,来来回回读了四五遍。加上此前我还读过手抄本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纲要》十讲,体悟到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乃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每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乃是特殊矛盾。
建构文学创作系统理论的机遇和挑战
后来我写《文学创作论》,说来有点冒险。因为1973年,已经解散了两年的福建师大复办,调进福建师大,条件就是只能到写作组。这个教研组向来是中文系的西伯利亚,没有什么理论可讲,改作业是手工劳动,在学术上没有前途。好在“文革”期间,这门课程是“开门办学”,只要做一个报告,带着学生到老红区和沿海前线采访英雄故事,几个月时间,帮学生修改作文,最后能选一些优秀的文章,出一本小书就很不错了。但是,1977级来了,要正规上写作课。当时只有两位写作教师,一位是新闻记者,领导就说,那就讲“基础写作”;孙绍振,你会写诗,就教“文学创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