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地情结与青年写作的三重维度
作者: 李晨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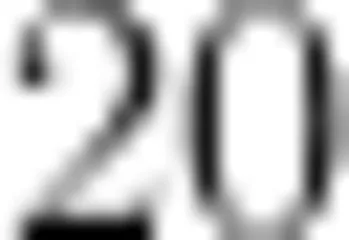
所谓"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源于希腊语而后引申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概念,如学者段义孚所言,这个词语旨在全面而精确地表达人类对物质环境所蕴含的种种深厚情感联系。对于人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沉淀在人类共享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恋地情结"成为青年写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它不仅是作家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地方文化、历史记忆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映。
毋庸讳言,地方性元素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恋地情结"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不仅是作品独特性和深度的源泉,丰富着作品的情感层次,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是连接作品与读者情感、文化认同的桥梁。因此,对新时代青年写作中的“恋地情结”进行深人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和风格,还能够揭示地方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
一、从乡土传统走来的创作倾向
依据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当下的青年写作还蕴含了一种价值评判②,即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尚未达到经典化的地位,其艺术风格仍处于塑造与变化之中。“在每一个自我确证的文本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对于当下与自我的纠结和张力,但这种集体絮语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时代之音的表达…如何从青年写作的情绪出走,进入更为深邃宽广的中年写作,从而以经典的面目进人当代文学史叙述成为一种必然。”③基于此,青年写作的突围已成必然之势。参考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文学现场,彼时的青年作家如莫言、王安忆、苏童等同样身处一个求新求变的上升期,他们的小说则以鲜明的地方性元素杀到台前,从地域出发,再到超越地域,以高屋建瓴般的当代意识成就一代经典。他们的艺术选择应当对当下的青年写作有所启示。
在20世纪的中国,以知识分子立场书写地域文化的小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是以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而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则是以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同样是以知识分子立场介人地域书写,启蒙与诗化这二者依据两种不同的现代精神: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前者更多地“依据科学和现代理性精神,以批判的眼光,去摧毁现实与传统中不符合自我构筑的现代图景的因素”《故乡》中闰土等农民形象在兵匪官绅的层层压迫下,表现出的是痛苦而不自知,唯有蒙味的麻木。事实上,从蒙昧麻木到可感知痛苦,再到“呐喊"出声的过程,正体现出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化小说书写内容的变迁。后者则“更多地依据民主和人道主义精神”,将丑陋与冲突化解为美丽与和谐,进人到诗意化的审美境界,并"以审美眼光去发现和构筑人性中潜在的符合自我构筑的现代图景的因素”。④譬如在汪曾祺的《受戒》中,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两小无猜的朦胧爱意超越了现实中的宗教教义。作家在结尾绘制了一幅图画:明海与小英子的小船划入芦苇深处惊起一片鸟群,这一情景的言语留白淡化了情节的冲突感,在诗意的和谐中留下了小说的余韵。在这一传统下,诗意化的世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乌托邦,乡村成了文人乌托邦的最佳外化情景,成了作家们寻找诗意、寻找浪漫、寻找人性寄托的最有可能的去处。
毋庸置疑,无论是启蒙,还是诗化传统,这些地域文化书写样本都脱离不了“乡土小说"阈定的界限。自鲁迅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几乎无一不是通过“乡土小说"这一载体来进行实验的。“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再是指那种18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作品,它是在工业革命冲击下,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生存共同意识,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任何一个民族和阶级的作家都希望站在自己的视域内,用‘乡土小说这个‘载体'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③这也是缘何乡土文学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消失,反而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土传统塑造了青年作家的写作观念和风格。在乡土传统的熏陶下,青年作家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更加注重对人性、情感和社会问题的深人挖掘。这种写作观念和风格不仅使作品更加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使作品更加贴近读者、更加引人入胜。新一代青年作家在继承乡土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特点,对乡土文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使其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富有时代感。
正是在承继了过往乡土传统的思想、审美以及哲学精神的背景下,当代乡土写作呈现出复兴与演变的趋势。学者丁帆在20世纪90年代已对地域书写作出了展望:“它只有在当代意识的统摄下,在审美观念的不断更新中获得存在的价值,获得向世界文学挑战的地位。”?那么,何为当代意识?诚然,当代作家笔下的“还乡记”之中,乡土已经由外向内地产生了裂变,比如物质文明尚未辐射至其中,又或是乡土社会人伦道德的失衡等问题。作家们总是在失落于“乡愁”的同时,渴望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式的精神原乡。有意思的是,人们愿意回到的桃花源只是精神上的,绝非现实中的,物质生活的便捷已经完全改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人们更渴望的仅仅是“农家乐”式的偶尔体验罢了。这也就带来了“城乡融合"的必然之势。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乡村,用笔墨记录乡村的变迁和发展,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情感。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在主题上,新时代乡土写作更加注重反映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关注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社会问题;在风格上,新时代乡土写作更加注重创新和多样化,尝试将现代文学元素与传统乡土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加新颖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
二、文学书写的两种地方性路径
在当代文学创作的广阔舞台上,青年写作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力和无限的创造力,成为推动文化多样性与创新的重要力量。其中,地域元素作为每个人不可回避的地方性资源,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青年写作。青年作家们以笔为舟,在地方性资源的挖掘与转化上,探索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的微妙平衡,展现出丰富多元的艺术风貌。这其中,“恋地情结”鲜明地表现在两种典型路径上。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yzjl20250316.pd原版全文
其一,“新山乡巨变”,即从旧到新的巨变照应着地域书写的典型路径。小说的经典气息,往往建立在对于时代的回溯性叙事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从“城乡互见”下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再到当下城乡融合的包容共生,“新山乡巨变"成为地域书写时代发展强有力的注脚。长久以来,文学始终在“城”与“乡"的二元对立中徘徊。事实上,广义的"乡土小说"定义中,“乡土"与“城市”是互为对照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组动态平衡的批评坐标系。而"乡土文学"最具价值的一面也是当人类渐次迈进工业社会的阶段后,其母题因为有了工业社会视阈下“共通视角"的观照才显示出来的。“城市”作为“乡村”的背反物,使作家更清楚地看到了“乡村"的本质。于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一方面是对那一片“净土"的深刻眷恋;另一方面是对“乡村"的深刻批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愁"便包含了批判的锋芒,而“异域情调”又饱含着对“乡土"生活的浪漫回忆。这种背反价值的交织,几乎成为20世纪每个乡土小说作家共同的创作情感。而隐含于这一背反律下的,是作家创作观念呈现出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也即有时用经过文明熏陶的"城市人"眼光去看“乡下人"和"乡下事”,有时又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去回顾"城市文明”。于是,地域书写就在更大程度上延展了其多义性。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周荣池的《单厍》魏思孝的《土广寸木》等长篇小说正是在拆解“村庄"的意义下,展现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这一路径见证了青年作家如何深入乡村肌理,捕捉到时代变迁下乡土社会的细微变化与深刻转型。他们在记录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与新生活形态的兴起之时,更在旧与新的交织中,探寻着文化的根脉与未来的方向,赋予地方性以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乡土写作的复兴与演变,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在世界朝着后工业时代发展时,自20世纪中期发展至今的小说中充盈着一股“现代人的焦灼感”。而这股“现代人的焦灼感”在“新时期”前后或许还有对西方社会浓重的模仿意味。究其根本,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较之西方社会具有整体的时间滞后性。换言之,西方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如工业化造成的失业潮、进城与怀乡的焦虑、城市中人们的精神困境等,当下的我们业已体味到了。事实上,“新时期"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渐次脱离了苦难的"浸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始的“启蒙”"救亡"意识也逐渐变为“自强”“自信”的人生信条。在更多的青年一代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对外来文化扭转了观念,从拒斥走向接受,再走向主动对世界敞开中国传统文化怀抱的文化自信之路。21世纪以后,中国人的艺术情趣和思维方式,甚至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大大地改观。然而这一事实也印证了人作为高级动物对于精神家园无穷尽的追求心境。哪怕如今的物质生活已经足够丰富,科技发展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可人类始终无法安然地享受静止在一种形态的生活中,我们始终不能摆脱精神的厌乏和审美的疲惫。诚然,新时期以后,小说的确陷人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另一极端的处境中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地方书写在先锋小说的表现形式中重新将审美精神拔高到应有的位置。而如莫言、残雪、刘恒等以“有意味的形式”进行地方书写的这些作家们,其创作精神仍然滋养着新时代的创作者们。事实上,新时代的小说在表现形式与反映生活内容上,企图达到一种更加平衡的美感。
其二,地域书写在从“小"地方到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过程中,内含着中国作家主观观念与客观现实合力作用的变化。之于20世纪,这一从“小"到“大"的历程耗费了中国作家太多的心血:“使中国文学走出中国”始终是横压在中国作家心头的一大心病。作家们从地方书写出发,作品中对特殊的地理样貌、民族图腾、风土民俗、方言土语以及地方性思维方式的描写仅仅只是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经由其展现的一项手段,而更深一层的用意却在于站在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来鸟瞰民族文化精神本身,也就是把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参照系中进行平衡,使两者在演化中互渗、互补、互融而成为一个崭新的有机的整体文化系统,完成人们从“五四”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国民性改造大计,拥有一种对国民灵魂重新把握的魄力。
在这一意义下,当学者们纷纷对当下青年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从“地方到世界”即成为必由之路。“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作,最终也需要落实到地方,借此获得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异性。”③这要求青年写作需要具备全球化视野,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辐射至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探讨普遍的人性议题,展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地方性资源成了连接全球对话的桥梁,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共生与相互理解。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庞羽在《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中捕捉都市生活的趣味体验,以全新的方式书写这座世界文学之城;秦汝璧的《夜里没有狗吠》描述了一个从高邮漂泊到黑龙江、上海等地的男人,其漂泊轨迹与归乡的执念形成张力,映照着以地理迁移寻找归属感的徒劳;孙频在小说《落日珊瑚》冲表达了通过海洋与世界联结的想法:“只要有一条船,便可以从家门口一直到达美洲大陆,还可以穿过赤道去往澳大利亚,甚至可以绕地球一圈之后又回到家门口。有时候,越是边缘地带,越是有着一种近于魔幻的四通八达。”③从《朱雀》《北鸢》《燕食记》里的南京,再到新作《灵隐》中的香港,葛亮以“外来者"的视角扬长避短地弱化了香港作为“地方”及相关“地景”的意义。对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视野的流动所带来的某种“日常”的情感指涉。其中蕴含的陌生化质地与空间多义性,都在现代文明与传统生存语境之间的博弈中生成了新的言说空间。
青年作家对地方文化的挖掘,表现为深人发掘本土文化,民俗、方言、地域风情等均可作为创作素材。必须指出的是,作家们在对地方文化进行挖掘之余,也完成了从“到世界去"到“在世界中"的内心转变。这一点在多位作家的小说中均有所体现。其中的典型,如徐则臣近三年散见于各大文学刊物上的“域外故事集”系列。在《蒙面》《玛雅人面具》《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边境》等小说中,作家化身为“徐先生"或“徐老师”,或虚或实地讲述着全球游历的故事。在此意义上,青年作家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跨越国族边界的快速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本现实。换言之,“在世界中"正日益成为小说的基本视域。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yzjl2025031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