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旧的木匣子里,装进热忱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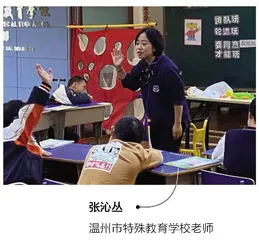
祖孙三代、家族中11人当老师,更特别的是,这家人从事的是特殊教育。时光回溯到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聋哑学校诞生了。老师、学生的世界是无声的,但他们的故事却掷地有声。
2021年,教育部公布100个首批教育世家名单,张沁丛代表整个家族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家族的奋斗被认可,爱的传承被认可”,受到莫大鼓舞的张沁丛继续坚守在岗位上,让更多特殊的孩子能够拥抱寻常的生活。
我有一个木匣子,四四方方,没有精良的做工,甚至还有些破旧。它陪伴爷爷奶奶从少年读书郎到讲台教书匠,又陪伴妈妈度过30余年的教师生涯,而今到了我的手上。
我的爷爷张忠铭,出生于1918年。幼年因发烧失聪,爷爷从此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也说不出内心的话语。少年时,他曾求学于洋人办学的上海福哑学校。临行前,曾祖给了爷爷一个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文具。此后爷爷在福哑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直至抗战爆发才被迫回到温州。
在上海求学期间,爷爷深切体会到“人间至苦,莫若聋哑,五官损其二,毕生毕世,沉沦于痛苦愚昧之域”。爷爷深知聋人学习文化知识后也能为国家所用,回到温州后,他与同窗陈希聪、蔡润祥着手筹办聋校。那时由于战乱,家族衰败,无法满足爷爷创办学校的梦想,于是老前辈们四处奔走,他们的执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十来套课桌椅、一张木床、一个时钟、一个皮球和几根跳绳,组成了早期的聋校。由于几位创始人都是聋哑人,与外界沟通极为不便,我的奶奶黄灿霞便成了学校的校方代表,义务为学校跑部门、筹措经费。
奶奶比爷爷小一岁,我曾问过她,为什么会嫁给失聪的爷爷?奶奶告诉我,撇开“父母之命”,爷爷外表儒雅,脾气温和,会打网球,写得一手古拙厚重的隶书,又有良好的修养,这足以让她忽略爷爷的缺陷。
1946年,学校迎来了第一位学生池曼青和她的妹妹,不久又陆续来了几位学生,上课地点就在陈希聪的家里。于是,浙南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就这么诞生了。爷爷奶奶教学生识字、计算等知识,也教他们做正直的人。1976年,爷爷奶奶退休,但他们也没闲着,带着姑妈去乐清发挥余热,创办聋校,后来学校成了乐清聋校的前身。
1979年,我的妈妈陈湖湖加入了聋校教师的队伍,木匣子里的物件变成了妈妈的小教具。最初,妈妈连手语都不会打,孩子们又无法用耳朵倾听课文。于是她起早贪黑地练习,没多久就能熟练地使用手语了,孩子们的语文课上得越来越有滋味。
妈妈爱她的学生,似乎更胜于爱我。听妈妈的老同事聊起,有一次妈妈挺着个大肚子带学生春游,大家打趣说:“学生们在后面排成队,陈老师在前面把‘鼓’敲。”她会带着理发工具给孩子们理发;天冷了,把家中的被子、棉衣带给有需要的孩子;天热了,给孩子们煮绿豆汤解暑……有一个来自福利院的孩子,逢年过节,妈妈都会带她和我们一起过节。每次妈妈给我买衣服时,都会买一件一样的送给她。现在那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2002年的冬天是个寒冬,它带走了我最尊敬的爷爷。长辈们为了不影响我学习,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噩耗。周末回家,奶奶告诉我,爷爷希望孙辈中至少能有一个孩子延续他的聋教生涯,哥哥姐姐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我成了唯一能够完成他遗愿的孩子。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爷爷的苦心,尽管迫不得已地答应,可心里充满了抗拒。我不要当聋校教师!我想学英语!我想学考古!无奈和挣扎一直折磨着我。但填志愿时,乖巧听话的我还是如爷爷所愿,以超出分数线数10分的成绩报考了南京特教学院,满腹遗憾地成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听障方向的学生。
2008年开学季,我迈进了温州聋校的大门,正式开始了我的特教旅程。我将木匣子放在办公桌上,看着它,我就能想起爷爷的殷切期望。新的我,新的学生,新的班级,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可很快,嘈杂的吵闹声把我拉回现实。这是一群听不见声音又不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只会发出“啊啊啊”的怪叫声,没有健全孩子的生活常识。
那就从零开始吧。我给孩子们制订计划:第一步,认识自己,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座位,能看老师的口型知道老师在点自己的名字就立马站起来;第二步,认识老师,所有老师的照片贴在墙上,见到这个老师就能拿出老师所教科目的书;第三步,认识学校,知道教室、厕所、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第四步,建立课堂常规,比如看到红灯亮了就知道要上课,喝水、上厕所只能在课间进行,老师布置的作业要及时完成,等等。3个月后,孩子们开始有了小学生的样子。偶尔我也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他们还会这么棒吗?
一天早晨,因为交通严重堵塞,我迟到了。当我飞奔到校,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即便含糊不清)让我惊奇万分,孩子们居然井然有序地坐在位置上早读,我的座位上还摆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水。原来临近早自习时,值日班长带着同学们进行早读,孩子们还给我倒了热水,等我回来喝。我站在门口,心中百感交集,这是一群多么好的孩子呀!
转眼间,这批孩子长大成人,有的成了舞蹈演员,有的成了动漫设计师。而我,转岗到了启智部,学生变成了智力存在障碍的孩子。他们的世界是简单的,零食、玩具能解决一切;他们的世界是神秘的,特别是自闭症孩子,当他们暴跳如雷、哭闹不止甚至自残伤人时,我们却难以琢磨到底是为什么。
我曾有个学生叫小灰,这是她妈妈给她起的真名。因为家里的孩子太多,小灰被妈妈送给了姑姑,后来又因智力问题被“退货”。妈妈把她当成了烫手山芋,好不容易熬到上学的年纪,赶紧送进学校。刚进来时,小灰被妈妈托管给一个阿姨。阿姨家有好多孩子,小灰分不到零食、玩具,慢慢养成了偷盗的坏习惯。也许是缘分,让我成了小灰的班主任。我们帮她建立物品归属感,知道“不是我的不能拿,如果我需要可以跟阿姨说”,2个月后她就改正了偷盗的坏习惯。但她的另一个需求——家庭的关爱,我们始终无法满足。妈妈对她心存芥蒂,不愿跟孩子产生牵扯。同为母亲,我相信每位母亲都有内心柔软的地方。于是,我常常把小灰好的一面分享给小灰妈妈,让妈妈真正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一天又一天,小灰妈妈从答应学期中接她回家一次到主动提出一个月接她回家一次,我明白,迎接小灰的是幸福!
现在,木匣子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我知道,我的价值装在木匣子里面——陪着这些孩子学习将来要用到的各种生活技能,让他们顺利地融入社会,自理自信,自食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