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着的诗歌简史
作者: 杨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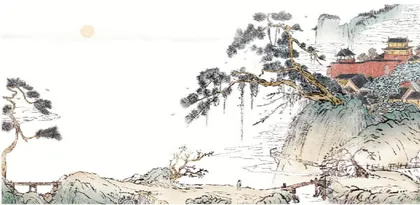
恰如“丁是丁,卯是卯”,文艺图书中,诗选是诗选,诗歌史是诗歌史,两者含混不得。但《宋诗选注》“出格”,在诗选中给读者夹带了“私货”——一部简约的两宋诗歌史。
这部简约的诗歌史就隐含在诗人小传中。我们将诗人小传联读,拈精撮要,就会很直观地看到两宋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书中开篇介绍柳开,说,在提倡学习韩愈、柳宗元方面,“他是王禹偁、欧阳修的先导”。在介绍王禹偁时,说:“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极力要改变这种风气。他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在介绍梅尧臣时,说:“王禹偁没有发生多少作用;西昆体起来了,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辞藻。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在介绍苏舜钦时,说:“他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的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么细密,(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辞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在介绍欧阳修时,说:“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在介绍文同时,说,他的“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质朴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辞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不再一一列举。仅据上引简介,我们就能鲜明感知,两宋诗歌发展的潮流变化,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读者了解了这一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的潮流,就把握了宋代诗歌发展史的主轴,有了巨人的视野和眼光。
把握了主轴,会不会挂一漏万,忽略了枝节?《宋诗选注》对此做了周密的“查漏补缺”工作,基本上做到让优秀的诗人、有影响的诗派、艺术成就较高的诗作雨露均沾。比如,书中在介绍林逋时,说:“那时候(宋初)有一群山林诗人,有的出家做和尚——例如所谓‘九僧’,有的隐居做处士——例如林逋、魏野、曹汝弼等。他们的风格多少相像,都流露出(受)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林逋算得这里面突出的作者,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在浓墨重彩地介绍“入世”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同时,钟锺书先生也不忘给山林隐逸诗派留一席应有之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先生在介绍宋诗诗人时,常常越位,将触角伸到其他朝代。比如,上引内容中,说,王禹偁、苏轼、张耒深受白居易影响,林逋等人受到贾岛、姚合创作的启发,等等。这是一种贴心举动,也是一种高能操作。它有效地拉长了《宋诗选注》所涵盖的文学史长度,使读者对选诗的观照有了更广阔的视角、更宏大的视野。
总结几句。将选诗和诗歌发展史联袂呈现是《宋诗选注》的又一创新之处[另两大创新之处分别是“将注解与文艺批评结合”(见2024年12月刊本栏目),“将学术理性与诗歌温情结合”(见2025年1月刊本栏目)]。这一创新做法有助于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某一诗歌用词斟酌、手法选择、风格形成的“前世今生”,从而能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诗心,明白优秀诗歌何以优秀,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在此诚挚地向读者朋友们建议,读《宋诗选注》,要字字品读,咬文嚼字,我们不仅要读其所选之诗,还要读其所作之注,同时也要读其所附诗人小传。特别要细读、精读常为人所忽视的诗人小传,原因是诗人小传中隐含着两宋诗歌史。而梳理好诗歌发展史,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选诗大有裨益。
思考:
江西诗派是两宋诗歌江湖第一大门派,由于立派时间久,门徒众多,所以其衣钵传承、派系组织等信息比较难把握。《宋诗选注》对江西诗派的发展脉络进行了隐性的梳理。请你重点细读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陈与义等人的简介,概括江西诗派的主要艺术特色,并绘制一幅诗派传承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