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要” 出发,读懂一首诗
作者: 潘瑶箐古典诗歌作为传统文化的最佳载体,被深刻地嵌人每个阶段的语文学习中,正如《古诗词课》里提到的,“读古典诗词,能够更好地建立我们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种血脉关联,理解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人生趣味”。2024年11月,研究了一辈子古诗词的女士去世,引起关于诵读、诗教等议题的诸多讨论,又吸引了一批新读者至古诗词的国度。
相较于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边缘化。对现代诗歌并不敏感的年轻批评者,更在现代诗歌评论这一写作文体前束手无策。其实诗文共通,现代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之一,并非与读者隔阂更深,它只是用了一种特定的语法,等待着有心人的解码。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里说:“你将在作品里看到你亲爱的天然产物、你生活的断片与声音。一件艺术品是好的,只要它是从‘必要'里产生的。"文学之于现实可能是"非必要"的,但在文学世界自身这一维度中,每一个好作品被写出来,都是绝对“必要”的一小说中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并不是为了展现戏剧性效果,散文中的情绪情感是长期积蓄而非矫揉造作,篇幅短小的现代诗更甚一一每一诗行,每一音节,每一语词,甚至每一个“的”,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可或缺一一以上是于写作者而言。作为评论者,发现这些“必要”正是切入一首现代诗的不二法门:这首诗中,哪个要素构成了它的底色?哪种修辞不可被替换?哪一语言现象最能引发“脊椎的战栗"?
相比AI写作的设定感和任务功能,人的写作是必须痛苦,必须快乐,必须悲哀,必须忧愁。这把名为“必要”的密钥可以帮助每一个徘徊在现代诗大门之外的人,打开沉重的大门,登堂人室,进入独属于现代诗歌的秘境。
必要的意象:诗人心魂所系
在一首诗中,意象也许最容易被发现,也最容易被分析,哪怕这种分析趋于浅显。经典诗作中,意象比比皆是一海子《九月》中的马头琴,郑愁予《错误》中的马蹄,张枣《镜中》中的梅花,卞之琳《白螺壳》中的白螺壳。如果把一首现代诗比作一个建筑,这些建筑物虽然风格各异,却有相似的地基。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的第一单元里,整个单元的现代诗同样意象遍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的那把小号,《红烛》中的那根鲜红蜡烛,《峨日朵雪峰之侧》中的渺小蜘蛛,《致云雀》中的云雀,正以各自的方式成为学生记忆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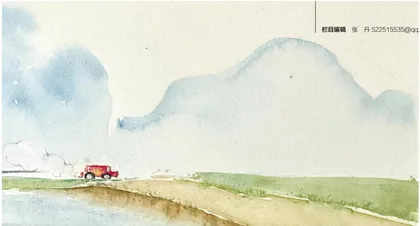
然而正如此前所说,正因显眼,意象分析也容易流于表象,批评者大多得其一便满足了,对它的挖掘不够深人,体察不够细微。面对这些必要的意象,好的评论必须秉承“绝不放过”的原则,将它作为一口井,层层下挖,直通文本深处。
拿着小号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吹号这一仪式有何意义?红烛和李商隐那根蜡烛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它可以作为诗集的序诗?蜘蛛体现了昌耀作为流放者的何种姿态?是抗争还是自度?诗中和云雀同样飞扬、高悬的喻体还有哪些?雪莱如何以多种修辞手法来向音声致意?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明晓为什么它们是诗人的心魂所系。
必要的多义性:读者各自的世界
奚密在《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里提出,现代诗区别于古诗的一大特性就是“模棱两可的歧义性”:对现代诗人来说,杜甫作品中那预设的、在诗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之间、诗和宇宙之间的共续性或同质性早已不存在,现代作品的晦涩更多地来自将外部世界转化为内在景观的内视镜。诗人王敖则更侧重其对读者的作用:“诗的多义性会精确地区分读者,并把他们送回自己的世界。”
对于现代诗歌评论来说,这种多义性是批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正因为读者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认知背景,他们才会在面对同一首诗时产生不同的反应,做出不同的解读。再卓越的批评家的评论也不可能是理解一首诗的唯一正确答案,年长的评论者和年轻的评论者,无论他们是饱经沧桑还是未经世事,在诗的领域,可以各有各的擅长:用自己的人生读诗和用最敏感的头脑、最热烈的情感读诗,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
综观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下册的两首现代诗《大堰河一我的保姆》《再别康桥》,其中大堰河的形象并不是固定的、单向度的,而是流动的、多层次的,康桥的意义也丰富复杂。而且,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评论的权利建立在读者和作品的亲密关系上,就算艾青和徐志摩说是误读,也作不得数一一在批评的范畴内,作者和读者拥有友人般的平等地位。
学生作品
蟋蟀:时间的使者
文/宁波效实中学 班马拜仁
在诗歌中,时间往往以一种不显眼的方式存在,和其他抽象的概念一同栖居在意象上,并时刻影响着诗句的意义。在李瑛的《蟋蟀》里,蟋蟀这个意象可以被多重解读,其中一种便是时间使者。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使者究竟拥有哪些特点,它又怎样赋予诗歌独特的文学价值。
在诗歌的中间部分,蟋蟀秋夜的鸣叫勾起了诗人对过去的回忆,而回忆中刚好存在另一只蟋蟀。蟋蟀既见证了诗人60年的变化,又引起了他对往昔的感叹。但不像历经60年沧桑依然不会变动的无机物,蟋蟀和“我”一样都是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生命体。因此,一只蟋蟀乃至所有蟋蟀很难代表时间,因为蟋蟀没有永恒性,只能是其片段的载体。这种特性在诗中呈现为“秋的深处,夜的深处,梦的深处”。这个并列句包含了一个递进关系,从自然的长久到自然的瞬间到个人的瞬间,蟋蟀正是作为这种节点式的标志唤醒了诗人,使他置身于孩童时期的情境中,置身于秋夜的梦与回忆中,同时将“梦的深处”从“养在陶罐用花茎拨动它的长须"变成追忆“我的童年早已枯萎”。用具有短暂性的事物片段来代表时间,就如同用历史中的人来描述另一个人,是文学中一种富有深意的措辞,毕竟“组成我们的是时间,是短暂性"(博尔赫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回忆的向来不是时间,而是无法重返的感受与经历。
“而今,我孤凄的叫声”一句发挥了语言的多义性,可以理解为"我发出的孤凄的叫声”,并构成“我”与蟋蟀的同感,但是理解为“我的蟋蟀的孤凄的叫声”可能更合适。首先,后两句采用了相同的意思“属于我的”,保持前一句用词意义,可以构成朗读时的音乐美。其次,纵观全诗,找出用来形容蟋蟀的词:瘦,轻轻的,胆怯的,没有家,没有寒衣的,挣扎,颤抖,凄清、纤细的鸣叫,等等,它们统一塑造了一个悲戚、垂死、徒劳的形象,而只有这样的鸣叫被“我"听到,敲打在门上,震撼着“我”,被怜爱地称为“我的叫声”,才能把“我”带回旧日。诗歌注重的是人们与时间的交互,而不是进人现在的时间。如此,蟋蟀成为文本中的时间,给时间增添了一层悲伤、脆弱的特性,蟋蟀本身则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些都是诗歌陌生化的概念。
《蟋蟀》里存在着片段的、遥相呼应的时间,易碎的、在秋夜濒死的时间,这些时间都在蟋蟀的身影和鸣叫之中。
指导老师点评
在面对《蟋蟀》这首现代诗时,作者首先抓住了蟋蟀这一意象最触动他的一种意义——时间使者。它既代表了四季轮转中的秋,又代表了昼夜更替中的夜,更由“是我童年从豆秧下捉到的那一只吗”一句,代表了不堪回顾的童年,代表了诗人60年的人生跨度。在这之后,作者又探讨了“我孤凄的叫声”的多种可能性,既确认了差异的可能,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精准且独特的解读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篇评论的语言同样具有诗的光辉。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zxtb20250414.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