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的百花齐放
作者: 贺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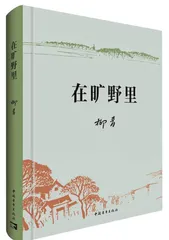
2024年,文学界出版了不少好书,有的是长在旷野里的,有的是在花园里专门培植的;有的充满野性,有的携带着特定的基因。无论哪一种,都属于“百花齐放”中所不可或缺的。
小说里的新元素
《人民文学》2024年第一期推出了著名作家柳青的一部佚作《在旷野里》,随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将其印成书籍在全国发行。这部写于70多年前的小说今天读来仍觉新鲜,柳青塑造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他以亲身实践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处理现实中的新事物。小说显示出柳青敏锐的思想,他自觉地将战争思维转向建设思维,让自己的写作追随时代的新变。《在旷野里》这个标题起得好,旷野的自然生态最真实地呈现在当代文学之中。
格非的《登春台》写北京春台路上四个人的命运流转,叙述绵实,情感幽微,显示出作者的笔力之老辣。张楚的《云落》是一部中国县城的发展史和心灵史,县城就像是解开中国现实万象的密钥,它牢牢掌握在张楚掌心,以此洞察人心和世事。张炜的《去老万玉家》以一次步步惊心的传奇之旅,完成了一个男人迟到的成人礼。麦家的《人间信》继续关注人物的命运挣扎和自我救赎,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首凄美的诗章。鬼子的《买话》以一个凤凰男的返乡,抒发了现代人的孤独感。李修文的《猛虎下山》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上演了一场寓意深邃的人虎博弈。杨志军的《大象》是一部叙述密度超强的小说,这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难度,但作者将他的生态观从西北荒原平移到西南热带雨林,赋予生态叙述更旺盛的生命活力。杨少衡的《深蓝》是一个将官场叙事、历史叙事和国家叙事交织在一起的精彩故事。提到以上这些小说,是因为我在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发现一些新的元素,这种新,是针对创作现状中的同质化而言的,或是针对作家本人的创作风格而言的,都很可贵。
老藤《草木志》的新视角
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新在观察世界的角度。这是一部写乡村振兴的小说,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很容易陷入模式化的窠臼之中,老藤所讲述的故事与众多这类小说大致相同,但老藤很聪明地在视角上做文章,他开辟了一个观察乡村的全新角度,这就是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入手去观察世界。小说中的驻村书记爱好植物,当他来到乡村,仿佛来到了一个植物王国。在他了解和学习植物知识的过程中,发现乡村里的村民仿佛与植物有着息息相通之处,他觉得在乡村熟悉了植物,也就熟悉了人。老藤便以植物来结构小说,每一章都是以一种植物来命名,既要描写这种植物的种种特性,也以这种植物指代村里的某一个人,这是老藤找到的一种认识乡村世界的方式。
我们认识乡村世界,会强调人与土地的关系,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去认识乡村历史和乡村人物命运。老藤则要说,我们还可以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去认识乡村世界。在乡村,看到一个地方各种植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就知道这里生态良好,一个村有良好的社会生态,人际关系就好,矛盾就容易化解。驻村书记来到墟里村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工作,其实也是在帮助墟里村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
刘醒龙《听漏》的“青铜”风格
《听漏》之新主要是针对作者刘醒龙本人的写作风格而言,这是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长篇的第二部,刘醒龙在这个系列里有了一些变化,既承继着自己过去的优势,又开启了一种新的风格——“青铜”风格。青铜厚重、庄严,细看青铜器上的图饰和花纹,又那么精致、细密,有一种飘逸感,细读刘醒龙这两部小说,你会读出飘逸感,这就是他的新风格。这种飘逸感首先来自刘醒龙的写作心态,他把小说当成了志趣的事情来做,心态特别的放松。表现在小说里,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叙述结构,故事的展开也充分通过悬念来推动,但无论是侦探小说叙述还是悬念的设置,在这里都不是纯粹技术行为,而是包含着他对考古和文物的认知。出土文物携带着历史的文化密码,考古则是要破解这些文化密码的。刘醒龙将自己化身为一位考古队员,把小说当成一次考古来做,因此小说中会有那么多的悬念。他同时还将小说的审美性维系在志趣上,仿佛是在自得其乐地玩着智力的游戏。比如,他写到马跃之问曾听长,谁是听漏工的祖师爷,马跃之自己来解答,他则旁征博引,证明了苏东坡就是听漏工的祖师爷,你读了马跃之这一段口若莲花的论述,会获得一种智趣的享受。说到底,飘逸感传递出了一种在文学观上的变化。但小说不只有飘逸,飘逸就会轻飘了,这不符合刘醒龙的性格。小说厚重的一面首先体现在作者有一个宏大的构想,他要充分展示青铜重器的历史内涵和精神风采。厚重还表现在他没有沉陷在历史的深渊里。刘醒龙有强烈的现实感,他借小说中的人物说: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刘醒龙要对今天的现实问题作出解答。刘醒龙一贯坚持的批判精神,当然,小说的批判性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锋芒毕露会伤了小说飘逸的风格,他的批判好像是飘逸之中捎带的,但这种捎带同样很有力量。《听漏》重点写的是马跃之的有情有义,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坚守理想操守上的光彩。
《亲爱的人们》:将风格发挥到极致
马金莲在这部小说里将作者的风格和特点发挥到了极致。马金莲的风格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审美化和伦理亲情的仪式化。这样的风格更适合写中短篇小说,但她却以这种风格写下七八十万字的《亲爱的人们》,读来却没有疲倦感,这在于马金莲是扣着日常生活缓慢变化中的“新”来写的,写新事物、新现象如何跋涉千里,进入羊圈门村这个西北偏僻的乡村,又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肌理。她以羊圈门村的方言为例,细数这几十年来增添进来多少新鲜的词,她感叹道:“方言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口袋,在不断地吐故、纳新、装进、倒出;也是一口恒温熔炉,能把装进来的捂热,熔炼,交汇,融和。正是这样开放式的吐纳,让村庄经历了几辈人的更迭,方言还完好地保持并赓续着。”
马金莲写羊圈门村方言的变化,写日常生活习俗的变化、情感的变化,以及眼界的变化。她以细密的日常生活细节丰满了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演变,她以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有生活血肉的文字,真实表现了西北最贫困地区之一西海固是如何逐步摆脱贫困、追赶着新时代步伐的艰辛历史。小说采取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作者毫无距离感地在他所叙述的人物中间,体贴他们,心疼他们,善良地为他们开脱,热切地期待他们幸福,这是马金莲的写作姿态,因为这种姿态,使她客观的叙述具有了一种强大的感人力量。小说不是刻意地要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了乡村振兴主题作品中极有说服力的文学文本。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