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视野里有“独立之精神”的人
作者: 张志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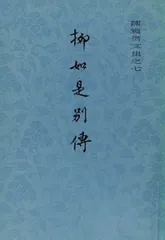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晚年倾其余生十年之力,以口授的方式完成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是既令人望而却步,又令人豁然开朗的一部书。
陈寅恪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更让我对他的作品充满期待。
《柳如是别传》有一个重要的副题,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当时看了这句话多少有些不解,为什么写“柳如是”这样一个传奇女子,要给予她如此高的定位。
《柳如是别传》为何令人“望而却步”
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据说有关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心境和《柳如是别传》史学创获的论述颇多,也引发一些人对陈寅恪感兴趣。《柳如是别传》名声之大,可以和陈寅恪“同日而语”。几乎所有人,在兴致勃勃地捧起《柳如是别传》之后,没读完三页,就已兴趣全失,越读越是一头雾水,望而却步。
打开《柳如是别传》,卷前的“出版说明”特别指出:“根据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引文中凡为阅读之便而辅入被略去的内容时,辅入文字加【 】,凡属作者说明性文字则加( ),原稿不易辨识的文字以□示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对繁体字尚能正常阅读,但对广大读者来说,实在是困难。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最难读的书。其实如能搞清一些基本问题,也没那么难。全书82万字,共分五章,前三章是全书的上卷,第四章是中卷,第五章是下卷。上卷:第一章,缘起;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推测及其附带问题;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附,河东君嘉定之游。
上卷出现上百人的名字,与河东君有关系或常往来的有十几人,同一个人物在书中出现,一会儿是他的名字,一会儿又是他的号,或雅称,或别名,或尊称,等等,随意转换,这使得在阅读时容易混乱,一定要把书中出现的与河东君有关联的人物关系搞清楚,知道这些人的字和号。同时,上卷有诗词歌赋几百首,一会儿是卧子,一会儿是河东君,一会儿又是牧斋、陈子龙、柳如是,要不断地去考证诗的先后顺序和相隔时间,在这种考证中不厌其烦地去解读。
在书中,陈寅恪想到谁说谁,不仅是对所涉及到的人信马由缰,而且对涉及地点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一会儿杭州,一会儿金陵,一会儿扬州,一会儿苏州,让读者很快就迷茫了。
显然,陈寅恪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本就没考虑迎合谁,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你是否能看懂,而是要把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全盘留给后人,不留任何遗憾。
这就是陈寅恪给读者展现的《柳如是别传》,这样不嫌絮叨,不嫌啰嗦的文字,没有点耐心是无法阅读的。该著作的原名《钱柳因缘诗释征稿》,如用原书名,可能会阻挡更多的人捧起此书。
为何要为柳如是立传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其说是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的评价,不如说是陈寅恪先生寄托自己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向往。
《柳如是别传》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种全新诠释。陈寅恪以明清转换的历史事实为轴心,在历史大转型、大转换中,通过柳如是的奇特经历,展开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可以从中看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严酷的命运面前选择自己的归宿的。
柳如是本是一个弱女子,完全可以“同流合污”,可以顺应时代的转换,以求得一偶之下的“卿卿我我”,或琴棋书画的个人生活,但她非不,这实在令人不解。
陈寅恪对绘就的这幅历史画卷中的核心人物柳如是,反复强调她的自由精神,侠气、才气和骨气,三者合一。
从柳如是身上,我理解了当年为什么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放在眼前的白面。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气,自古就有之,而来自柳如是这样一个娇小的弱女子的内心世界,是常人不解的。她在个人感情上没能做到始终如一,在政治上却真正从一而终,矢志不移。
在陈寅恪内心里,王国维和柳如是是同一类人,所以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既写给了王国维,也送给了柳如是。王国维在《人间画词》中将人生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唯有那些坚定信念,坚持真我,将自己化作一束光的人,才能领悟这人生的三个境界,我想,陈寅恪正是因为读懂了王国维和柳如是,才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此书为何又令人“豁然开朗”
如仅从柳如是个人来看,《柳如是别传》所要说的故事并不复杂。柳如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妓,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浙江嘉兴人,幼年被卖给官宦人家,后沦落青楼。与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同称“秦淮八艳”。先努力要给陈子龙做妾,后嫁给钱谦益。
柳如是是著名歌妓才女,个性坚强、正直聪慧,人虽娇小,却魄力奇伟。她不仅貌美,还善诗词会曲,能书擅画,敢追求个人幸福,又明于民族大义,她与当时多位名士往来,常常与他们纵论天下兴亡,抒发独有的政治主张。其书法深得后人赞赏,被称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陈子龙是明朝崇祯十年进士、文学家和诗人,有“明代第一词人”之称。陈子龙与柳如是曾有短暂的同居,两人相爱,有大量诗为证,但两人却没能走到一起,这主要是因为陈子龙有家室,其妻张氏曾带人羞辱柳如是,导致柳如是内心抗争,不甘受辱,离开了陈子龙。
钱谦益,号牧斋,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明万历三十八年探花,也就是一甲三名进士,后卫东林党的领袖之一。59岁时,钱谦益迎娶比自己小36岁,风情正好、年芳23岁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为钱牧斋生有一女。
关于官员士大夫娶妓为妻一事,在唐代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纳妓为妾还是比较常见的。到了宋代,相关的法律大体上继承了唐代。虽然也有一些禁令,但从大量宋词中仍然可以窥见当时士妓之间的频繁交往。到了元代,法律中明确出现了禁止卖良为娼和娶乐人为妻妾的规定。在明初,上述这些禁令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刑典《大明律》之中。从整体上来说,从唐以来,士妓婚恋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是受到阻隔的。应该说,这也是陈子龙没有娶柳如是的关键所在。钱牧斋也面对同样的伦理文化背景,但他最大的不同是无视了这些礼法。应该说,钱谦益所处的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大转变时期,社会变化受资本主义萌芽或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不循常规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妓女与官员士大夫的婚恋交往也得以公开和活跃。钱牧斋和柳如是都是那个时代的“叛逆之徒”,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要公开迎娶。从当时的礼法制度和观念来看,两人所做的一切真可谓惊世骇俗。两人婚后,钱牧斋对河东君极其信任和包容。
在我看来,想读《柳如是别传》还真得做好读不下去的准备,这真是一套难读的书。但我始终认为,难读的书,不见得没人读;好读的书,也不见得很多人看。读书无用,但读无用书,才是乐趣,没有任何功利之心。陈寅恪写的《柳如是别传》就是一本无用之书,是一部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传的书。
作者系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