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地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经验探索、现实挑战与实践策略
作者: 张惠强 周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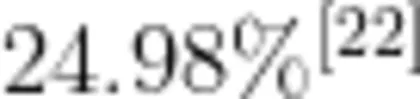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根基。
本期继续聚焦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精神,开设“农业强国”专题,邀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团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蔡海龙教授团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何兰萍教授团队,分别就“中国优势地区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经验探索、现实挑战与实践策略”“嵌入国家现代化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工代赈40年:演进历程、政策逻辑与展望”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策划:杨果 易晓艳)
关键词: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土地管理制度;市场化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25)004-0037-014
[DOI编码]10.19631/j.cnki.css.2025.004.003
2024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的意见》。会议明确要求,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在我国的政策话语体系中,所谓“优势地区"并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统一的界定标准。本研究对此采取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即经济规模较大、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资源要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以及武汉、西安、长沙、郑州等中心城市。当前,人口和经济加速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聚,土地资源约束日趋紧张,亟须识别土地要素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探索和改进土地管理制度和利用方式,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
作者简介:张惠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城乡区域发展和体制改革;周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城镇化。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在大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优势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土地管理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优势地区要素集聚、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起着关键作用。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如何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赋能优势地区发展,成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早期关于土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古典经济学派如亚当·斯密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认为合理配置土地能促进经济增长[1。以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为例,从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因素探讨工业布局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为优势地区产业集聚下的土地利用研究提供思路[2]。当前围绕土地制度展开的研究论述主要是从体制改革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个主线展开,包括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供给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
(一)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产权制度改革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制约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障碍。在现行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需经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后方可人市交易,导致农村土地价值难以显化,建设用地供需失衡[3]。彭森指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需重点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集体经营性土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并通过完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解决利益冲突[4]。程雪阳、彭鯙进一步提出,土地发展权的归属与收益分配需通过法律明确,防止政府垄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5-6]。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离不开土地所有制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地所有制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主张土地国有化,认为国有化可以强化国家调控能力,遏制土地兼并,但同时也面临路径选择和运行成本高的争议[7]。二是主张土地私有化,认为私有化能激发农民长期投资意愿,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但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8]。三是完善集体所有制,通过确权赋能,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推动“三权分置"改革,增强农民财产性收人[9]。
某种程度上讲,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体两面的,只有清晰界定并有力推进土地产权,才能促使其迈向市场流转,而市场化配置,可加速实现土地产权的价值。
(二)土地供给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
合理的土地供给机制可以引导产业和人口在不同区域合理布局。例如,通过对特定产业用地的精准供给,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在东部沿海地区,政府通过优惠的土地政策,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大量土地,吸引相关企业集聚,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协作[10]。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求,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应减少了一般性制造业和批发市场等用地供给,增加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产业用地以及公共服务用地;河北则根据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增加了产业园区用地供给,优化土地供给结构。
我国对经济发展用地实行严格的指标管控,行政层级越高,获得指标的数量和自由度越大[1]。董祚继指出,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区域,土地需求旺盛,但土地供给受到指标、规划等限制,导致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如在一线城市,由于人口持续流人,住房和产业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但土地资源有限,土地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推高了房价和地价,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12]。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建立“增存挂钩"机制,向优势地区倾斜用地指标,优先保障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存量土地[13]。例如,成都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规划先行,显化农村建设用地价值,促进城乡协调发展[14]。张惠强的研究指出,以成都为代表的一些地区探索了集体建设用地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要推广相关的经验,化解保护与发展间的矛盾[15]。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cqsk20250403.pd原版全文
(三)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刘守英等认为,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如灵活的土地用途管制和弹性的土地供应计划,能够为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企业等提供充足且合适的发展空间,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成长[16]。周其仁认为,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释放农村土地资源,能为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如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提供空间基础[17]。李昕等认为,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如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土地优惠政策、设立科技园区的土地专项保障等,能够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形成创新生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18]。
孙久文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土地的空间布局、功能配套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土地管理制度在规划、审批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其发展[19]。董祚继指出,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提供优质的土地资源和配套设施,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企业,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龙瀛等在关于智慧城市与土地利用的研究中指出,未来应加强数字化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土地资源的精准监测、智能规划和高效配置,以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20]。
(四)当前研究的不足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更多聚焦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某一具体方面(如土地流转、产权制度等),缺乏从整体上对适应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二是多数研究基于静态产权分析,缺乏对交易成本动态影响的深人探讨。部分实证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区域有限,不能充分反映不同类型优势地区的土地管理实际情况和需求,导致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可靠性受限。同时,对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政策实施效果的长期跟踪和评估研究不足,难以准确把握改革的长期影响和动态变化。三是与国家宏观政策衔接研究不足,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如何与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宏观政策更好地衔接和协同推进,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难以形成政策合力以促进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过程中,但研究往往对政策的动态变化适应性不足,不能及时根据新政策、新要求进行研究内容和方向的调整,导致研究成果与实际政策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鉴于此,本研究从当前土地要素配置出现的三大结构性失衡现象入手,分析导致这些失衡的原因和机制。客观上存在的失衡,需要从地方破解问题的解法入手,向实践找办法。因此,本研究梳理了优势地区破除土地要素约束的创新性探索与成效。在此基础上,分析土地利用方式创新仍面临若干障碍,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土地要素配置出现三大结构性失衡
近年来,人口和经济向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聚态势日益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 3 7 . 7 8 % 上升到2020年的 3 9 . 9 3 %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量占到人口总量的 4 0 % 以上[21],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区域。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和经济集中度加速提升,深圳从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常住人口增加了713.65万人,GDP占广东全省比重从 2 1 . 9 2 % 提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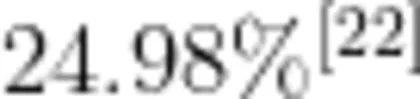 。然而,我国的土地指标以行政计划性分配为主,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实际需求不完全匹配,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价值的挖潜存在制约,土地要素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总的来看,土地要素配置与区域发展之间呈现三大结构性失衡。
。然而,我国的土地指标以行政计划性分配为主,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实际需求不完全匹配,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价值的挖潜存在制约,土地要素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总的来看,土地要素配置与区域发展之间呈现三大结构性失衡。
(一)空间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建设用地指标的供应存在区域空间错配。从建设用地与人口流动的关联视角来看,存在着建设用地增量与人口流向背离的情况。在2003年至2012年的时间区间内,中西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出区域,其建设用地供应在全国总量的占比显著上升;反观东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当年新增建设用地供给在全国的占比却从 6 9 . 1 6 % 滑落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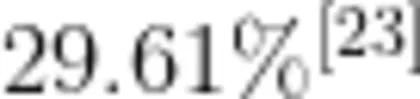 。2022 年江苏的城区人口增加了45万人,但建设用地面积反而减少了981平方公里;而四川的城区人口减少了145万人,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17平方公里[24]。从各省份城区人均拥有建设用地面积和工业增加值的比较来看,存在着建设用地分布与工业发展不完全匹配的情况,2022 年,在人均建设用地资源方面,甘肃城区人均占有的建设用地量是广东城区的1.7倍;但在工业经济产出方面,甘肃工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的 7 % 。有的城市不断吸引人口流入,但建设用地面积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增加,导致人均占地面积不断下降。此外,各地土地利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兴业研究的数据,目前存量工业用地面积前30名城市的低效用地总和约为1 240.78平方公里,相当于这些城市 2022—2024年工业用地年均供应量的5.21倍,盘活潜力较大。其中,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东莞、重庆、武汉、天津、青岛、苏州、成都等城市的待盘活规模位于前列[25]。
。2022 年江苏的城区人口增加了45万人,但建设用地面积反而减少了981平方公里;而四川的城区人口减少了145万人,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17平方公里[24]。从各省份城区人均拥有建设用地面积和工业增加值的比较来看,存在着建设用地分布与工业发展不完全匹配的情况,2022 年,在人均建设用地资源方面,甘肃城区人均占有的建设用地量是广东城区的1.7倍;但在工业经济产出方面,甘肃工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的 7 % 。有的城市不断吸引人口流入,但建设用地面积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增加,导致人均占地面积不断下降。此外,各地土地利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兴业研究的数据,目前存量工业用地面积前30名城市的低效用地总和约为1 240.78平方公里,相当于这些城市 2022—2024年工业用地年均供应量的5.21倍,盘活潜力较大。其中,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东莞、重庆、武汉、天津、青岛、苏州、成都等城市的待盘活规模位于前列[25]。
(二)城乡失衡
优势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存量较大。据测算,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有4200多万亩[26],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势地区。根据广东“三旧改造"试点调查数据,全省共有416 万亩建设用地进入试点入库,其中集体建设用地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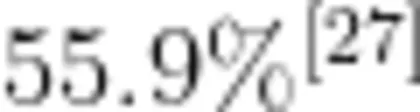 ,珠三角区域市、县集体建设用地占比更大,但再开发利用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虽然历经多次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了合法依据①,但在法律条文与政策文件向地方实践转化的过程中,缺乏具体操作细则,难以搭建起三者之间有效的制度衔接桥梁。经过多年发展,国有土地在出让、开发、建设以及交易等方面,已形成了日益完备的制度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领域存在较大制度空白,诸如用地手续的完善流程、产权登记的具体办法、相关规划的调整方式、交易规则的制定原则、片区综合整治的实施策略、税费征收的标准设定、收益分配的合理方案以及项目监管的有效手段等方面均缺乏明确规定,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相关工作时举步维艰,社会资本也因无章可循而难以开展具体操作[27]。
,珠三角区域市、县集体建设用地占比更大,但再开发利用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虽然历经多次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了合法依据①,但在法律条文与政策文件向地方实践转化的过程中,缺乏具体操作细则,难以搭建起三者之间有效的制度衔接桥梁。经过多年发展,国有土地在出让、开发、建设以及交易等方面,已形成了日益完备的制度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人市领域存在较大制度空白,诸如用地手续的完善流程、产权登记的具体办法、相关规划的调整方式、交易规则的制定原则、片区综合整治的实施策略、税费征收的标准设定、收益分配的合理方案以及项目监管的有效手段等方面均缺乏明确规定,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相关工作时举步维艰,社会资本也因无章可循而难以开展具体操作[27]。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cqsk20250403.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