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流动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
作者: 郭未 王若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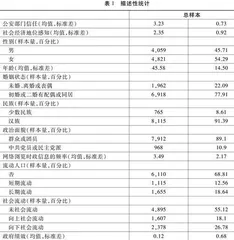
摘要:公众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的提升在提高公安部门的执法效能及促进城市社会治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21年数据,使用OLS模型挖掘流动视野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其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Bootstrap中介分析探究网络浏览时政信息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正向作用于对公安部门的信任。这一关系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中具有异质性,在进行长期人口流动的群体中最强,非流动人口中次之;在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更强,未经历社会流动的人口中次之。网络浏览时政信息的频率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起负向中介作用,这一作用在非流动人口和未经历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显著。研究发现为公安部门如何更为有效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证据为本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流动;信任;社会经济地位;工具变量;人口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4)06-0072-016
一、引言
公共安全服务是政府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在日常生活中以居民报警服务为主要表现形式,薛克勋:《公共安全服务中的政府响应机制研究——对某沿海城市一般紧急事件报警情况的调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并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相应事务。翟军亮、吴春梅:《论公共安全合作能力建设:缘起、结构和路径》,《行政论坛》,2016年第1期。公安机关承担着打击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以及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陈晓莹:《风险社会视角下深度伪造型网络犯罪及其治理研究》,《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4年第8期。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公安机关共计受理治安案件864.88万件,成功查处782.89万件,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数量高达442.33万件。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2022年),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访问日期:2024年8月5日。公安机关在高效处理众多案件方面,其成效既植根于部门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也与公众对其高度信任息息相关。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程度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较高的政府信任是巩固执政合法性及优化政府行政效能的核心要素,也是政府稳固其执政基石的关键表征。马子博、王立志、张成福:《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相应地,公众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的提升,也能够提高公安部门的执法效能与助力夯实其执法成果。因此,深入探究公众对公安部门信任度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并在流动中国的实然情景下细致剖析流动人口在此影响中的异质性,对于理解并提升公众对公安部门的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蕴涵。
那么,何种因素在影响个体对于公安部门信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论认为,个体占有资源与其信任水平具有正向关联,田北海、王连生、王彩云:《资源占有与资源分配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影响的比较研究——对“资源因素论”视角的一个拓展性解释》,《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既往研究也验证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对政府信任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郑建君、马璇、刘丝嘉:《公共服务参与会增加个体的获得感吗?——基于政府透明度与信任的调节作用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2期。社会经济地位涵盖了收入与财富分布、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层级等客观社会资源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参与塑造了社会成员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相对位置的感知,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et al.,“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9, no.3 (July 2012), pp.546-572.因而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是影响其公安部门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就流动视野下的人口流动维度而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但相关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服务与管理机制尚待完善,导致流动人口在多个领域面临着较当地户籍人口而言的制度性差异与不平等。郭未、于瑶:《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小镇青年人力资本、社会阶层的代际与空间流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在制度差异的背景下,若既有的社会架构与制度安排未能有效提供民意畅通与情感宣泄的渠道,就极易导致城市场域的人们对于政府信任水平的降低;而鉴于流动人口的高度集中性与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其在对政府相关部门信任感下降的情况下就可能形成抗争性政治行为的群体性风险,最终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陈颀、吴毅:《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社会》,2014年第1期。 就流动视野下的社会流动维度而言,关于社会流动对包括公安部门信任在内的政治信任产生的影响,学界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向上社会流动与较高的信任水平呈现正相关,向下流动则与较低的信任水平紧密相关。
鉴于此,深入探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其对公安部门的信任水平、解析其作用机制,并探究这一关系在人口流动与社会流动性中的异质性,对于优化社会治理策略、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信任构建的复杂过程,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以针对性地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促进社会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
作为政府信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公安部门的信任在既有的文献中大多被视为评估公众对政府整体信任度的某一考察维度,向颖、卫松:《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社会分层与利益表达》,《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其来源与更广泛的政府信任有着相似的机制与基础。已有文献对于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的定义尚未统一,比如,有学者将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视为一致的概念;高学德、王镇江:《危机沟通策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3期;谢文俊:《政府治理绩效如何影响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和传统政治观念的调节作用》,《统计与管理》,2024年第3期。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政府信任与对公职人员的信任;陈思艺:《政府工作透明度对公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探究——基于CSS2017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张要要:《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5期。Norris则将政治信任划分为民主制度的信任和机构运作的信任,公安部门信任属于后者。参见Norris P.,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本文将其视为内涵一致的概念。已有文献从宏观角度对政府信任的来源进行了解释,认为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较为简化的机制,对其的理解可以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入手。制度主义从政府绩效的角度解释信任来源,认为政府绩效决定了其被信任程度。Citrin J.,“Comment: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no.3 (September 1974), pp.973-988;韩华为、陈彬莉:《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政治社会效应——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4期。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公众对公安部门的信任源于对其保护和服务能力的评估以及能够正确和合理使用权力。苏娜:《警察信任及影响因素:国外研究与学术反思》,《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与探究,信任则被认为是生命早期习得的基本性格决定的,Putnam Robert D.,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28, no.4 (September 1995), pp.664-683.但人际信任具有溢出效应,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对于人的信任逐步拓展,通过与政府人员或政府相关机构的成功合作被投射到政府。Mishler W. and Rose R.,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no.1 (February 2001), pp.30-62.此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及秉持各异价值观念的个体,对于公安部门的职能定位、作用效果可能持有不同的期望与评价,在评判其绩效时展现出差异化的视角与评价标准,游宇、王正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间接作用于公安部门信任。因而,文化主义主张公民与政府安全部门之间的互动经历是其构建安全部门信任的关键因素。刘颜俊、周礼为、王超晨:《竞逐安全:后冲突社会安全供给与公众信任》,《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
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主要从宏观层面剖析信任构建的根基,也有学者从微观视角探索信任生成的多元维度。鉴于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背景、政治和经济经验或个体感知和评价的不同,个体间的信任水平也会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发现,收入、学历、公平感以及政治参与等微观层面的因素都会对个体层面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郑建君、孙瑞佳、马瑾霏:《个体公平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基于政治信任的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曹柠梦、孙炳海、任梓荣等:《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应用心理学》,2022年第1期。个体的社会安全感也会促进公安与公众的信任。蔡培鹏:《政府质量如何影响民众对警察的信任:社会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微观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细化了对信任来源的理解。其中,资源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主张信任水平取决于个体占有资源的数量,随着个体占有资源的增多,其信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14-220.并从三条路径解释了个体资源影响信任水平的机制。一是资源充裕的个体更倾向于预期自身能够赢得他人信任,这种预期会作为一种驱动力,促使他们主动向外界释放信任信号;二是资源起到缓冲的作用,降低了信任关系破裂时可能遭受的相对损害,从而提升了个体的信任阈值;三是资源丰富的个体更能有效利用社会中存在的责任性机构抵御信任风险,维护信任关系。因此,资源优势的累积促进了信任关系的形成与稳固。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0-171页。此外,在制度机制的挤压作用下,可能利益分配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个体中具有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公安的执法效率。李峰:《户籍、同期群及其对警察信任度的影响:基于上海数据的分析》,《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6期。作为衡量个体资源拥有量的关键指标,收入、教育水平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均作用于信任程度。拥有较高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个体往往对政府机构持有更为正面的评价,倾向于表现更高的信任水平。张文宏、马丹:《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Knack S. and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2,no.4 (November 1997), pp.1251-1288.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弱势群体通常具有更低的信任程度,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可能由于对政府期待更高,进而具有更低的公安信任。胡荣:《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影响其公安部门信任程度。
假设1a: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越高,其对公安部门信任程度越高。
假设1b: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越高,其对公安部门信任程度越低。
(二)网络浏览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中的作用[HTSS]
当下人类正迈入以“数字”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其深刻型塑了人们获取信息与进行交流所依附的网络。知识沟理论认为,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能够更为迅速和轻易地获取、处理并解析通过大众传媒渠道传播的信息,加剧了两者间本就存在的知识鸿沟。王延广、姜艳凤、胡大敏:《基于数字鸿沟与教育鸿沟的高校馆读者信息素质塑造冷思考》,《现代情报》,2010年第1期。这一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可被视为信息技术掌握程度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正相关性,已被许多文献佐证。一项聚焦于汶川地震信息传播的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媒介渠道多样性,能更早获悉地震相关信息,并展现出对相关知识更为深入的掌握。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在传播生态中处于多重劣势地位,包括媒介资源利用的有限性、接收工具持有量的不足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的相对薄弱。王正祥:《社会经济地位与汶川地震消息的扩散——来自安徽淮北的调查结果》,《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但也有学者对知识沟形成机制的研究仅从个体层面探讨其成因,指出其存在局限性,并补充传播方式的社会化程度以及知识折旧的速率同样是构成知识沟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易龙、奚奇:《知识资源视角下“知沟”演化机制研究——基于糖域模型仿真的方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社会经济地位对网络使用的影响深远且复杂,它不仅决定了个体获取信息的速度与广度,还深刻影响了其处理信息、利用信息乃至创新知识的能力。通过影响公众网络政治信息的接触频率、理解深度及参与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还间接作用于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政治社会化过程本质上是个体不断吸纳政治信息,进而形成对政治领域稳定认知与态度的动态建构过程。Easton D. and Hess R. D., “The Child's Political World”,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no.3 (August 1962), pp.229-246.
在数字社会的宏观框架下,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成为现代公众获取政治信息、形成政治认知的重要来源。公众对政治现实的认知深受媒体对政治事件报道的影响,媒体成为推动政治社会化重要的力量。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程中,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媒体接触对个体政治态度的影响展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目前学者大多支持良性循环论关于媒体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结论,该理论强调媒体在维护公众对政治制度和价值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媒体以正面视角呈现政治现实时,公众的媒体接触将正向促进政治信任。Norris P., A Virtuous Circl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In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Ideas, Involvement and Institutions (ed.),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1, pp.100-117. 媒体抑郁论作为另一重要视角,主张媒体中的负面政治内容可能诱发公众的政治疏离感,进而削弱其政治信任。Norris P.,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52-555.第三种理论视角秉持媒体中立性观点,认为媒体是政治资讯传递的纯粹媒体,而非价值判断的载体。该视角主张,当新闻内容对政治人物呈现批判性时,此非源于媒体本身的负面性,而是源于其报道对象,即负面政治事件的客观存在。在此过程中,媒体更多地扮演着镜像角色,映射而非塑造公众情绪的波动与态度的变迁。胡荣、庄思薇:《媒介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