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安亭情系党的教育事业
作者: 夏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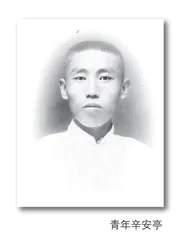
辛安亭,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或许不多,然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读过他编写的教材的人却是数以亿计,影响了几代人。
从偏僻山村走进北大红楼
辛安亭(1904—1988),字适然,出生于山西离石县沙会则村。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哥哥,耕种几亩薄田,年景好时勉强可以糊口,遇到大旱之年就连吃饭都成问题。
辛安亭自幼瘦弱,9岁进入村冬学堂读书,勤奋好学的他只用3个月就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和上百首五言杂诗。12岁考入本村初小,当时初小是4年学制,由于他刻苦用功,提前一年即毕业。他本想继续学业,无奈家境贫寒辍学回乡。不久,省立第二贫民高小在与他家乡临近的方山县开办,学杂费、书本费、制服费、伙食费均由学校供给。辛安亭征得父亲同意后考入该校,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
1923年,高小毕业后的辛安亭徒步跋涉4天,来到省城太原,报考进山中学。通过5轮筛选,他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排名第二。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可以在进山中学享受公费就读,因此他顺利完成6年的初高中学业,后到晋中祁县简易师范和祁县中学教了两年国文。
在积攒了一些积蓄后,他于1931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红楼这座闻名中外的学术殿堂里,他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还和在北京就读的原进山中学同学裴丽生、宋劭文、刘岱峰、狄景襄、席尚谦等组织“宏毅读书会”,探讨研究救国救民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他们深入研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阅读苏联文学和各国进步作品。
这一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抗日救国浪潮的呼唤,坚定了辛安亭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师长的教诲,益友的帮助,加上他少年时代艰难坎坷的求学经历,使他确立了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志向。
为边区编写新型教材及通俗读物
北大毕业后的辛安亭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绥远省正风中学、太原师范学校等校任教。由于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抗日救国进步思想,被国民党山西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为名逮捕入狱。后因未找到证据,才被释放。
这段72天的牢狱经历,使辛安亭对随意剥夺人权的国民党失望至极,促使他更加向往共产党。1938年3月,他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7月,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之后,他于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边区小学仍沿用国民党当局编写的课本,不仅知识陈旧,远离社会现实,而且充斥着封建糟粕思想。根据党中央精神,结合抗日形势,辛安亭等人从教材内容到编排体系进行了大胆革新。编写教材的有4人,他们同住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集体讨论、拟定编写宗旨和具体要求,并埋头苦干于各自负责的科目,常常加班至深夜,编写出小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本,为边区新型教材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此外,根据不同受众需求,辛安亭还编写了许多儿童读物、民众识字课本、工农干部识字课本及《新三字经》(后改称《儿童三字经》)《日用杂字》《农村应用文》《中国古代史讲话》等通俗读物。
辛安亭编写教材和通俗读物特别注重深入浅出,朗朗上口,如《新三字经》第一部分开头:“好娃娃,爱家庭,帮大人,做事情。腿又快,手又勤,眼又尖,心又灵。也抬水,也扫地,也烧水,也喂鸡。”又如民众识字课本中编入群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不识字真可怜,做起事来不方便。不会写,不会算,拿起报来不会看。写不了状子真作难,快快来上识字班。”再如《中国古代史讲话》将中国古代各朝代连缀成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两宋,元明以后是清朝。夏朝以来四千年,公元前后各二千。东汉以后公元后,西汉以前公元前。”简洁明晰,易诵易记。这些教材和通俗读物不仅受到群众欢迎,而且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作家吴伯箫读过《新三字经》后,专门写信向辛安亭致敬。历史学家范文澜十分欣赏《中国古代史讲话》,称赞辛安亭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爱民族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辛安亭在陕甘宁边区从事教材编写工作11年,编写出小学课本及各类通俗读物40余种。由此,边区流传有“政府的林主席(指林伯渠),编书的辛安亭”之说。1944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辛安亭被评为甲等教育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
深耕大西北文教园地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辛安亭随军到达甘肃兰州。1949年8月,他作为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带队接管兰州大学。一进驻学校,他就宣布了党中央保护全校教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方针,并明确表示支持原校长辛树帜继续执掌全校校务。
当时,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下,一些教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准备收拾行装向国统区转移。辛安亭面临的紧迫任务即是探索一套具有新中国特点和发展方向的教育思想和方针策略,否则对旧教育的接收就只能是接收一个空架子或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接收过程中,他注重调查研究,多次与诸多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沟通交流,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如“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兴盛之本”“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教育要继承传统,向世界学习”等。一大批教授、学者正是在与他的交往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态度。由于辛安亭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拥护,短短几个月就恢复了教学秩序,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度,安定了人心,彻底粉碎了有人企图煽动部分教师外逃的阴谋,翻开兰州大学新的一页。
1949年12月,辛安亭被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又被政务院任命为甘肃省文教厅厅长,同时兼任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辛安亭夜以继日,为建立新教育制度呕心沥血,为甘肃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统编教材
1951年8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为该社社长、总编辑,辛安亭出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此,他协助叶圣陶承担起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任务。
依据当时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特别是新颁布的学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叶圣陶和辛安亭共同主持编写和出版了第一套教材(1951—1953)。这套教材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的正常供应和平稳过渡,建立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虽然这是一套在全国中小学普遍使用的通用教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编教材,还存在一些其他版本的选择,也没有做到学科全覆盖。
1953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从全国各地抽调学科专家汇聚到北京,开始了统编教材的编写编审工作。在编写实践中,辛安亭不断总结新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编写规律,明确提出3个要求:一是要“新”,即要吸收科学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不断更新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二是要“精”,即在保持本学科必要的完整性、系统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础知识,讲深讲透,不可贪多求全;三是要“清”,即要写得清楚明白,简洁易懂。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统编教材全部出版,投入使用。这套教材观念与时俱进、内容科学严谨、结构简洁明晰,受到全国各地中小学师生的普遍好评,为新中国的教材编写作了奠基性工作,使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受益。
再赴西北,被誉为“甘肃的孔夫子”
1961年12月,辛安亭再度衔命返回兰州。彼时各省大多有了教育学院,唯独甘肃还是空白。应甘肃省委省政府之邀,他受命创办甘肃省教育学院(今兰州文理学院),出任党委书记兼首任院长。他广纳贤士,组建师资队伍;悉心调研,编写适用教材。他大胆起用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名教授、学者,如留法数学教授段子美、法学教授吴文翰、中国最早留美学习电化教育的南国农教授、留美博士邹念鲁、美术教授张介平,以及民国时期的高才生匡扶、刘滋培、吴福熙、霍旭东等。短短的三四年间,辛安亭白手起家,从既无师资又无校舍起步,把这所培养教学骨干和师资力量的高校办得生机勃勃。
1973年,辛安亭第二次进入兰州大学,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任命为该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书记、校长缺位)。他以古稀之年忘我工作,大力整顿干部和教师队伍,整顿教学秩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一大批蒙冤的教师、干部平反昭雪,同时建立新的领导体系和教学体系。几年工夫,使得兰州大学的工作重点很快转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正轨上来,校风和学风得以逐步恢复。他这次在兰州大学任职11年时间,直至1984年离休。在2009年兰州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仪式上,该校将辛安亭列为为该校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校长之一。
为了更好地联系教育界同仁,身为共产党员的辛安亭于1982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甘肃省8个民主党派正酝酿筹办一所民办大学,由于辛安亭威望颇高,年近八旬的他被一致推举为该校首任董事长。之后,他殚心竭虑,东奔西走,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实际困难,很快就办起甘肃省历史上首所民办大学——金城联合大学。离休后,他仍担任兰州大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教育学会会长、甘肃省人大常委等职务。
辛安亭一生情系党的教育事业。他严谨治学,辛勤耕耘于教材编写工作;为人师表,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的著述涉及教育、文史、教材建设和通俗读物多个方面,共计400余万字,有的通俗读物印刷量超过100万册,可见其影响之大。他编写的教材和通俗读物既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吸收借鉴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他对学校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课堂教学、学生考试及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创新观点和实践方法。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