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上的医疗救护
作者: 周铁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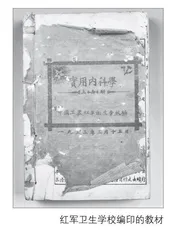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不断,伤员数量持续增加。而红军医护人员有限,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材,伤病员经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另外,红军部队在艰险残酷的环境中日夜兼程,将士们衣物匮乏、粮食不足,寒冷、劳累、饥饿导致他们抵抗力下降,极易发生各种疾病。红军的医疗救护面临严重困难和巨大挑战。
为改变不利局面,中革军委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医护宗旨,建立了高效的战地救护队伍,为保证红军将士的生命和健康,壮大革命有生力量,赢得长征最后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走到哪里,医疗救护必须跟到哪里”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决定:师级以下医疗单位人员全部重新编组,分派到各团、营、连一线部队,设卫生队、医疗站、救护组等,保证伤病发生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同时根据伤势、病情决定是否送上一级医院。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要求医护人员:“红军走到哪里,医疗救护必须跟到哪里,及时救治、维护将士的生命与健康,保持战斗力。”
总卫生部还从各部队每个连抽调1名战士作为卫生员,参加为期两周的医疗救护短训班。结业归队时,每人配备止痛用的吗啡注射液10支、阿片10片,碘酒、高锰酸钾消毒液和绷带、药棉,医用剪刀、镊子、缝合针线等。他们虽只能做消毒止血、缝合包扎、取子弹和弹片等简单的处置,但这些处置和小手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将士们的伤势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救护。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创办卫生学校,时任学校教育长的李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办的卫生学校,有军医班、调剂班、保健班和看护班,总共有五百多名学员,由各方面来考察,其成绩都不差。”在长征艰难的环境中,红军依然十分重视对医护人才的培养。1935年2月,卫生学校利用部队在遵义休整的时机筹备复课,仅用3天就从前线各部队调集学员200余人,备齐教材,排好课表,开始分班授课。
卫生学校从1931年创办到红军长征出发前的3年多时间里,共培养出学员686人,有效增强了红军的医疗救护力量和防病治病能力。
同时,红军还注重招收通晓医术的专业人才。民间郎中、草药师大多懂中药、善偏方,但缺乏西医诊疗知识,红军医护人员就手把手教他们测体温、测呼吸、量血压,以及清创、缝合、包扎等外伤诊疗、护理技能。
长征中,红军野战医院都要随部队同行,各医院按伤病情不同,以“能走长路、不能走长路、不能走路”为标准,将伤病员分别编为“重伤”“轻伤”“休养”“康复”连队,安排跟护、搀扶、担架等。对短时间难以治愈的伤病员,则做好思想工作,留下足够的生活费和药品,安置在当地可靠的群众家休养。
为预防多发病和传染病,总卫生部制定出《行军卫生条例》,利用标语、传单、文艺演出等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如“出发前要带足凉开水,检查鞋是否破损,绑腿不要过紧过松;不吃不知名的野菜、蘑菇和不干净的东西;宿营时要挖厕所,要用热水洗脚;野外露营尽量多铺稻草”等。
翻越雪山时,医护人员要求每个战士多带烧酒、辣椒、生姜,多穿衣服、吃饱食物;随身物品尽量减轻;每人要带强心药,散寒止痛的济众水;不可途中睡觉等。这些卫生知识在部队中深入人心,有效起到了预防作用,保证了将士们的健康。
同时,总卫生部还颁布《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等规定和条例,完善了各级医疗卫生勤务的工作制度。
“只要有一点希望,就绝不放弃”
1931年10月,中革军委在江西兴国创建红军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1934年10月,总医院跟随部队长征,医护人员无私无畏、忘我付出,救护、治愈了大批负伤患病的将士。
每逢重大战役,总医院都要派出医疗救护队驻守前线,并根据战事发展、变化,在战场周边建立临时医院或医疗所,同时在前、后方之间设转运兵站,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休息、治疗。湘江战役中,红军重伤员大量增加,需用担架抬行,总卫生部调集480名战士组成担架队,由总医院指挥,负责转运重伤员。
1934年12月,红二、红六军团先后攻占湘西的永顺、大庸(今张家界)、桃源等地,前、后方距离拉长,总医院就在大庸建起临时医院,收治从各个战场转运来的100多名重伤员。
参加长征的各军团所属医院中,由傅连暲院长率领的中央红色医院最为著名。傅连暲曾是红军卫生学校首任校长,培养出一大批部队急需的医护骨干。他本人也医术高超,尤其擅长西医内、外科和传染病防治等,曾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治愈疾患,也为刘伯承、王树声等诸多红军将士治好了伤寒、疟疾等,毛泽东赞誉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连暲医生就是华佗。”
傅连暲参加长征时已年近半百,还患有严重肺病,征途上的高原气候不时让他心慌气短、行动困难。总卫生部为照顾他的健康,特意派了一顶轿子,但他坚持不坐,大多时间跟随部队徒步行军。红九军团医生涂通今晚年回忆说:“傅院长在工作中有一句口头禅:‘只要有一点希望,就绝不放弃。’行军每到宿营地,他把背包、药箱和干粮袋一放,就带人支帐篷、搭炉灶,点火烧水,消毒医疗器材,或为伤病员体检、换药,或跑出去到附近群众家找木板搭手术台,连夜为伤员做手术。”
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发起娄山关战役,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激战中小腿负伤,一连包了10多层药布,鲜血仍向外涌,但他依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3天后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才被人用担架抬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解开包扎一看,伤口已严重感染,必须立即从膝盖以下截肢,否则菌毒入血,危及生命。当时,医院的药品长时间得不到补充,已没有麻药,只能用草药熬制的麻醉膏外敷止痛。
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钟赤兵疼得几次昏死又几次苏醒,术后没几天却伤口感染,腿肿得像水桶,持续高烧使他不时陷入昏迷。军团长彭德怀来医院看望,见他病情危急,叮嘱傅连暲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活。傅连暲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会放弃,但从伤情看,只能再次截肢。”
这次手术一周后,钟赤兵的创口又开始化脓,只得又一次截肢。他半个多月历经3次大手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他翻越雪山,穿过草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李治回忆说:“第二次到遵义时,住在一个大洋房内,红色医院收容了娄山关战役的重伤员……没有一个发生意外的危险。”中央红色医院医生张汝光也回忆说:“第二次进入遵义后,部队获得10余天的休整,我们用总医院援助的麻药,为来不及做手术的伤员都突击做了手术,使80%以上的伤员治愈归队。”
红军的“药房”遍山野
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药品和绷带、药棉、碘酊等医疗物资主要靠从敌占区购买、战场缴获、打土豪没收来补充和储备。长征出发时,总卫生部携带了200多担医疗物资,并预发给各部队约3个月用量的药品。但路途上经历大小战斗无数,尤其是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伤员激增,医疗物资基本用尽,加之部队逐渐摆脱敌人追截,行至人烟稀少地区,药品等医疗物资补给愈发困难,医疗救护条件也越来越差。
为让负伤、患病的将士们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护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用土办法疗伤治病。没有纱布、绷带、药棉,他们就撕开旧军装,将布和棉花用碱水洗净、煮沸消毒后使用;用牛油或酥油代替凡士林来配制软膏;用木板、竹片做夹板固定骨折部位;用牛羊肝脏治疗雪盲症;用大蒜液、生姜汁预防和医治感冒、痢疾等。
红三军团卫生处的饶正锡晚年回忆说:“长征路上我带的一本《中草药手册》,为我们采草药帮了大忙,当时红军医生都是学西医的,不懂中药,这本书正好充当了老师。我们从中不但学会了识别草药,还记住了许多验方。”
1935年8月,红军来到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一带,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发起高烧,多次注射退烧药都降不下来,时常昏睡,生命垂危。战士们从黑水县城请来一位老中医,他为洪学智把脉后说:“不用急,是伤寒,我开个方子,先带你们去‘药房’拿药。”
“药房?”大家不解地问。
老中医微微一笑,指了指窗外的大山说:“那里就是药房。”说着带领几个战士进山,采回10余种草药煎汤,洪学智吃了3天就病症全消。后来,战士们也把出去采草药称为“去药房拿药”。
长征时,为摆脱敌人追堵,红军多走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的小路、山道,腿脚常被尖刺划伤,夜间行军常发生摔伤、骨折;行至高原地区,许多来自南方的将士水土不服引发胃肠病、皮肤病,加之粮、盐等短缺,导致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患病人数急剧增加。另外,宿营环境恶劣,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蚊虫肆虐,非常容易流行传染病。
1934年9月,四川城口地区爆发疟疾,当地人称“鸡窝寒”。红四方面军到达这里时,正值“鸡窝寒”大范围蔓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疫情肆虐,立即派医护人员去中央红色医院求援药品和抗疫方法。红色医院派来一位富有治疗疟疾经验的老中医,他带领大家采集中草药,熬成汤剂发给部队将士和群众服用,不到20天,患者病情好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百姓称红军是“救命的活菩萨”。
为预防、治疗多发病、流行病,医护人员除用草药煎汤外,还将其烘干舂粉,制成膏、丸、散,如疏肝理气、消郁祛滞的胃痛丸,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三七膏,防治暑热虚脱、头疼头晕的藿香水,治疗风寒感冒、咽喉肿痛的柴胡液等。
有一次,傅连暲见一个红军战士牙疼,整个腮帮都肿了起来,就让对方咬住一个黑药团。不一会儿,战士开始口唇发麻,傅连暲立即把坏牙拔了下来。那个充当麻醉剂的黑药团,就是他行军路上采集草药制成的。
过草地时,董必武双脚发炎,疼痛难忍,医护人员用草药制成的“钻地蜈蚣粉”敷涂,他的脚疾很快治愈;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患上伤寒,领导让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坚决不同意,找到女军医何曼秋请教快速康复的办法,何医生给了他一小包焙干的“蝥虫散”,吞服了几次就逐渐好转。
不畏艰险的女医护员
红军长征队伍里的女兵,大部分工作在医院、卫生队、救护站等。她们不畏艰险、尽职尽责,以执着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肩负起战场救护、日常护理、转运伤员、筹集药品等艰巨任务。
红二十五军医院有7名女医护员,上级曾两次劝她们留在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担任繁重的医疗救护任务,她们尽心竭力、细心周到,不让一个伤员发生意外。徐特立曾在回忆录《长征中的医院》中赞誉女医护员:“她们要沿途雇担架民工,进行民工及伤病员教育和关照工作,所雇民工不够时,自己也抬担架……女医护员总是从道路的两旁到群众家里去宣传鼓动,因此部队行50里,她们就走了60里或65里。”
时任红军医院医护组组长的赵桂英晚年回忆说:“长征路上,医护员要每天给伤员洗血绷带,洗起来水里都是刺鼻的血腥味,然后就是为伤员包扎创口、打针换药、喂水喂饭等,千方百计减少伤员的痛苦。遇到飞机轰炸,首先要保护担架上的伤员,有的医护员就是为掩护伤员受伤或牺牲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女医护员,不但在炮火硝烟中勇敢地救护、转运伤员,还要为伤员的日常生活操劳:没有粮食,她们就去采野菜、剥树皮,掺上米糠蒸成窝头,给伤病员充饥;伤员的衣服破了,就缝补或收集布料重新缝制;遇到自理困难的重伤员,就一口一口地喂药喂饭。她们日夜轮流精心救治、护理伤病员,挽救了许多将士的生命。
红一方面军卫生团的女医护员危秀英,虽身材矮小,却是抬担架时间最长、救护伤员最多的一位,她的事迹多次在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上刊载。一次,危秀英和战友邓六金去寻找粮食,邓六金不慎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四肢无力、瘫软在地。危秀英毅然背起邓六金在险要的山路上艰难前行;实在背不动了,就架着她一步一步挪动。本来30多分钟的路程,她们用了2个多小时才与前来寻找的战友会合。
娄山关战役时,危秀英发现一位腿部受伤的高个子战士行动困难,她立刻上前搀着伤员行走。伤员见她几步一歇,累得气喘吁吁,就劝说:“同志,放下我,不能拖累你。”这时,后面响起敌人的枪声,危秀英猛然发力,一鼓作气把伤员背进300多米外的山坳里隐蔽下来,救了他一命。1957年,危秀英到北京开会,竟遇到当年那位被救的同志,这才知道,他叫廖志高,已是四川省委第三书记。
长征路上的女医护员,人人身兼多职:部队宿营或驻扎休整,她们要筹集粮食、药品,走街串巷刷写标语、作演讲,向百姓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主张,还要参加文艺演出,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红军长征途中的医疗救护,是红色医护人员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作出的巨大奉献,是他们“一切为了伤病员”的使命与担当,是他们恪守职责、无畏险阻、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的生动体现,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医疗卫生史册中光辉的一页。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