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凤群《大望》的老年书写
作者: 李冰摘要:李凤群的小说《大望》以老年人为叙述对象,在困境假设的叙事策略下使得老人们落魄还乡,书写了老年群体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困境。《大望》不仅在形而下的层面再现了当代老年群体的现实生存境况,而且在审恶历程中不断地逼近与审视,探寻人性的深处,试图通过忏悔的方式实现困境的突围,具有形而上的追求,是当代老年文学创作的一部优秀之作。
关键词:《大望》;老年书写;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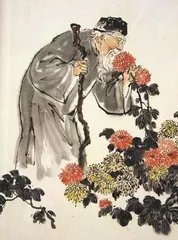
李凤群是70后的实力作家,从《大江》《大风》《大野》到《大望》,她以恢弘的气魄和优异的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作品广受好评。小说《大望》主要讲述了在夏日的某一天,赵钱孙李四位老人毫无预兆地陷入某种异常的困境,儿女们把他们遗忘,而在城市的他们无依无靠,处境艰难,于是不得不返回故乡大望洲。四个人在大望洲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迫去正视曾经视而不见的东西。事实上,由于启蒙语境现代性诉求的影响,中国人内心深处暗含“青春崇拜”的情结,老年群体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被严重遮蔽的形象,他们往往在传统的“新/旧”二元对立架构中作为青年形象的陪衬对应物,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子夜》中的吴老太爷。值得一提的是,李凤群以敏锐的文学触觉突破了传统书写的桎梏,回归个体生命本身,聚焦于老年群体的生存之艰和精神之困,挖掘当代老年人的灵魂隐秘,解读自我突围的路径与方法,为中国老年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空间和借鉴路径,对其书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叙事策略:困境假设下的落魄还乡
困境假设是中外文学常见的一种叙事方法,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把主人公安置在一个极端贫困潦倒或富贵显赫的现实处境,通过命运的骤然变化使人物的情志错位,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则会直接设定荒诞不经的假定困境来暴露世界的深层奥秘。李凤群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荒诞的艺术手法,正如卡夫卡把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一样,“像是有一只手在搅动他们的生活,破坏了这个世界的秩序”[1]。她把四个老人放入一个荒诞的困境之下:儿女将他们遗忘了,他们不被这个世界认可了,这对于高度重视伦理关系的中国老人来说几乎是世界末日,小说在构建写实的语境的同时具有现代主义的因子。
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认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建立在平衡和打破平衡的关系上,在破坏的过程中孕育着对抗的力量和满足性的力量,于是在破坏之后又企图建立起新的平衡。《大望》的困境假设实质上是为了打破原本平衡的关系,李凤群通过这种魔幻的叙述把人打出正常的生活轨道,让四位老人到另一种生活环境中去,把内心隐蔽处显示出来。如荣格所言,人都是有角色面具的,即使情境有所变化,也能够在意识的作用下迅速调整。只有在动态、动荡的情况下,把人物打出正常的轨道之外,使其来不及调整,其内心深层才能暴露出来,而逆境、倒霉或灾难就是使人物的情志错位[2]。她要逼迫四位老人无路可走而“落魄还乡”,这里的乡就是指生养他们一切行为观念的大望洲,它承载着老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记忆与心理经验,在这里方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实验。现代小说的还乡模式以鲁迅的《故乡》《祝福》等为肇始,通常包括“离去—归来—再离去”三部分,故乡代表着愚昧、落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回归原乡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批判落后的“原乡”,也有着新的前行方向。沈从文和废名笔下的故乡则偏向于一种精神之乡。而《大望》中的老年人的离去本身并非主动行为,随着子女在城市中安家乐业,他们只是依附而去,没有清晰的认知意识,对原乡既无批判之意也非精神寄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罪恶之渊薮”的象征场所。对四位老人而言,离开并不能掩盖过去之行的烙印,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太可能主动返还故乡,而作者一定要让他们直面某些东西,需要一个返乡的机会。
《大望》中的四位老人分别是老赵、钱老师、孙老善和老李,他们曾是大望洲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村干部和家庭主妇。年老之后,都跟随子女离开大望洲去了不同的城市。“大望洲的青年人,去了城市;大望洲的老年人,或进了坟墓,或去了城里。随着最后一批老年人的离开,大望洲最终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岛,缄默不语,静静等候。”[3]人们陆续离开,标志着大望洲成为一座真正的孤岛,这个曾经生养他们的地方渐渐被遗忘,成为一片荒芜。老人们在城市中依附子女生活,无人知晓他们的过去,因此可以戴上一层厚厚的面具。在城里,老赵尽管只会“放放血”,不影响他常常夸大自己的行医事迹,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还将他的只是普通外科医生的儿子说成是院长;钱老师学历不高,如何当上老师且为何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却始终没有转正,这背后的故事无人知晓;孙老善因儿子是大望洲首富,又为人宽厚,在城市里俨然成为人见人爱的慈善家,可他的小儿子在部队牺牲,夫人去了九华山修行,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隐情;老李的女儿为何不肯认自己的母亲,这同样是个谜题。在李凤群假设的极端困境之下,老赵目睹儿子完全不认识自己时的冷漠,而当他想要质问对方时竟然失语了;钱老师兜兜转转也找不到三个儿子的家;孙老善如同空气一般被儿子无视;老李也联系不上女儿。对于丧失个人生存能力的老人,这无疑是绝望的,他们没有钱,没有居所,而唯一能容纳他们的地方只有故乡大望洲,大望洲能提供基础的生存条件,庇护落魄还乡的老人。“三个人的头上和脚上都湿漉漉的,他们不像从只需四个钟头车程的上海、两个钟头车程的南京和一个钟头的开城而来,他们像从大西北的沼泽地、珠穆朗玛峰还有南极而来。再一看,又像三个刚刚溺水被救出水面的幸存者,满身满脸写着四个字:落魄还乡。”[4]四位老人在城市生活久了,看似已经成为所谓的城里人,但他们的行为逻辑是来自大望洲的。在这里,他们会被迫直面曾经的一切,跟遗忘的记忆抵抗。老人们想尽方法寻求破解之策,却始终无法解开谜团,直到发现“讲真话”的秘诀后,对人性的考验悄然来袭,作者的“上帝之手”逼迫他们去揭开过往的遮羞布。
二、所向何方:老年群体的生存困境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大望》,老年书写,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忏原版全文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人,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末,年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我国总人口的21.1%,65岁以上的人群占总人口的15.4%,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社会中涌现出的种种问题亟须得到更多关注,李凤群认为,“作家把现实问题带进作品,这是职责,也是本能。因为文学作品不能放弃社会性,不应该在空中楼阁中完成。”[5]在此文学观的关照下,李凤群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基于对老年群体的密切关注,把四位老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意图揭露老年危机的现状,真实展现当下社会和时代老年群体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困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社会学意义。
《大望》中的四位老人,分别姓赵钱孙李,这对应了我国《百家姓》最开始的四个姓氏,如此设置,他们的形象就具有了泛指意义,意在揭示老年群体共性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身体层面的焦虑,老年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疾病对于生命的威胁常常使老年人产生对死亡的恐慌。小说中的四位老人大多患有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失聪、心脏病等等,只能大把大把地吃药,最后孙老善甚至患上老年痴呆症,无法进行独立生存的基本活动。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乐生恶死”,老人们恐惧疾病与死亡却无能为力,展现出老年群体的无奈以及难以自理的窘境,与身体和解成为重要的必修课。其次,对于老人而言,伴随着身体退化而来的还有尊严失落的困境。不知何时,年龄开始成为当下社会身份评判的潜在标准,因为年老的身份,老人的精神尊严常常被忽视,很难得到社会认同,几乎是鄙视链的底端存在。四位老人在小说中几次被出租车司机耻笑,甚至在警察面前也没有得到信任的交流,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坏人,只怀疑他们是病人,是脑子出了问题。终于他们心灰意冷,深刻明白“老,似乎本身有一种符号,这个符号遮蔽了其他的信息;这个符号否定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威严,他们的体面,甚至是他们的眼泪”[6]。伴随着不可抵挡的身体危机的到来,老人们似乎不得不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除此以外,李凤群还觉察到当下老年群体的养老困境。中国高度重视血缘伦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个老人所希冀的。我国的养老模式自古以来是“反馈式”养老,即父母养育子女成人,子女再为父母养老。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当老年人失去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后,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变得尤为困难。小说中的钱老师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只能依靠三个儿子轮流抚养,钱老师患有各种疾病,做过手术,伸手要钱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他的口袋一向是空的,身无长物,只余药物。就算儿子是富豪的孙老善也没好到哪去,在小岛的生活可谓捉襟见肘。因此,当四位老人与子女断联后,他们最先面临的就是丧失了基础生存条件,不知该所向何方,何去何从。钱老师找寻子女无果,最初的反应是被遗弃了,但这一想法并不是杞人忧天。老人被弃养,是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部分子女对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不履行赡养和扶助的义务即构成遗弃罪。钱老师的担忧从侧面反映出部分老年人不安的心理状态,由于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儿女的赡养,常会充斥着可能被遗弃的恐慌。在家庭中,老人则会出现严重的存在感与价值焦虑的问题。老人们脱离社会角色回归家庭,从家长地位退居,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只能通过做家务、照顾子女孙辈等获取认同以证明自身价值。小说中几位老人在子女的家庭中都承担着类似作用。此外,相对于青年人,老年群体与快速发展的时代产生了一定的脱节,认知趋于窄化,生活在一起的两代人观念差异难免会产生代际隔膜。小说中老赵的故事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老赵不能理解儿子和媳妇的相处方式,对媳妇百般不满,多次干涉二者的夫妻关系导致儿子离婚。
总之,老年是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一段生命历程,李凤群在《大望》中从衰老病死谈起,呈现了老年人的身体、尊严、养老及认知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向我们展示了老年群体真实的生存图景,隐含着对老人生存关怀的呼吁,同时令人深思“我们该如何面对年老之困”?
三、忏悔之路:审恶历程中的人性困境
众所周知,人性是最为复杂的哲学命题,对于人性困境的探讨是文学亘古不变的追求。《大望》中的人性之困贯穿了小说始终,在除去年龄的外围特征后,更多地把重点放在老人作为“人”的层面上,审视人性自身。李凤群曾在访谈中谈及“对我而言,我一生的主题就是在写‘过错’与‘承担’”[7],这实际上是作家个人对忏悔意识的重视。忏悔作为文学常见的母题之一,“罪与罚”的故事可谓经久不衰。西方文学由于受宗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强调意识“原罪”与赎罪,出现了以深刻性和反省性著称的《罪与罚》《忏悔录》等世界名篇。而中国自古以来受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更强调“乐感文化”,推崇实用理性。中国的实用理性使人们较少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8]。这种文化传统致使中国文学中少有纯粹的忏悔意识出现。《大望》中具有忏悔色彩的主题,升华了小说的格局与深度。作者试图以引导人类忏悔的方式寻求人性困境的突围,表现出了强烈的自省意识与人文关怀。
何谓忏悔?忏悔是主体以自我为对象,经过良知的审判而自我知罪、归罪,且能够主动在忏悔中赎罪。《大望》中的赵钱孙李四名老人回到大望洲之后,逐渐发现每当他们坦诚过去所犯下的罪,竟有利于解除失联的困境,于是开始走向自我解剖的忏悔之路。每个老人陆续“解密”过去发生的事,秘密的暗门背后藏着世间的真相。小说的后半部分基本交织着现实与回忆交错的言说方式,在时空的跳跃中窥探四位老人忏悔的真与假。
孙老善的忏悔最具讽刺意味。孙老善年轻时是村干部,颇有良名,表面上人畜无害、乐善好施,因此被大家称为孙老善。但这样一个人来到大望洲后不停地褪去一层又一层的皮,最早开始遗忘自我、走向衰败,这和他的过往之罪脱不了关系。孙老善的小儿子小明被他逼去当兵,不幸在部队牺牲,夫人也因此离家去九华山修行。可小明的当兵名额是孙老善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挤去了耀祖的名额得来的。耀祖家境贫困,失去当兵资格后在外摸爬滚打,最后走上了犯罪的歪路。孙老善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明和耀祖的悲剧发生。作为村干部,孙老善包庇村民拐卖、殴打少女,带领村民不顾真相讨伐他人,自己的大儿子开饭店用地沟油也视若无睹。直到小明死去,孙老善才有后悔之意,他开始信佛,小说中多次提及孙老善引用佛经原文。佛教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孙老善认为小明的死是对他的惩罚,这暗示了孙老善在潜意识里清楚知道自己的罪过所在。在小说结尾,孙老善坦白了关于小明的事,可面对钱老师的质疑,老李“认罪是唯一的出路”的劝导,他还是拒不归罪,精神状态甚至变得歇斯底里,叫嚣着“如果我们有罪,全国人民都有罪”,声声怒吼彻底宣告了孙老善忏悔之路的失败。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大望》,老年书写,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忏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