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参与的三个维度
作者: 王怀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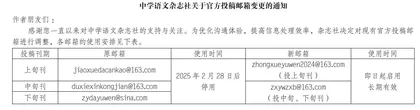
摘 要 发展逻辑思维,是语文学科课程目标之一。日常教学中的逻辑参与活动,时有形式化倾向。切实发展逻辑思维,须有严谨的教学设计。理据研判,是逻辑参与的基础和前提;规则剖析,是逻辑参与的核心任务;奥义探寻,是逻辑参与的深层目标。
关键词 逻辑思维 语言规律 逻辑规则
逻辑参与活动时常不可避免地呈现于语文课堂,但怎样才能用以切实发展逻辑思维,却是棘手问题。统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供了一则解决此类问题的素材: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形式上的逻辑参与,往往仅从“见孺子将入井而怵惕恻隐”便推导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空洞结论。其实我们可以扣住“乍见”二字分析,强调人们的“怵惕恻隐之心”是在“突然间”“下意识”的情境下生发的,这样,岂不更加符合事理逻辑?
逻辑参与是否高效,与理据、规则紧密相关,也制约着对微言、奥义的探求。
一、理据研判,是逻辑参与的基础和前提
逻辑思维活动,起始于对基本理论、事实依据的占有和运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强调“辨识、分析、比较、归纳和概括基本的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1],此过程需要以“理据研判”作为基础和前提。
赏析登临词的课例中,有时会缺少对登临地的研究。殊不知,抛却丰实的理据,赏读抓手已失,遑论发展逻辑思维!登临作品中的登临之地,不管是有意选之还是无意登之,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登临的基本意义是“登山临水”,且不论“山、水”天然具备的令中国文人登高伤怀、临水兴叹的元素,单是翻看教材中收编的登临佳作,多数登临地还兼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刘禹锡登上的是作为长江要塞的“西塞山”,孟浩然登上的是羊祜曾登的“岘山”,苏轼登上的是被他当成赤壁的赤鼻矶,辛弃疾还曾登临过建康一处所谓“赏心亭”。
作为理据,“登临地”之于“登临意”,常具指向意义,这在《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词人登临之地“造口”便可作为逻辑参与的理据。“造口”在今江西万安县西南,当时驻赣州执行公务常经造口的辛弃疾应当知晓,距其题壁四十多年之前,金兵在追击隆祐太后的过程中,大肆骚扰了包括造口的赣西一带。战事虽然发生在辛弃疾出生之前,但硝烟犹未散尽、伤痕已刻心底,因为这是立志做抗金志士的辛弃疾,是曾写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弃疾。这是一片伤心地,触碰了词人心头的敏感区域。在造口壁题写的《菩萨蛮》,便自然地带着“感伤”基调。
作为理据的,不仅有“造口”,还有“郁孤台”。郁孤台建在赣州西北的贺兰山顶,因其郁然孤起而得名。开篇“郁孤台下清江水”表明此台曾是词人登高远望的立足点,下文“西北望长安”也源于此。唐代虔州刺史李勉曾登台北望长安,表示心念朝廷。宋代文天祥也曾于登台后写下《题郁孤台》诗,留有“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倚栏时北顾,空翠湿朝曦”的忧国忧民之句。郁孤台“登临”而“念君”的文化内涵与辛弃疾的家国情怀相契合,这对“造口词”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规则剖析,是逻辑参与的核心任务
课程标准倡导逻辑参与要运用“基本的语言规律和逻辑规则”,这是因为,思维主要是通过语言传达的,而逻辑规则体现的正是思维的基本规律。重视语言规律和逻辑规则,是逻辑参与的核心任务。
以《巴黎圣母院》片段为例。一方面,作者用符合人物形象特点的语言极力刻画克洛德灵魂上的“罪恶感”,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揭示克洛德丑恶灵魂的一贯风格;另一方面,又用超乎寻常之笔凸现克洛德“尽管有罪恶感但冷酷性不减”的变异心理,从逻辑规则上看,这反映出的是克洛德的“人性畸变”。
可是当那头骡子靠近了刑台,使骑在它背上的神甫看清了犯人是谁的时候,那神甫却低下眼睛,用两只踢马刺踢着骡子急忙转身走开了,好像在逃避一声耻辱的呼唤似的,他很不愿意在那种场合被一个不幸的人认出来并且向他致敬呢。
作者说他“低下眼睛”,是否遵循了某种语言规则?有人也许会说这是表现克洛德为脱离干系而生出的掩耳盗铃似的神态,但是,面对自己的养子惨遭酷刑的场景,克洛德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丝罪恶感,这种说法应该不算牵强。克洛德“用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对自己放纵本能的举动进行谴责、评价,从而造成人内心的冲突和精神的折磨,产生出沉重的罪恶感”[2]。
从逻辑规则的角度看,事情远未就此结束。克洛德看到自己的养子在受刑,有了罪恶感之后,为什么“转身走开了”?不妨变换一种身份来想,假如现实中的你我就是克洛德,在有了罪恶感之后,会转身走开吗?一般而言,可能会有两种选择。要么现场声明“罪恶在我”,以表现人性之“善”(可惜克洛德不是这样的人);要么留在现场观看行刑,以强化人性之“十恶不赦”(可惜作者并没有这样写)。那么作者雨果还想表达出什么意图呢?
刻画一个人物形象,如果把他写得连罪恶感都没了,那么这确实写出了他的无可挽救,但这样的形象是一种“扁平”形象,也让读者少了一点逻辑参与空间。雨果在文中刻画克洛德形象,既表现其“罪恶感”,更表现其“罪恶感”之后的“冷酷”,这就写出了人性的畸变。
克洛德的人性畸变,类似于《雷雨》中的周朴园、《项羽本纪》中的吕马童。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含有某种真实的成分,但当这种怀念与自身名利、家庭稳定产生冲突之时,伪善便会撕破一切,这便是人性畸变。吕马童虽为项王“故人”,但在西楚霸王兵败之时,决然转身留下一个冷漠的背影,亦然。
需要强调的是,克洛德的人性畸变,符合逻辑规则,因为它缘于时代,缘于社会。这位生活于15世纪的副主教,本来一心专注于“圣职”,但正是禁欲主义思潮的长期压抑,使他人性天平两端的砝码(美、丑),在遇见爱斯梅拉达之后,瞬间失衡。
三、奥义探寻,是逻辑参与的深层目标
钩深致远,探赜索隐。追索隐秘事实、探究深奥义理,这既是逻辑参与的过程,也体现了逻辑参与的深层目标。司马迁称屈原之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不是一个简单判断,而是在对《离骚》精微之言和深奥义理深入探究之后作出的逻辑判断。探究微言和奥义,在语文学习活动中意义深远。
试看《李凭箜篌引》起首两句:“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这两句十四言,“高秋”“空山”“凝云”“不流”之语乍看甚似平淡,实则言简义丰。其中微言、奥义,必经深入探求方可得到。
首先,为何强调“吴丝蜀桐”?浅层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言音乐之美,先说乐器之精。写箜篌构造精良,借以突出音乐的高雅。深层看,不仅说材质之精良,而且有一定的文化意味。逻辑参与的具体方式是体验传统文化,比如,庄子用凤凰自况,说“鹓雏(神话中与鸾凤同类的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再如,《诗经·大雅·卷阿》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之语,梧桐是和凤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高贵、高雅的联想。
其次,解读“张高秋”,重在体味美妙乐曲声所创设的那种清澈澄洁的高远境界。逻辑参与的具体方式是,联系古诗词,发掘新思维。“张”,一般理解为“弹奏”,当然是可行的,但没能深入体会李贺的用意。若将“张”字解为“紧弦”(演奏前的一种准备活动),则别有一番风味。同为调弦准备,白居易《琵琶行》用的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显得闲逸从容。李贺用“张”字,则显得僵硬紧张,也衬出箜篌声的高亢坚硬,这就与后边的“昆山玉碎”相协调。
再看“空山凝云颓不流”,山是“空山”——苍穹之下,别无所有。人事和自然,都与山无缘。为何无缘?联想一下《列子·汤问》中抚节悲歌、响遏行云的境界吧,这一联想的过程,正是逻辑参与的有效过程。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体悟教学”阅读与表达校本课程体系开发与实施》(批准号:TSXM/2021/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6.
[2]唐迎欣.伊甸园中的背叛:西方文学中的神父类型及文化底蕴[J].玉林师专学报,1999(1):56-60.
[作者通联: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