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隐身衣》,用“眼睛”聆听的音乐
作者:孙若茜(文 / 孙若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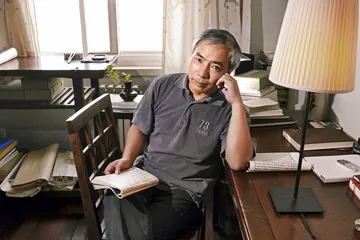 ( 格非 )
( 格非 )
KT88、《培尔·金特》、奶妈碟、“萨蒂,《玄秘曲》”……小说章节的命名,有专业器材名称,也有乐曲名称。
音乐发烧友能轻松读懂这其中的暗号,观看同为音乐发烧友的主人公为高端客户定制音响设备为生的种种境遇时,就好像伴着音乐进行。小说中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与音乐存在某种对位关系,文字本身就像是那些乐符的注解,反倒造就了一场想象中的音乐盛宴。
在故事框架和人物设置上,依然可循音乐性。欧阳江河解读这本小说,就把与男主角相关的四个女人比作四重奏,母亲是大提琴,姐姐是中提琴,两把小提琴分别是前妻玉芬和后来的“玉芬”。而格非告诉本刊记者,在他看来,音乐是最神圣的,它包含了人类重要的秘密,因此所有的艺术都向音乐靠近。虽然在写作中他并没有真的去设置谁是第一小提琴,谁是第二小提琴,但音乐听多了的确会对写作造成影响,会慢慢发现:小说里也有主题展开和变奏,不知不觉就成了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读《隐身衣》,很明显能感觉它和《春尽江南》之间的某种联系,《隐身衣》是《春尽江南》的一个附属品吗?
格非:是的。《春尽江南》里的主人公端午是音乐爱好者,我写的时候,就在想要不要把音乐的部分放进去,后来我想适当地放一点,因为《春尽江南》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再去写一个爱乐人的生活会有点儿问题,所以《春尽江南》写完后我立刻就写了这个,确实可以说《隐身衣》是《春尽江南》脱胎出来的一个东西。
 ( 《隐身衣》 )
( 《隐身衣》 )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春尽江南》里有很多东西没有能全都表达出来,这些留在《隐身衣》里继续表达的主题,是不是欧阳江河所读到的“这个时代的耳朵聋了”?
格非:听力出问题,是这个叙事里很小的一个主题。实际上不仅是耳朵坏了,我们的眼睛也坏了,嗅觉也坏了,所有的感官都坏了,被一种甜腻的文化,喧闹的波段,把口味败坏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其他比较复杂的一些想法。
《春尽江南》对我来说可能过于沉重了,读者读的时候也特别压抑。我就试图在《隐身衣》里做一些变化,里面有一些古典音乐,音乐本身能给人一点温情。另外,叙事语调上采用了第一人称,可能相对于冷漠的第三人称,会更亲切一些。
还有一个,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忧虑感喟,就是我们怎么面对生活,确实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也是《春尽江南》里不能包容的,我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小说看似有哥特式的结尾,有些地方故意笔下留情吗?
格非:对。我对生活的观念有些变化,人在生活中,生活已经够糟糕的了,还是需要有某种安慰,需要我们对生活中的某种价值的确认。我们现在很可怜,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好的空气、阳光,这些原来根本不需要金钱购买的公共空间的东西,都一天天地被毁坏;你可以拿到手的,或者可以希望的有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很多人生活在一种非人的状态中,大家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怨妒。所以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尝试给读者一个新的暗示,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边试图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边认真地来固守自己内心好的东西。
在这个小说里,我还是在很多地方留了情面,没有特别残酷地把生活里的东西揭开,这个实际上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区别于《春尽江南》的写法,我不太想把那些过于触目惊心的现实暴露得特别厉害,而是希望故意有所收敛,让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最重要的是怎么去生活,音乐这个美好的东西在这个小说里是一个象征。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包括主人公所认为的音乐发烧友所组成的乌托邦,到最后也没有被现实戳穿,甚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也还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格非:换句话说,这种心理其实就是我的心理,我在别人手里买过无数的唱片,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很多器材也都是通过互联网从不同的地方买回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件让我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跟这些发烧友打交道都是先付钱,然后再发货,三四天货就到楼下了。
我在小说里写乌托邦的时候是自己的一种体会,每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经常被人骗,而我周围的发烧友都非常好,是一个紧密的联盟,有好的信息大家会交流,感情上来往也很密切,确实是音乐这个媒介让大家聚到了一起。所以,我从某种意义上坚持小说里描写的乌托邦。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里好像一直在说:“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格非:发烧友这个群体我接触得太多了,这些人首先我还是比较尊敬,哪怕他们已经被物质化的东西迷惑,去选择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有几个发烧友已经去世了,他们一辈子都想做出中国最好的音响,花了无数精力,最后中途死了,也有很多朋友花了上千万元去购置音响。
看到这些,你一方面会觉得没有必要,觉得他们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又会很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因为这些人的心里都是很悲观的。他们对生活中的乐趣已经视而不见了,把自己封闭起来,穿着一件“隐身衣”完全躲起来,陷进古典音乐很小的关于声色的事情里完全不能自拔。
这是一种新的欲望形式,只不过这个欲望打上了音乐特有的标记。对物质化的无止境的追求,确实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但我不讨厌这些人,我也经常去这些朋友家里听音乐。在我看来,发烧友这个群体确实有很多人都是病态的,但这种病态不是让人厌恶的病态,而是一种让人同情的病态,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隐身衣”是指音乐本身么,还是也包括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隐形的暴力和死亡?
格非:“隐身衣”的意义有很多,一个人喜欢音乐,音乐给他带来了一个屏障,使得你听音乐的时候忘掉痛苦,你可以暂时把自己隐身。也有很多人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乐趣全部放到对音响器材的物质性追求里,这当然也是一种隐身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这么个东西,都穿着这么一件衣服,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个符号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有一种人认为他对生活中所有问题都能掌控,这个世界是非常清晰的,世界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未来很清楚,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另外一类人认为,虽然我们这个世界被曝光得很厉害,但是世界仍然是神秘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里留有很多没有交代的东西,比如蒋颂平和他姐姐的关系,以及丁采臣的故事等等,你有打算再写一个版本来揭开多处留白造成的悬念吗?
格非:我原来有过这个打算,可能会写两个版本,丁采臣写一个,蒋颂平写一个,分别用他们的第一人称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其实都有他们的理由,这里面很复杂。
在“我”的故事里,丁采臣是一个背景;在丁采臣的故事里,“我”可能是个背景;我希望在写丁采臣故事的时候,《隐身衣》里面的人物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就是以背景出现,不一定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但我写作不是为了提供答案或者揭开谜底,我要写的故事是单独的,如果说跟《隐身衣》有关系,那就是里面的人物可能会在某个关节点出现,会相遇。几部作品之间有桥梁会比较有意思,但并不见得会把悬念解掉,也可能会设置更多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每个章节都用器材或是乐曲的名称命名,这是一种故意用名词堆砌的写作手法,还是可以算做发烧友之间的一种密码?
格非:任何物质都一样,都是恋物癖对物的文化的某种想象,不懂器材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亲切感,没法理解一个线怎么会有美感,只有用过10条以上的讯号线或者喇叭线,才会知道线的原理,知道它为什么漂亮。
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知道绝大部分读者都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些对他们来说会有另外的感受,他们不知道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见过实物,但是他可能有其他的想象,这就足够了。
我在小说里写这么多名词,是希望给发烧友的生活提供一个物质保证,没有这个物质性,小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每个人物出场或退场时相对应的“音乐”好像也和人物有很密切的关系,一种音乐和写作的对位,比如丁采臣的人物感觉就很像萨蒂的《玄秘曲》。
格非:丁采臣对萨蒂的那种观感是不自觉的,他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但一下子就会喜欢上萨蒂的钢琴曲,而且说钢琴曲里有一种雾,这也是我听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它不让你看清楚。萨蒂的音乐特别简单,充满了色彩感,又很含蓄,丁采臣本人也是如此,不太想让人看清楚,很内敛,话不多,有很强烈的内心生活,但是他也会失控,也会把枪拍出来。这个人物也有一点病态,病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让人讨厌,但是在小说里是很迷人的。再比如“奶妈碟”,比如蒋颂平用的那些器材,跟他的人物性格是对位的,这个没有问题。但很多场合的安排也是随意的,不必深究。
三联生活周刊:《隐身衣》里似乎格外多地提到了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
格非:一方面现在听古典音乐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些老板,就像小说里蒋颂平那样的人,器材相当豪华,靠这个炫耀,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真正爱音乐的人主要在知识分子群里。
第二,我也很想把这个主人公和知识分子之间通过供货联系起来。我认为今天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最有意思的,或者说最让我担忧的可能是在知识界的这样一个争论,几十年来的一个争论,在最近几年来变得尤其激烈。但是在我看来,小说里面也写到了,表面上看好像很激烈,大家观点相左,但小说里有个观点,不一定是我的观点:其实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都是很简单的。
这是作为一个叙事者,我对知识界的忧虑。我也在这个群体中,很多道德化的话题背后都很复杂,你发现今天的争论空前激烈,但另一方面思想成果却非常可怜,离理性越来越远。小说里大家看出来好像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非常失望,确实如此。 文学小说发烧友隐身衣萨蒂格非眼睛聆听音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