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图画书文图关系之叙事互补
作者: 赵霞幼儿图画书有3种基本的文图关系模式:意义解释关系、叙事互补关系和趣味点缀关系。这3种关系模式的多元创意与交替组合,赋予了幼儿图画书丰富的文图艺术可能。上期介绍了幼儿图画书文图关系中的意义解释关系,本期重点介绍叙事互补关系。
在这一关系模式下,幼儿图画书的文字与画面虽然也共同讲述一个故事,但二者互为补充,文字与画面各承担一部分内容,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一关系中,如果没有画面的参与,文字部分会出现重大的叙事缺失;反之亦然。比如图画书《鳄鱼怕怕?牙医怕怕》(五味太郎?文/图),它的文字部分读起来是这样的:“我真的不想看到他……但是我非看不可。/我真的不想看到他,但是我非看不可。/……”如果仅看这些文字,读者大概会一头雾水。只有当我们同时看到对应的画面,才会明白这是发生在鳄鱼和牙医之间的一场趣事,而它的幽默感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文字和画面之间的上述互补。结合文图的共读,我们知道了首页文字叙述中的前一句“我真的不想看到他”,表达的是鳄鱼不得不去看牙医的心情;后一句“我真的不想看到他”,表达的则是牙医不得不给鳄鱼看牙的心情。一模一样的语言,表达的是同样的不情愿和不安,又恰好适合故事里彼此对位的两个角色;但在适合的同时,又从两者身上生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内涵:鳄鱼害怕的是什么?牙医忐忑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文与图的互补中既一目了然,又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于是,在文与图的巧妙配合下,简单的语言重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叙事和语言幽默效果。
再比如图画书《母鸡萝丝去散步》(佩特·哈群斯?文/图),其文字部分讲述了母鸡萝丝出门散步的简单行程:“她走过院子,绕过池塘,越过干草堆,经过磨坊,穿过篱笆,钻过蜜蜂房,按时回到家,吃晚饭。”但图画书的画面部分除了表现母鸡萝丝的散步,还讲述了文字中没有提到的另一半故事:在母鸡萝丝散步的过程中,有一只狐狸始终跟在她身后,其动机不言而喻。然而,狐狸试图逮住母鸡萝丝的努力却一次次遭遇滑稽的失败,先是踩到钉耙上,再是跳进池塘里,之后又陷入干草堆……这样,在画面和文字的叙说之间就构成了有趣的对衬关系。文字叙述的悠闲感反衬了画面叙述的紧张感:毫无危机感的母鸡会被早有预谋的狐狸抓住吗?但这紧张的悬念又一次次被悠然的情绪所化解:狐狸的预谋无一成功,而母鸡的散步从未被打断。故事独特的叙事趣味就在这样的图文互补中得到了充分的传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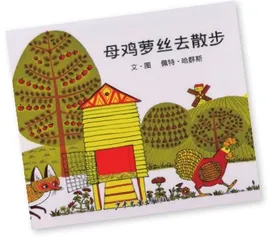
在当代图画书的艺术探索中,这一图文叙事的互补关系发展出了十分多样的形态。图画书《鼠小弟的小背心》(中江嘉南/文,上野纪子/图)运用这样的互补,讲述了另一个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句普通的自述起头:“妈妈给我织的小背心,挺好看吧?”画面上,小小的鼠小弟,穿着红背心,神气地站在中央。随后,鸭子、猴子、海狮、狮子、马、大象等动物先后穿上了鼠小弟的背心,相应的文字主要是以下对话的循环往复:“小背心真漂亮。让我穿穿好吗?”“嗯。”“有点紧,不过还挺好看吧?”如果只看文字,读者也许感到不知所云。同样,如果只看图画,则难以理解对话背后的角色关系、态度和情感。与此同时,每一次文字中表达的“穿背心”的强烈愿望,与图画中传递出的“勉强穿上背心”的挤压感,也构成了有趣的反讽。尤其是故事临近结尾处,当大象穿上背心,他巨大的身体占据了整整一个页面。这时,鼠小弟又出场了,他急得跳起来:“哎呀!我的小背心!”只见他拖着被拉长了的、再也穿不了的小背心,伤心地走了。看上去,图画书的正文到此就结束了,但它真正的结尾其实并不在这里—如果结束在这里,故事的心理感觉和氛围就是消极的,因为大动物成功地欺侮了小动物。让我们翻到封底看一看,在那里,小小的画框中央,被拉长的小背心成了一架红色的小秋千,挂在大象的长鼻子上,鼠小弟正坐在秋千上快乐地荡着。在图与文的完好互补中,它的幽默才是温暖、明亮和智慧的。

一般来说,幼儿图画书的图文叙事,其基本方向往往是一致的。但一些作品也会通过有意制造两者之间的叙事矛盾,来营造特殊的表达效果。比如图画书《大卫,不可以》(大卫·香农?文/图),与每一页上的“大卫,不可以!”“不行!不可以!”等命令文字相反,对应的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那个正在违反禁令的孩子的快乐身影。这样充满喜剧感的矛盾场景,大概写出了现实中许多幼儿的普遍生活状态;而在这一切的矛盾和对立之后,故事最末的那句“我爱你!”和那个爱的拥抱,也才显得尤为甜蜜和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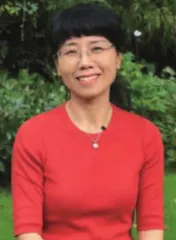
赵霞,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出版有《阅读是最美的礼物——0-6岁亲子阅读指南》《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批评的体温——赵霞评论选》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