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汽车央企战略性重组:全球汽车产业的拐点之战
作者: 杨继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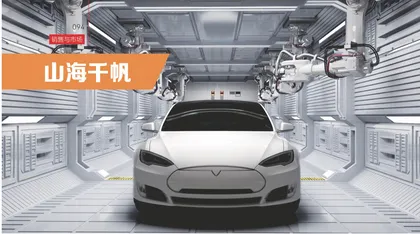
如何在保持“汽车国家队”底色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转型,是横亘在三大汽车央企面前的根本命题。
卷到极致的中国汽车产业,终于迎来破局时刻。
在3月底结束的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三天汽车央企(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即将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消息成为焦点。这场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导的汽车行业变局,将如何改写全球汽车竞争格局?即将登场的“汽车国家队”,将会对上下游产业链、技术研发路线以及“汽车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带来哪些影响?对于传统民营车企、外资车企及造车新势力而言,汽车江湖又会迎来怎样的风风雨雨?
接下来,我将从产业整合、竞争格局与全球化布局等层面,解构这场变局之后的本质与趋势。
重组前夜:百年汽车工业,来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1886年1月29日,德国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KarlFriedrichBenz,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者、“汽车之父”)成功研制了单缸汽油发动机,发明了全世界第一辆不用马拉的“三轮车”,这一天被视为“汽车诞生日”,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也由此赢得了“汽车发明者”的殊荣。
接下来的130余年,汽车行业不断上演“宝刀屠龙、谁与争锋”的戏码:英国的罗孚、捷豹、路虎,德国的奔驰、宝马、大众,法国的雷诺、标致、雪铁龙,意大利的菲亚特、兰博基尼、法拉利,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日本的丰田、本田和日产,韩国的现代、起亚,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都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BBA(奔驰、宝马与奥迪)的品质神话、福特的大规模流水线、丰田的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丰田生产方式)等,也都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进入21世纪,来自中国的一汽、东风、长安、上汽、广汽、北汽、奇瑞(国有控股)等国企厂商与以吉利、比亚迪、奇瑞(已实现股权多元化)、长城等为代表的民营车企,再加上以华为(官方多次表明“不造车”,此处特指华为旗下“鸿蒙智行”)、小米、理想、小鹏、蔚来、零跑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它们正快速成长为全球汽车产业的中国力量。当下,正值以“汽车新四化”为代表的全球汽车产业革命如火如茶,标准、话语权、产业链、游戏规则等,都在发生改变。
马斯克的特斯拉与王传福的比亚迪,正成为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东西双雄”。一场围绕“电池 + 芯片 + 算法”的三位一体逻辑,正在跳过传统发动机的技术迭代路径,构建出一个以“软件定义汽车”为标志的行业发展新范式。汽车,正在从一台“机械燃油巨兽”演变成“超级移动终端”。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意识到,这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汽车性能之战,而是来到了百年汽车工业的历史转折点 一场围绕平台架构、智能驾驶、人机交互、生态系统的拐点之战。
从这个角度看,一汽、东风、长安这三家汽车央企的战略性重组,不再是过去那种“为了保而并”或者“为了稳而合”,而是站在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三大汽车产业转型浪潮之上,对中国汽车产业国家战略与全球竞争力的重新定义。
要理解这场战略性重组的深层动因,我们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汽车产业的演化路径,二是三大汽车央企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汽车产业的演化路径
如果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的解放牌汽车问世算起,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已走过近70年征程;而如果要从那辆名为“桑塔纳”(Santana,德国大众旗下汽车品牌)的轿车,以CKD(全散件组装)形式,在上汽安亭工厂组装完成的1983年4月1日算起,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汽车工业也已走过40余年。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属于典型的“后来者曲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次跃迁:
第一阶段:学习模仿期 (1983—2005年)
以合资为主,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理念,成立了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神龙汽车(包括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等)、东风本田、东风日产、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广汽本田、广汽丰田、长安福特、长安标致雪铁龙、长安马自达等合资企业,中国一度成为“万国汽车城”。这一时期,国企是合资的主力,中方企业主要承担生产制造任务,而技术和品牌主导权仍旧在外资品牌。
第二阶段:自主发展期(2006—2015年)
在这一时期,以吉利、奇瑞、比亚迪、长城等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快速成长,打破了“外(资)强自(主)弱”的局面,自主品牌份额逐步上升。从李书福那句“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几个沙发吗”的豪言壮语,到奇瑞尹同跃在安徽芜湖的“小草房创业”;从“保定车神”魏建军带领长城汽车从皮卡到SUV一路过关斩将,到从电池领域转战汽车,靠一款F3拿下国内年度(2009年)轿车销量冠军的比亚迪王传福。这10年,见证了中国自主品牌的真正崛起,实现了自主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跨越。同时,以上汽、一汽、长安、东风、广汽、北汽等为代表的汽车国企,也开始在自主品牌发力,有快有慢,有喜有忧。
第三阶段:变革引领期 (2016—2025年)
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汽车市场从传统燃油车快速切换到新能源汽车,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最快、规模最大、销量最高的区域市场。有两件事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是特斯拉入华,以首个独资外企汽车厂商的身份,引领了中国乃至全球电动智能汽车产业发展,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包括理想、小鹏、蔚来、小米、零跑等在内的造车新势力崛起,中国车企在电池、电驱、整车架构、智能化、产业链等方面迅速建立起全球领先优势;二是比亚迪“称王”,通过多年努力,终于在2023年销量突破302万辆,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不加其他定语的)销量冠军(2024年,比亚迪全年销量为427万辆,蝉联销量冠军),并带领中国车企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出口)市场拔得头筹,中国车企也完成了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sc20250520.pd原版全文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同时,比亚迪的“垂直一体化”、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帝国”、华为的鸿蒙智行(车机系统与智能座舱)、小米的“人车家”(生态链)等,都成为中国车企创新引领的集中体现。然而,这波以中国车企为主要驱动力的行业浪潮,三大汽车央企却不是主角,也并非站在行业变革最前线。
三大汽车央企所面临的挑战
回顾历史,三大汽车央企本是汽车产业的“国家柱石”。一汽集团是“共和国长子”,从解放牌卡车到红旗轿车,见证并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启蒙与荣光;东风汽车(别名中国二汽),军工底色深厚,也是国家“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成果,在商用车领域有深厚积累;长安汽车则是自主创新起家,也是三大汽车央企中发展自主乘用车战略最坚决、创新创业文化最浓厚的汽车企业,还是第一家跨入“千万俱乐部”(突破1000万辆销量)的中国品牌(2014年)。总体看,三大汽车央企资源雄厚、资产丰厚、组织体系庞大,然而,在这一轮新能源与智能化汽车浪潮中,走得并不快。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第一,技术路径不清晰
比如,有的企业平台架构转型缓慢,自主研发节奏跟不上,尤其是对用户生态、数据服务、智能座舱、车机系统等方面的理解仍停留在燃油车时代。这就导致很多新车型看似“新能源化”,实则是“油改电”
的思维惯性在延续,缺乏对整车电子电气架构的重构与突破,也缺乏以“软件定义汽车”的认知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
第二,品牌定位模糊
比如,旗下的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如何并驾齐驱,自主品牌车型之间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内部品牌矩阵混乱、同质化竞争严重、战略资源错配等情况发生。此外,面对造车新势力主打的“科技感、年轻化、时尚化”等标签,三大汽车央企在品牌定位与推广等层面与用户的沟通明显滞后,未能建立清晰、具象、可感知的品牌认知。
第三,国企惯性强大
多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一直推进国企改革,也取得了很多成效。然而,部分传统国企的组织冗余、效率不高、人浮于事、创新乏力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车企决策机制仍偏保守、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缺乏真正面向市场、面向用户的灵活机制。因此,在很多涉及新能源、智能化、技术创新等项目的推进中,存在“拍脑袋立项一层层上报一流程冗长一执行滞后”的典型问题,往往会让车企错失最佳市场窗口期。同时,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在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上,部分国企仍存在一些非市场化限制,难以有效吸引和留住互联网、AI(人工智能)、科技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在创新力和响应速度上,与造车新势力仍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三大汽车央企也面临“资产重、负担重、转身慢”的结构性问题。在传统产能未能有效消化的情况下,推进新能源转型意味着“两头烧钱”一既要持续维持传统业务的运营稳定,又要大力投入研发与制造体系升级,资金压力与资源分配的矛盾越发突出。尤其在当前行业竞争日益白热化、外资品牌加速本土化的背景下,三大汽车央企若不能快速破局、重塑战略,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同时,三大汽车央企还承担了大量政策性任务与社会责任,这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为企业本身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度和战略应变能力。如何在保持“国家队”底色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转型,是横亘在三大汽车央企面前的根本命题。
更进一步地讲,在“脱钩断链”与“关税大战”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智能化)正成为“工业主权”的关键链条。它不仅关乎老百姓的日常出行,更关系到能源结构(电动化)、城市治理(智能交通)、数据安全(车路云协同)、芯片控制(自动驾驶)等诸多方面。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新能源汽车这一局,不仅涉及市场竞争力,还涉及国家竞争力,包括定义标准、掌控算力、输出生态等,这些都会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再造“汽车国家队”,也就成为本次三大汽车央企战略性重组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是,“汽车国家队”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组和登场?
模式选择:是高铁模式、电信模式,还是邮政模式
在卷之又卷的中国汽车市场,三大汽车央企重组的本质,是对产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优化。这既有主动而为的成分,也有被逼无奈的意味。一方面,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崛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汽车产业成为“卷王”最集中的领域,一些汽车央企的做法,还停留在过去的燃油车时代,国务院国资委给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不容易完成;另一方面,这种卷之又卷的竞争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内耗,国务院国资委希望通过战略重组、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打造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汽车国家队”。
那么,三大汽车央企将会以什么方式进行战略性重组?显然,这次重组要解决的不是“谁合并谁”的问题,而是战略再分工、能力再聚焦,在国家战略层面筑牢“产业护城河”的问题。
对照过去10年央企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成功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以高铁模式、电信模式、邮政模式为例进行拆解,分析每种模式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利弊。
高铁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怕的是失去活力
一句话总结高铁模式的逻辑:集中资源,统一标准,减少内耗,提升效率。
回望中国高铁快速崛起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典型的“国家队突围战”:从早期技术引进到自主整合,再到打通全产业链,中国高铁在不到2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买技术”到“卖标准”的大逆转。这种模式的成功,依赖3个核心条件: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sc20250520.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