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从一本杂志开始
作者: 王奇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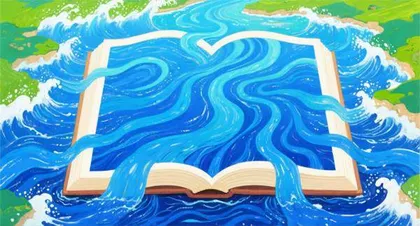
《新青年》创刊早期影响甚微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追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则是越纪念越模糊。
最初纪念的时候,只是纪念学生爱国运动;后来渐渐将“新文化运动”也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来纪念;再后来,纪念“五四”,主要纪念新文化;纪念新文化,又主要纪念“民主”与“科学”。
“五四运动其实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为开端,1923年左右结束。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声势。
历史学者在考察《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每每看到《新青年》杂志后期的巨大声势,难免会有意无意放大它前期的影响。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最初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当时,张国焘正在北大读书。
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陈独秀与蔡元培很早就认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件事必须经过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向教育部申报的时候,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最初一两年,《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既没有鲜明的特色,主编和作者的名气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响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让出版商继续维持。
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杂志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杂志投过一篇稿。当时毛泽东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
借重北大招牌,“炒作”扩大影响力
《新青年》杂志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那个时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后来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就立即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他们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杂志抗衡,但没有搞得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除了北大这块招牌之外,陈独秀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炒作”。
怎么“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杂志编辑部假冒读者的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登出来。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东方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杂志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与《东方杂志》竞争。为了打压《东方杂志》,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复辟活动。于是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中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而且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的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东方杂志》的很多老读者,老订户,不再订阅了,转过来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
除了陈独秀“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这个人到晚年,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就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为什么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对《新青年》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帮助呢?这里不说别的,仅举白话文为例。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之后的事
上面我说了这么多,意思是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1915年《新青年》杂志一创刊,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事实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还没有形成为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形成,应该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的事。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是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我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然不用说。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其他地区就要滞后一些。
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的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共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是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民主”与“科学”并非《新青年》真正主张
最后,我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三年前,有人送我一套《新青年》杂志的电子版。这套电子版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主题词检索。我拿到这套光盘后,试着进行主题词检索。检索什么呢,长期以来,我们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民主”与“科学”。于是我首先想到检索一下“民主”与“科学”这对主题词。
但是检索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但也不过五六篇。
考虑到谈论民主和科学的文章,不一定标明在标题上。于是我又检索了《新青年》杂志中“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检索的结果是,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一词的频度高一些,但也只出现1907次。在总字数多达540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和“科学”这两个系列的主题词,出现的频度都相当低。
当然,我也检索了“民主”和“科学”的同义词、近义词。检索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检索以后,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
于是我回过头去寻找他们的依据。经过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几乎所有教材和研究论著中,凡是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谈《新青年》杂志;谈到《新青年》杂志,必提“民主”与“科学”;提起“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的,题为《本志罪案答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