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斌谈穆旦
作者:苗炜 三联生活周刊:冯至1941年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这篇文章介绍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您认为,这篇文章也是针对现实的发言吗?
三联生活周刊:冯至1941年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这篇文章介绍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您认为,这篇文章也是针对现实的发言吗?李章斌:这是对时代的一个评估。冯至的表达比较隐晦,克尔凯郭尔说过,一个“平均一切”的时代没有深情,这样的时代必定会造出一个幻象,冯至借此对20世纪40年代做出批判。这个幻象可以说是“意底牢结”。有了这个幻象,大家像走在云里面一样,觉得很安全,很舒适,飘飘然,没有谁会说云下面是一片深渊或者一个悬崖,有可能会一脚踩空。假设有人说这么一句话,那么大家就会说他是一个疯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就把他踢下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穆旦就是这么一个提醒者,他穿透云雾,冷眼旁观,说出了很多要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后才能懂的话。冯至也有所意识,但是他比较懂得在什么时候说话,在什么时候沉默,冯至到1940年代末期基本上就沉默了,不再涉及他这篇文章里面的话题,他实际上把话说了一半,就没有往下说了。我们现在说话,也有点儿像冯至。
三联生活周刊:袁可嘉1946年有一篇文章叫《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他提到一种病态,即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活力的唯一表现形式。您能讲讲这篇文章吗?1948年,晋军等人对穆旦的批评,似乎是一种非常粗野的评论,到此时,是否诗艺上的讨论已经变得不可能?
李章斌:袁可嘉这篇文章中的主要概念是“政治感伤性”,他说,今日诗中的政治感伤性是属于观念的,这并不是说,作者要表达的政治观念本身含有感伤的成分,它们常常极为庄严、伟大;而是说,承受与表达这些观念的方式显示出了感伤性。很多人借观念做幌子,将观念的壮丽,借作为作品的壮丽,这都是袁可嘉的原话。政治的感伤性,有点儿像后来昆德拉所说的“媚俗”,比如说某个乞丐多么惨多么苦,读者会说他都那么苦了,我们怎么能够对他的苦难转过脸去?我们肯定要流几滴同情的眼泪。这在昆德拉看来是一种媚俗,不仅要求自己感动,还要求全人类跟着他一起感动。
这第二点很重要,即要求全人类跟着他一起感动。如果你不感动不流泪,那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不同情苦难的人。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判断应不应该同情苦难这个问题,而是说当同情苦难变成一个绝对的标准,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它就会带来问题。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给老人让座,这是很好的修养,但是不能走极端,如果一个工作一天的青年人不给一个健步如飞的老头让座,你就抡起棍子来打他,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任何抽象的观念和伦理,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下讨论,这个就叫观念的情境化或者说“情境的伦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走到一种“存在的遗忘”的状态。昆德拉说过,媚俗是存在和遗忘之间的中转站,媚俗让我们从存在通往遗忘。再回到袁可嘉,袁可嘉说应该承担一个创造者的思想和感觉的重担,创作者不能打着观念的幌子,把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思考给丢掉了,把自己作为创作者应有的敏感给丢掉。
至于说阿垅等人对袁可嘉的批评,正是政治感伤性不折不扣的一种征兆,他们讨论的话题跟诗艺的高低没有太多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抗日战争是否会让群众、集体这样的概念更有市场?会对个人造成压力?
李章斌:我打个比方来说,抗战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磁铁,它改变了原来指向各异的指针,如果没有磁场,指针可能一个指向东,一个指向西,一个指向北,但是有了这个磁铁,这些指向各异的指针都会指到一个方向去,就是民族大义的方向。原来那些写个人情感或者说个人体验的东西,慢慢地就在伦理上不合法。这也是冯至会发出对“平均一切”的感慨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一些人的写作则是例外,比如冯至和穆旦,还有小说家里面的沈从文和废名,还有批评家里面的袁可嘉和朱光潜,等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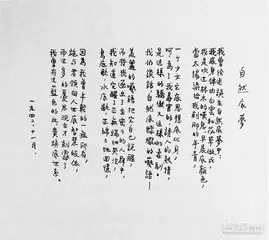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分析穆旦作品中“感时忧怀”与宗教关怀的内在角力。穆旦的这种宗教情怀从何而来?他后来在《隐现》等诗歌中表露出来的宗教情怀和他在野人山的经历有关吗?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分析穆旦作品中“感时忧怀”与宗教关怀的内在角力。穆旦的这种宗教情怀从何而来?他后来在《隐现》等诗歌中表露出来的宗教情怀和他在野人山的经历有关吗?
李章斌:穆旦参加远征军,从缅甸往印度东部撤退的时候,经过了条件非常艰苦的原始森林,野人山有很多瘴气毒虫,这是1942年的事。在此之前,穆旦的不少诗歌就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宗教体验了。宗教的体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皈依,也是向内寻求的一个结果。穆旦的宗教情怀来自他自身的经验和获取的知识,这两者不断转化而形成。王佐良《穆旦:一个中国诗人》中说,穆旦对于中国新诗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不是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
至于说《隐现》这首诗与野人山的经历有没有关系,确实是有关系的,因为里面写了很多死亡的体验,还有一些死亡的意象。对这首诗,我做过考证,他是1943年开始写的,跟他参加远征军赴缅甸的抗战经历有关系,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跨越时代的东西,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很长,1943年开始写,现在看到的版本是1947年的了,经历了多次修改。
三联生活周刊:您觉得诗人的经历,对我们理解诗歌有帮助吗?该怎么读一个诗人的传记?
李章斌:传记材料对于我们理解诗和诗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给我们一个进入诗歌的语境。但并不是说我们读每一首诗都需要去对应传记。这里面有一个常识,诗人处理诗歌写作的材料,包括他的生活体验,对一个事物的观感,也包括二手经验,从报纸上看到的或者从书上看到的,这都是诗歌的材料,还包括诗人自身的情绪状态、过去的阅读范围。处理这些材料的方式,用艾略特的说法叫“聚合”,不是说把已有的东西简单地组合,而是像化学反应一样,在高温高压之下,在催化剂作用之下,这些材料合成为一种新的东西,这是聚合。我们不能把诗歌还原为聚合反应之前的东西,而是要像伽达默尔建议的那样,去领受被语言姿态所唤醒的东西。伽达默尔在《谁是我,谁是你》中说,所谓理解诗就是去领受被语言姿态所唤醒的东西,读者用自身的经验去填补诗歌里面的空白。我们可以把诗人的传记当作一种跟诗歌平行的文本来读。传记有时可以作为一首诗的脚注,有时毫不相关,甚至跟诗歌写作截然相反,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阅读体验。我比较反对把诗歌当作传记的脚注,这就不对了,不能把诗歌当作传记的脚注,而应把传记当作一部分诗歌的脚注,这个关系不能倒过来。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一书的扉页,有一句题记,是艾略特讲何为“历史意识”,他说,历史意识是对于永恒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而且是对于永恒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个作家进入传统。您能讲讲穆旦的历史意识吗?
李章斌:这里说的“历史意识”与艾略特说的还不一样,他更重个人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我这里更重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穆旦在1940年代就有比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所谓清醒的历史意识,就是说他对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冷静的判断,并且这种判断还能够在诗歌中有所体现。如果你有判断,但在诗歌中不呈现,那算不上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意识了。历史意识,打个比方来说,你坐在一辆行驶的大巴车上,大家都昏昏欲睡,你抬头一看,司机也有点昏昏欲睡,这时候你就应该意识到可能有危险,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刚刚说穆旦是一个提醒者,他的历史意识不是仅存在于早期或者后期,而是贯穿始终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谈谈穆旦晚年的诗歌吗?好像他晚年的诗歌,句子更整齐,更好懂一些。晚年的诗歌和早年的有区别吗?
李章斌:确实有区别。奥登说过,大诗人的风格从早期到后期,应该看出显著的区别。大部分杰出的诗人都会体现出风格上的变化。穆旦晚年的作品确实跟20世纪40年代的很不一样,这里面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写作的环境和语言的环境不一样,尤其是后一点,语言环境就是指一个人日常跟其他人交流,用什么方式说话,他看书看报纸接触到的语言,其句式和词汇是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其次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穆旦作品,中间是断了很多年的,所谓穆旦的后期作品,绝大部分是在70年代写的,他早期的语言模式,还有表达方式,已经不适合进入他后来的写作当中了。他在1940年代有很多语言试验性质的表达,很多隐喻,到后期写作中基本消失了,他的后期写作,语言比较明白晓畅,没有那么多晦涩的表达。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是明白晓畅,但是它有很多深层次的观念,也可以说是比较晦涩的观念,隐藏在一些比喻的深层结构当中,这里面有一首很典型的诗,就是《苍蝇》,他用很明白的话来表达一个很深刻的时代体验。
穆旦晚期的写作跟翻译有一定的关系,他翻译拜伦和普希金,但是穆旦翻译的范围很广,他不仅是翻译这些人的浪漫主义诗歌,还翻译俄国象征主义诗人丘特切夫的作品,还有英国现代诗选,包括那些现代主义诗人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后期穆旦跟浪漫主义画上等号。简单来说,穆旦晚期的写作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大巧不工”的阶段。
比如《冥想》这首诗,最后两句是,“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每次给学生讲到这两句,大家都非常感动的。他的视野具有穿透性,不在意个人得失,而是教导人谦卑。布罗茨基有一篇文章说,如果说流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它能教会人谦卑。人要接受自己的无足轻重,就像济慈所言,“你远在人类之中”。还有穆旦的《智慧之歌》,也是现代诗歌史上最为沉重的作品之一,诗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诅咒”的东西,朝向自我的诅咒。我说过穆旦的语言有一种自反的现象,就是语言自己跟自己打架,你可以往正面方向理解,也可以往反面的方向理解,可以是双重理解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反讽的一种语言,它背后指向一种很深刻的虚无,也包含了一种“死亡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