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一实践一评价"视域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研究
作者: 曹靖 温晓宇 尚嘉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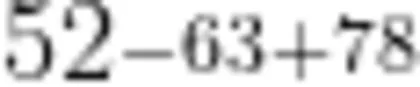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湖北高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线上线下混合式高校‘金课'建设规范与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1294,项目主持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0-0022-09
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提出“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缺技术岗位,培养一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服务国家战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撬动职业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也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行依赖于管理层子系统、执行层子系统以及评估层子系统对应的制度、实践、评价等各要素间的协同发展[]。其中,制度决定了现场工程师的培养目标、资源配置和运行逻辑,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实践是制度得以落实的中间环节,连接教育与职业岗位的需求,也是现场工程师知识、技能和素养形成的关键;评价则是对制度和实践的反馈机制,并将反馈作用于制度调整和实践优化。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现代学徒制实践在工程教育领域的创新,当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必要性、内涵特征及培养路径等方面,缺少对国际先进培养经验的比较借鉴。透过“制度一实践一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困境进行审思,挖掘德国、英国、美国三国可供参照的经验,可以为探索贴切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一、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实践梗阻
(一)制度掣肘:顶层设计供给不足、政策乏力,培养标准亟待确立
1.制度建设滞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需要各培养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协同配合,政府的各项规制行为要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产教融合政策,以补充市场机制所不能实现的功能。一方面,顶层设计不健全。尽管政策层面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整体建设,但尚未制定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指导细则、政策保障、财政激励以及推进机制,无法生成政策合力,进而延缓了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进度。另一方面,制度供给不及时。当前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是一种‘自我复制与自我维持'的过程,并未很好地激发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2],如“专项计划"对参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企业给予“金融 + 财政 + 土地”组合式激励的表述仍旧沿用《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中的政策内容。
2.政策执行延后。我国虽然形成了“部委一省厅一市局”相互贯通的政策执行网络,但各部门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的协同度与合作作为的耦合度仍不高[3]。截至2025年2月,浙江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等18个省级行政区域已依据“专项计划”制定区域适配性细则,其他省级政府则未能深度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和技能人才需求发布省域培养方案。此外,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促进条例”,地方政府无法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各培养主体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
3.培养标准落后。当前国家尚未出台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标准,不利于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在标准维度上的结构性适配。2023年,教育部公布第一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项目企业名单,共有447家企业上榜。而“企业所提供的251个现场工程师岗位在岗位要求和岗位名称等方面存在规范性不足、描述模糊的问题”4],说明培养标准的落后导致企业主体对现场工程培养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削弱其培养质量并影响培养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实践壁垒:校企衔接貌合神离、权责模糊,利益分配尚待调节
1.培养主体间未建成有效的沟通机制。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各培养主体在行为动机、价值取向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践教学安排、育人质量评价等关键环节难以聚焦。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具有长时性和延时性,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缺失导致现场工程师各培养主体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的方式不匹配,培养过程中逐渐出现“条块分割”的情形,如企业着眼于现场工程师对企业的好感度、忠诚度,或建立师徒情感连接并极力明确人力资源的流向;职业院校则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看作学生需完成的企业体验式教学活动。
2.培养主体间未生成稳固的合作关系。调查发现,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初期,企业与职业院校常通过“私人情谊"开展合作。随着企业对现场工程师培养投人的成本逐渐增多,依靠个人关系生成的培养模式运转举步维艰。此外,现场工程师培养缺少专业第三方组织的参与,各培养主体间的资源要素流通不畅,难以为现场工程师培养提供持续稳定的实践培训场所与技术指导支持。
3.培养主体间未形成一致的利益分配。职业院校遵循公益逻辑,偏重知识外溢与社会效益;企业遵循市场逻辑,追求技术垄断与经济效益,并承受实习实训设备折损、导师团队及人力资本投入的多重压力。校企双方在“合作剩余”分配中的争议,使企业调低实习实训的技术含量以应对成本损耗,职业院校压缩实践教学时间以规避风险,培养主体间的异质性行为导致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利益分配不协调及不持续。
(三)评价桎梏:专业认证主体缺位、标准缺漏,认证效能有待提升
1.评价过程中的专业认证主体缺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专业认证主体呈现“强政府一弱市场"的态势,教育行政部门基于科层制建构起相对封闭的认证场域,使专业认证制度演化为政府行政性干预的工具。同时,行业企业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专业决策权被压缩为程序性参与,其产业实践话语权在学科本位的认证标准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多主体”评价流于形式,专业认证标准与产业技术迭代速率不吻合,专业认证结果得不到行业企业的认可。
2.评价过程中的专业认证标准缺漏。专业认证标准是指特定专业领域内建立的系统性评估框架,由认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两个部分构成[5]。认证通用标准是现场工程师要达到的一般性要求,其缺漏导致各培养主体在培养过程中难以把握现场工程师的职业能力素养;专业补充标准的缺漏则导致难以为特定岗位的专业胜任力提供客观评价依据,无法精准适配行业的细分需求。此外,现场工程师培养涵盖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以及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只有采取递进式的认证标准才能实现培养目标与质量要求的纵向契合,但现有专业认证标准及体系未明确各层级的能力梯度与评价阀值,导致职业教育层级间认证割裂。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jyzx20250503.pd原版全文
3.评价过程中的专业认证效能缺失。申请注册为某一类型的现场工程师,要获得经教育部或行业协会认证专业的毕业资格。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业认证与注册工程师之间尚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联结,教育部门主导的专业认证与人社部门管理的职业资格认证分属独立框架,持有认证专业学历的现场工程师在获取职业资格认证时仍需重复参加基础性能力考核。产业界对现场工程师知识与能力的“追求”难以经由专业认证反馈到教育系统,专业认证工作也缺乏对个人职业规划的考虑。
二、德、英、美三国工程师培养的经验观照
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内涵特征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工程技术教育培养的技术工程师具有一致性,两者均属于工程技术型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还需胜任技术指导、资源协调及现场复杂问题解决等工作[。其中,德国、英国、美国三国作为工程技术教育领域的先锋,拥有成熟的制度、完善的政策。总结他国经验,能够为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提供有益借鉴。
(一)制度层面:立足国家战略所需,推行协调适切的育人机制
1.统筹布局:形成顶层设计统领,区域实践平台驱动,牵引工程教育资源向高新技术领域倾斜。德联邦教育暨研究部于2021年发布《联邦政府2025高技术战略报告》,明确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技术、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工程领域为国家优先发展方向[]。2022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提出今后4年亟待实现的5项高新技术战略目标有:推动清洁和可持续制造以支持脱碳、加速微电子和半导体制造创新、实施支持生物经济的先进制造、开发创新材料与加工技术、引领智能制造的未来。美国政府认为,同步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教育与培训,推动职业与技术教育体系的升级迫在眉睫,要通过支持行业合作培训项目为学徒提供实践培训机会,强化学徒对工程领域的认知8。《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区域创新引擎计划》强调,由各州政府依据区域特色汇集产业界、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等共建体现地方特色的“创新引擎”,如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工程教育中心、密歇根州的先进制造工程教育平台主张“场景驱动”的育人活动,提出要为区域产业链的现代化发展培育行业适配性高的技术工程师[9]。
2.制度保障:健全政策法规以引导企业行为,保障未来技术工程师顺利成长。2017年,英国推行“学徒税"制度[,提出年薪总额超过300万英镑的雇主按年度工资总额的 0.5% 缴纳学徒税,用于支持学徒培养,并要求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制订学徒培养计划,促使企业承担起技术工程师培养的重要角色。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加强21世纪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技术工程师提供基于工作的学习机会,包括工作场所体验、增加职业与技术教育课程的相关内容与指导、提升个人就业竞争力并明确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2024年,德国政府发布由莱布尼茨教育研究与教育信息研究撰写的《德国教育2024》,提出要赋予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法定管理职能,政府与社团组织依据职责分担投入资金,通过企业培训岗位补贴、跨企业培训机构经费支持等举措,增加企业及社会合作伙伴的收益,充分调动企业主动及深度参与技术工程师培养的积极性[12]
3.标准指引:制定技术工程师培养规格,厘清技术工程师基本能力要求,明晰人才培养方向。2025年1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颁布职业培训条例,明晰不同行业领域技术工程师的培训标准及专业技能要求,并将行动能力、个人能力、社交能力、方法论能力及学习能力确立为技术工程师的核心能力[13]。2020年,英国工程委员会发布第四版《英国专业工程能力和承诺标准》,提出技术工程师的五项核心技能,包括知识和理解、设计开发和解决工程问题、责任管理和领导力、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个人与职业承诺[14]。美国工程教育协会也明确要求技术工程师须具备个人效能能力、学术能力、工作场所能力、行业广泛的技术能力以及专业技术能力[15]。此外,美国国家专业工程师协会发布的“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也强调技术工程师的工程伦理素养,提出技术工程师在设计或执行工程项目时需将公众的健康、安全、福祉置于首位,并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16]。
(二)实践层面:注重产教有效融合,筑就多元主体参与的育人环境
1.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促进学岗对接。德、英、美三国的技术工程师培养可归纳为“项目依托"模式和“合作教育"模式。项目依托模式以“基于任务的学习”为教育理念,采取应用导向的项目式教学,通过组建“师生共同体”,在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与攻克企业技术难题的过程中推进人才培养,如英国华威大学与施耐德、奎奈蒂克、科威国际等企业联合实施“学位学徒项目”,学徒或受训者将参与具有规模和多样性的实际项目,能够在完成知识、技能学习的同时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并朝着职业资格迈进[17]。合作教育模式主要指校企在培养对象选拔、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教学与指导、师资队伍建设、考核与评价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学校邀请企业以“特殊主体”身份深度参与协同育人,特殊主体指学校依据先进性原则与契合性标准,遴选出与学校人才目标定位一致的行业企业作为专门合作主体,与学校共同承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培养任务,如巴登一符腾堡双元制大学是德国第一所将职业培训融入学术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其课程将高等教育内容与众多合作企业的在职培训相结合,即提供学术技能和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使学生或受训者能够获得广泛的实践经验[18]。
2.发挥教育中介组织作用,增强育人成效。为教育中介组织提供较为开放的成长空间,并引导其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工程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协会和鲁米娜基金会定期发布工程技术教育和市场需求分析报告,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及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提供决策参考。同时,教育中介组织定期举办交流会和专业研讨活动,保持与政府、院校和企业的密切联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潜存风险,推动工程技术教育的资源共享与合作。美国未来就业组织通过设计解决方案、推广实践、投资创新来与雇主、投资者、行业协会、政策制定者、学校等建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组织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项目,并帮助雇主识别具备符合其需求技能的技术工人[19]。此外,教育中介组织通过提供经费支持,为产学研合作铺路搭桥。例如,德国劳恩霍夫协会作为连接行业与学校的中介组织,与汉堡应用科技大学、汉诺威应用科技大学、哥廷根应用科技大学等高校实施合作试点项目,设立合作专项基金并定向支持前沿技术研发与相关师资培训,为工程技术领域的学生提供贴近产业需求的实习机会。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jyzx20250503.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