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
作者: 吴义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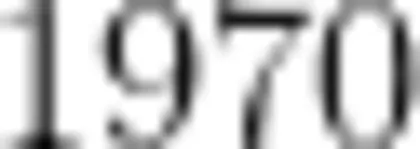
如何有效地叙述和想象1960至1980年代的自我和地方,如何讲述那个时代自我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在确认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内部差异性元素的同时,建构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王蒙来说,其在新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①的经历和体验具有独特的资源性价值。作为一个年少成名、历经波折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王蒙能否以及如何用文学的形式承担起以个体故事讲述民族故事、国家故事,以地方讲述承载共同体命运的文化责任?在这些问题上,王蒙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在伊犁》②,可以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文学答卷。
一、地方生活的呈现及穿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生活根基
共同体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共同体可以表现为家庭、社区、教会、族群、民族等等能使个体寻求归属感的文化形式”③。个体和不同形式的群体,对“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皈依、文化归属,是塑造主体共同体认同的关键。关于国家认同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国家认同并非意识形态产物或者学术体制内部自转而产生的空洞话语,而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渊源。这来自于中国的复杂构成一它从来都是多地域、多族群、多语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体’,其核心凝聚力来自于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④。《在伊犁》以特定历史情境下伊犁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和入口,从地域、族群、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形象地展示了对这一共同体的深切体认。
《在伊犁》通过对伊犁、新疆地方生活和风俗细致而耐心的描述,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在王蒙笔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认识,它不是来自理念、说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是从生活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呈现的。王蒙是一个热爱生活、始终对生活葆有真诚信仰的作家。他极其注重文学的生活维度,将生活作为其创作的基础和可靠的资源。他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首先,生活与人密切相关,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所谓客观生活或理念化的“生活”。他最喜欢和欣赏“那些惟妙惟肖地刻画生活、刻画人的精神世界的作品”。在他看来,“精神生活当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着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气息,是我最偏爱的东西。这种生活(包括人的内心)境界,是我最重视、最神往的东西”③。其次,文学表现生活的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表现,或“不完全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而是按照生活在特定的人的心目中的感受,用类似电影的主观镜头的方法,既表现人的内心,又表现人的环境、遭遇和生活,既追求客观的真实,也追求主观感受的真实”。无论以何种生活为描述重点,以何种方法来表现生活,“不是取消了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一原则,而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再次,经历了三十年坎坷人生的王蒙,在复出之后更相信生活的美好,更注重挖掘和表现其积极、美好、温暖、光明、有建设性价值的一面。他反复用抒情的笔调感叹:“生活有多么美好!这仍然是我当今作品的一个主旋律。”“生活仍然是美好的,而且是更美好了!在我飽尝了生活的酸甜苦咸辣五味之后,我更感到了对生活的甘之若饴。”“生活是发展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会相当快地进入我的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生活是不会停滞的…我们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我最近又来到新疆伊犁地区了,我要倾听新时期新生活的声息,我要表现新时期新人物的新生活,我应该写出更好一点的新篇章,我必须加油努力!”③上引文章《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完稿于1981年9月作家重返新疆伊宁之际,时间亦在《在伊犁》系列小说之前。王蒙在文中关于生活、时代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理解,是进入《在伊犁》系列小说的一把钥匙。③小说主人公老王和伊犁人民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处境及遭遇,关联、言说着民族的历史和人民的心声;伊犁城乡面貌,各民族的生活情态和文化习俗,使小说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品质。在上述"客观性""生活性”的纪实性描述中,始终有“我”的眼睛在注视,有“我”的心灵在触摸,始终洋溢和流淌着激情和温情。正是因“我”的存在,而使伊犁成为渗透着主体认知和体验的独特风景:“这一段经历确实是非常难忘的、奇特的与珍贵的”;在时空转换中,“那时的生活反而愈加凸现和生动迷人”;回忆起来,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历史的动荡,而是“我们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在沉重的、不幸的年代,“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③因为爱生活,所以渴望表现它。《在伊犁》系列小说通过“简朴的记录”,忠实地描绘特定时代情境下伊犁各族人民的自然生活、心灵世界和精神面貌,艺术地“再现”那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所忽略的“生活”之美。作家通过一种真实却又巧妙的表现本领,使大时代背景下似乎并无多少深刻意义的平凡人事具有了特殊而又普遍的意义。
在王蒙自然真诚的笔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边远地方平凡的日常生活之美被简洁传神地揭示出来。从《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的房东二老家,到《淡灰色的眼珠》中的马尔克家、《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的图尔拉罕家,再到《逍遥游》中各族人民聚居的城根小杂院,各民族人们居住的房屋、院落和生活的环境,简单、清洁、优美,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又知足,在物质生活条件极为有限甚至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能按照自己的民族习惯,过着有秩序、有仪式感的生活。他们保持着传统的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和宗教仪式,自如地应对一切情境。他们是乐观、充满智慧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乐观、节俭,享受舒适、正直、善良和快乐的生活。在这里,生活得以提升,展现了自身的地位,具有了一种高贵的品质,获得了尊严。
需要注意的是,《在伊犁》注重以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式表现伊犁、新疆各族人民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生活,与那种专注于历史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模式有所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对历史的放逐,在关于伊犁、新疆的生活场景和细节描述之中,有着时隐时现、似断实续的时代隐线和历史行进的足迹。首先,在王蒙笔下,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共同的命运而形成的,共同体意识是历史产物,它始终存在,并不是新生事物。其次,小说也生动书写了新疆人民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公路、风景等写到了新疆日新月异的变化。再次,小说也不回避边疆生活的特殊性,民族、宗教、语言和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以及生活的艰难和各种挑战,但更注重表现新疆人民的乐观、智慧,甚至面对“文革”这样特殊的政治处境,也可以凭生活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淡化”“纠正”其带来的伤害与影响。小说对时代和历史的艺术处理,巧妙地揭示了共同体的历史维度和发展: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形成与建构实践,是人民在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中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yzjl20250308.pd原版全文
注重经验性的现实生活,而不以某种脱离人们生活实际和人的本性的话语为旨归和依据;推崇和强调人心、情感而非某种超级理性话语,是《在伊犁》生活美学的基本特质。小说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抒写主人公老王和伊犁各民族群众之间能将心比心,人与人能体会特定情境下的“难能”与“可贵”。这里有同情和理解,也有对个人尊严、人格和相对自由的空间的尊重。小说中的老王是个来到基层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外来者、作家,他与伊犁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有着民族身份、政治地位的不同,以及经历、遭遇和文化修养上的鲜明差异。对于伊犁当地人来说,老王显然是个来自外乡的“客人”。前者在伊犁出生、成长或长期移居伊犁,与那片由河流、树林、土地和庄稼构成的小世界融为一体,是这个地方小世界的一部分。而老王只是这个小世界的“偶然”的“进入者”。各方面的差异,加之与伊犁地方的关系不同,造成二者对同一个地方、同一片土地有着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差异性?有研究者提醒:“少数民族从来都不是与整体性相对的差异性,而是整体性中的特定性存在。这不是抹杀少数民族特定的民族历史、风俗、文化,而是避免其陷入认同混乱和文学上的风情化叙事。也是在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思考关于时代的重大命题,要求把握整体性的思考。”@对此,《在伊犁》既表现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真实描述了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礼仪习俗、宗教信仰;在表现“习相远”的同时,小说又注重表现“性相近”,描绘不同民族人民之间共通的朴素的人性情感。在此,王蒙笔下的“共同体”呈现为一种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热情淳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们对知识文化的尊重,以及同为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他们爱国、敬老、重学、重农、惜粮、积德劝善的共同美德。《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穆罕默德·阿麦德极为尊重“北京来的”老王,并以最高规格款待他,小说写到他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他是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老王则“向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学习,学习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团结”。这篇小说的最后写到一处细节,穆罕默德·阿麦德大声说:“…我要流浪去,在我们的母亲祖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流浪!”“‘伟大的祖国’几个字,他突然改用汉语说,他的两眼发出了邪而热的光。”对祖国热烈诚挚的爱激荡着这个经历坎坷的维吾尔族人身心。《淡灰色的眼珠》中马尔克称老王为“干部”“书记”“汉族大哥”,“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来说,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是书记!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主人!”他在与老王的交谈中,说出自己请老王做客的想法:“‘在我们心里',他指指自己的心窝,‘我们对老王同志是有敬意、有理解,也有友谊的好人哪!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噢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心,我们心贴着心这岂不好哉!’。”在富有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中,不难感受到马尔克这个普通的少数民族农民、木匠,对老王和汉族同志的友谊、敬意和对党的信任。《边城华彩》写新疆少数民族同志在春节时给汉族同志拜年,汉族同志在开斋节与古尔邦节时给少数民族同志拜年的风俗习惯。新疆人认为“拜年可以加强民族团结”。
“在伊犁”,作为地方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之间、伊犁百姓的命运与中国的历史命运之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同样关心中国的现实和命运,对中国历史转机与命运转变也有着相同的期待和态度。这一点在《虚掩的土屋小院》《葡萄的精灵》等着力描写房东二老和老王日常生活及内心交流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共通情感与家园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情感基质
哈布瓦赫揭示了集体记忆的情感性质:“哈布瓦赫认为在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是暴力原则而是爱。他坚持集体记忆的情感性质。正是情感纽带使个体被归属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集体。不是暴力,而是情感把文化团结在一起。情感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并给予记忆以色彩和定义。”在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等共同体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情感、想象、形象、感觉起着与事实、知识、理性同等重要的作用,并且因其潜移默化的渗透性,更具有内在的持久性。“在伊犁”是一种植根于作家记忆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隐喻和象征。作为个体记忆的结晶,作家“在伊犁”的经历和见闻、感受,植根于伊犁的具象如自然地理景观,伊犁各族人民的形象、行为,伊犁的器物、风俗中。同时,这些凝结着个体经验的景物和事物,又关联着普遍性的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历史)。以普遍的人心为依据的共同体伦理情感,灌注全篇,是构筑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在伊犁》注重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有着丰厚的情感内容和清晰的家园意识。小说有意识地将作家的个人情感与共同体情感相融合,在传递时代情绪的同时突出了联结各民族成员为共同体的普遍情感,通过贯穿性、弥漫性的情感书写,重构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小说呈现的“共同体”是情感的共同体、深情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
在谈到“真正好的小说”时,王蒙认为:“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探求、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幽思。”如果说,这一表述的前半部分侧重于文学之与时代、历史、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维度和开阔、深邃、广博的宏大品格;那么,后半部分则更突出文学之与人、个体的关系,强调文学的个体感受性、情感性维度和真诚、深切、细腻的品格。《在伊犁》体现为二者的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即是情感共同体,是建立在普遍的共通的美和善的人性基础之上的。按照王蒙的看法,共同体是感恩、快乐的共同体,深情的共同体,《在伊犁》记述他个人在伊犁、新疆工作和生活期间,与当地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时时处处流露出他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感恩之情。他笔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构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一个“深情共同体”,洋溢着一个多民族团结和谐、共荣共存的“共同体深情”。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yzjl20250308.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