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X一起读书
作者: 蒋芳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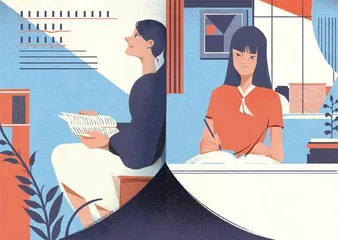
“我们不要等到久经世事之后才开始写作。”
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被闪电击中,便去寻找它的出处,发现它来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随笔集《偶然的创造》,便在二手书网站上买了一本。
费兰特在《冲击》一文中说,这些随笔是“偶然创造的”,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随机应变,应对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一样。在这本二手书上,在这段文字下面,不知哪一任书主,用铅笔画了线,线条纤细笔直,不容置疑,仿佛画下了一个真理。我微微一笑,也画上了属于我的线,它弯弯曲曲,和那些直线并在一起。
写作有一种不可预知性,就像一段旅程,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人,往往在你的计划之外。阅读也是,好的作品总能带你去往从未去过的地方。而那位在我之前画线的朋友,便是一位旅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便用“X”来指代吧。
很多人认为,自己要有足够的文学功底或者生活经验,才能开始写作,但费兰特不这样认为。在《必要的写作》一文中,我看到了最初打动我的那个句子:“我们不要等到久经世事之后才开始写作。”在费兰特看来,对那些想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是刻不容缓的,要不断强化它的紧迫性,把它摆在很多事情的前面。即使没有笔和纸,也要在自己的头脑中不停地遣词造句。在这篇文章里,我画了很多线,很高兴,X也在同样的地方画了她的线。
在一篇谈论母亲的文章里,我和X却不约而同地停住了想要画线的手。费兰特说:“大约十岁时,我开始恨她(母亲),也许是因为我太爱她了,一想到会失去她,我就一直生活在焦虑中,我必须贬低她,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默默地看着费兰特的坦诚相告,体会着她,理解着她,但并无共鸣。我们的沉默在书外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共鸣。
《女版名著》里,费兰特提出一个特别好的设想:很多小说的主人公是男性,如果换成女性,故事还行得通吗?《这就是我》里,她为“为什么某张照片里的自己特别漂亮”找到了答案:其实照片里的自己也是真实存在过的,只不过那是在罕见的时刻。我在那些充满新奇想法的句子下面画线,可也是在这些时候,我发现弯曲的线条旁边,再也没有了纤细笔直的属于X的踪迹。
是X没有看上那些文章吗?
我回过头去翻看前面的文章,发现X最后的画线落在《无缘无故》一文的结尾:“也许,敌人仅仅是产生于情感的衰竭,一个人抽身而出,想要摆脱一种辛苦、复杂的处境,也就放弃了快乐,还有友谊带来的暧昧的东西。”
真是令人五味杂陈的画线。
我劝说自己要平和地看待这件事:X并不知道我的存在,这段画线不是因为我而画下的。我也不愿意相信,她是没有看上后面的这些文章,因为我们在前面那么多文章里都能心心相印,又怎么可能在最后几十页失去共鸣呢?她一定是因为什么,突然终止了阅读,甚至将这本书转手他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购买二手书,因为二手书里总会留下一些前任书主的痕迹和故事。也因此,我才认识了X。
有了X的陪伴,阅读费兰特之旅变得愉悦而又意味深长。而这位陌生知己的突然别离,也让我充分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常和惆怅。我想告诉X,我喜欢和她读书的时光,喜欢和她一起在同样的段落画线,在同样的篇章里沉默,也接受她最后将阅读的孤独还给了我。
希望有一天,她还是能将这本书读完。
真想知道,她又在哪里画线?
(本刊原创稿件,Cyan Lin图)